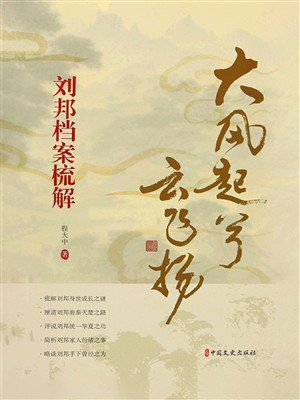三、出生地
关于刘邦的出生地,《史记》中已有记载,即“沛丰邑中阳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丰县中阳里街道的范围。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沛丰邑中阳里”指的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和哪一国的称谓?何谓“邑”?何谓“里”?
“沛丰邑中阳里”是战国末期刘邦出生时的地名称谓
司马迁所指“沛丰邑中阳里”这一称谓的时间,应该有两个可以分析判断的时间段:
一是司马迁按照写《史记》时的行政地域划分为依据,指出刘邦的出生地,是西汉中期的沛郡丰县中阳里。
二是司马迁以刘邦出生时的行政地域划分为依据,指出其出生地,是战国末期的楚国沛县丰邑中阳里。
对第一个分析判断的时间段可以首先排除。因为刘邦建汉后,为提升家乡沛县的名声,将秦时沛县所隶属于的泗水郡更名为沛郡,并同时划归沛郡下属“县三十七”。《汉书·地理志》就此记载:“沛郡,故秦泗水郡,高祖更名,治所在相县,辖相、萧、丰、沛等三十七县。”也正因此,几年后刘邦探望沛县时,把沛县设为汤沐邑而不包含已分置出去的丰县,故沛县父老请求刘邦“哀怜之”而以丰“比沛”。也就是说,自西汉建国初始,丰邑独立设县并直接隶属于沛郡,而不再是沛县下属的一个城邑。因此,如果《史记》中的“沛”是指西汉中期的沛郡,司马迁应该写为“沛郡丰县中阳里”,或“沛丰县中阳里”,而不是“沛丰邑中阳里”。不然司马迁为什么非要把已为县治的丰县写为丰邑呢?
因此,本书肯定第二个分析判断,即:“沛丰邑中阳里”是指战国末期刘邦出生时的楚国地名称谓。
如果肯定第二个分析判断,还有必要从沛县初始的历史,以及沛县、丰县分别设置县治的时间简单说起。
沛县地域古称“沛泽”。相传唐尧时,名士许由拒不接受尧的禅让,为躲避而隐居于沛泽,这说明此地当时乃是一大片水泽、陆地相间的丰沛茂盛之地。后来又有老子在沛泽隐居悟道之史说。而“沛”作为地名,不仅出现于《史记》,也在反映春秋战国历史的《战国策》中有记载,其中说:“楚破南阳、九夷,内沛。”“九夷”是先秦时期对居住在淮河中下游部族的泛称,此处虽不能说明当时“沛”的行政建制,但也说明“沛”地在“九夷”范围内,是值得单独提出而颇有影响的一片地域。公元前 286 年之前,沛地隶属于宋国。但至公元前 286 年时,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灭掉瓜分,沛地归属为楚国。而战国期间各战胜国普遍的做法是在侵吞他国的地盘上设立县治,如楚国在公元前 706—前 701 年时,就将灭掉的权国改设为权县,是周代最早设立县治的诸侯国。由此可以判断,沛地自属楚国后就已经被设置为县了。
公元前 221 年,实现全国统一的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 36 郡,泗水郡(《史记》亦记载为泗川郡)为其中之一;泗水郡辖沛县,沛县辖丰邑。再据《汉书·地理志》载,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设楚国及沛郡,丰邑独立为县,成为和沛县并列的沛郡下属 37 县之一。但此说和东汉荀悦所著《汉纪》不同,《汉纪》中记载: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刘邦灭黥布返沛,以沛为汤沐邑,“既至长安,立丰县”。
 即丰邑是在前 196 年从沛县分置为县的。虽然史书记载不同,但也均说明了丰县是在刘邦称帝时期独立设置为县的。自此以后,虽朝代屡有更替,但沛县和丰县一直各自存在并延续至今。
即丰邑是在前 196 年从沛县分置为县的。虽然史书记载不同,但也均说明了丰县是在刘邦称帝时期独立设置为县的。自此以后,虽朝代屡有更替,但沛县和丰县一直各自存在并延续至今。
上述所说是不可省略的历史铺垫,因为就此分析,才能说明《史记》中“沛丰邑中阳里”之称谓所对应的年代。也就是说,自公元前 286 年宋国灭亡起,沛地归属楚国已经设立为县,而作为当时其治下的丰邑中阳里,在刘邦出生时的公元前 247 年被称为“沛丰邑中阳里”当无问题。同样,自秦朝始至汉朝建立,虽然沛县隶属于秦新设置的泗水郡,但沛县的建制与管辖范围没变,因此对当时刘邦出生地“沛丰邑中阳里”的称谓也依然准确。至于丰邑分置为县,那已是刘邦称帝以后的事情了。
对此,应劭、孟康、师古三位先辈史学大家,早已在《汉书》中作出了相同的注释说明:
应劭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曰:“后沛为郡而丰为县。”师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举其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喻之’,故知邑系于县也。”(《汉书·高帝纪》)
如上,我们肯定第二个分析判断,并明确得出如下结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指的“沛丰邑中阳里”这一地址称谓,是指汉朝建立以前的行政隶属关系。即刘邦的出生地为当时的楚国沛县丰邑中阳里。
何谓“邑”?何谓“里”?
以上以“沛”为引解释了“沛丰邑中阳里”的指向年代,下面再简析一下“邑”和“里”。
“邑”是指具有较多人口聚居的一定地域范围。在古代它可以指国都,也可以指一般的城镇。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里指无先君宗庙的城镇为邑。《六国论》说:“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这里的“邑”是指比城小一些的乡镇。《国语·齐语》则说:“三十家为邑,邑有司。”而《周礼·地官·小司徒》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作注补充说:“四井为邑,方二里。”显然,这里的邑指的就是类如较大的村镇了。从以上引据可以看出,邑的层级和范围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它可以大到国都,小到村镇。并且,它有时又延伸为一个人为任意圈定的地域范围。如刘邦称帝后“以沛为朕汤沐邑”,赐萧何食邑 8000 户等;后世《新唐书·房玄龄传》也记载:“进爵邗国公,食邑千三百户。”这里表述的就是一个无明确范围,而以户数为标准的私人封地概念了。因此,从总体上看,古时历代人们对“邑”的理解和运用多有不同,但一般多指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小城镇。
关于对“里”的解释,《尚书·大传》卷二中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汉书·食货志》记载:“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宋代朱熹在其《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中又说:“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从上述历史文献中对“里”的解释与运用可以知道,随着朝代的更替或所在不同的行政区域,这个“邻、里”地缘关系范围的大小,也有不同的规定和说法。但总体上说,对邻的范围大都固定在四到八家的相邻关系中,而里、乡的范围则大了许多。它不仅是人们因居住而产生的地缘关系,而且也延伸为一种基层组织单位。这既是一种以户数和住户间的距离所划定的地域范围概念,也是随时代发展和人口增多,人际关系需要逐步规范治理而不断优化调整的社会组织表达。这种以户数和距离范围划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随时代的发展并未消失,如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籍贯是彭城绥舆里,而其出生地则在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明朝朱元璋推行里甲制,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使其成为一个明确的地域行政组织概念。即便时代发展至今日,“里”的地域称谓虽已多不具有行政职能,但依然在广泛沿用,如上海市的“里弄”、南京市秦淮区的“长干里”、北京市众多以“里”为名的居民区等,而现在的台湾乡村则更是普遍以“里”为行政单位,还依然具有基层社会组织的意义。
不仅如此,以“里、党、乡”等所划定的民居范围,还衍伸代指为人居关系用语,如“邻里”关系、“乡里”关系、“乡党”关系等。而这些用语以其蕴含的浓浓亲情,也在历代的社会交往中广为称之。
总之,刘邦出生于“沛丰邑中阳里”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在邑曰里”,也说明中阳里在当时是丰邑城内的一个居民小区。只不过那时的小城镇居民,还主要以农业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