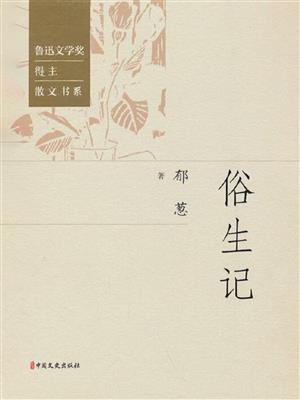俗世如玉
早年朋友给我刻过一方闲章,上面刻着我常说的八个字:“心有闲趣,身无虚名。”这方印章,是我心境的真实写照。记得我在一篇散文中说过,我是一个乏味、单调的人,除了简单的生活、写作,没有多少其他嗜好,不善交往,不善应酬,也不喜欢迎来送往。我性格的形成,除了先天的那一部分,大概就是受最初结识的田间、徐光耀、李满天等前辈大师内涵洒脱、特立独行性格的影响。所以我做了几十年的刊物编辑和主编,除了会议和活动,跟我在一起单独吃过饭的作者几乎没有。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总觉得现在的文坛,充斥着世俗气、市侩气、江湖气,我无力改变,但起码我自己尽量多些文人气、超然气、诗人气,离那些非诗的事与人远一些。离得远了别人会说你孤僻、没情趣,时间久了,朋友有饭局也就不叫我了,正好,清心寡欲,各得其所。
一直说生活是第一位的,所以除了写作,乏味的我也有自己的乐趣和喜好。比如说,我爱逛古玩市场,爱赏石赏玉,喜汝瓷,觉得能识新旧、辨真假,这也属于我浮浅生活中不多的爱好。好像我的不少同行都有这样的雅好,文人之趣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一些物什才被称作“文玩”,我也没有能够脱开这个“俗”。
喜欢捡石头,喜欢去欣赏一些旧物件,这是我在编辑部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养成的习惯。我并不懂收藏,也并不是很喜欢收藏。1998年左右,我在编刊物的思路上与当时的省作协主要领导尖锐对立,那些年《诗神》办得很有影响力,却一定要我改成《诗选刊》,说是可以盈利。我的性格倔强刚硬,宁折不弯,一直顶着。当时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如果长期在那样的纠葛与矛盾中,我会撑不下去,去旧货市场是我在那个特定的阶段为自己选择的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我可以到那里走走。逛旧货市场的时候是需要专注的,一些繁杂的事情也就忘记了。当然,造假会永远走在人们认知的前面,所以有时候也买到不真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所谓值不值,有个嗜好确实在当时缓解了我的压力,起码给了我几天的忘我,这就值了。
收藏这种事情是没有尽头的,像个无底洞,永远没有满足。比如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是独特的,无论它的品质和形态怎么样,见到一枚石头你都会觉得它是新鲜的,刺激人的购买欲,于是就有想得到的冲动。买回来之后,如果是很有品位的石头,而且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就是喜欢,这就买对了。我非常不喜欢所谓像什么不像什么的石头,像什么动物,像什么树,像什么鸟,越看越觉得乏味。所以朋友们有时候问我摆在案头的清供石像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它什么也不像,就像一块石头。石头本身存在了数万年数亿年,最后能把自己修炼成为一块石头,已经是很大很大的造化了。
星期天的时候,我爱到石家庄高东街古玩市场转转,换换心境。古玩市场艺术界的熟人多,跟朋友们聊聊天,偶尔也花个三五百元钱,淘一件喜欢的物件,给自己带来起码几天的欣慰。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为几元纸币,淘来的也不会是什么传世之宝,仅是一种乐趣。不过说句实话,能够“捡漏”的机会也实在不多,这要看眼力,也要凭缘分。有时朋友们问我怎么能辨别玉的真伪,我说,这跟写诗一样,靠悟性。喜欢赏玉在于它的“质”,喜欢汝瓷在于它的“变”。你看那一枚和田玉籽料,虽是软玉,但质地温润,坚硬如铁,不是坚硬如铁,而是比铁还要硬。如果你用刀子刻在玉器上面,留下的不是石头的痕迹,而是铁的痕迹。玉石的硬度,它的润度,它的韧度,它的密度,甚至它的亮度,让人觉得有一种神韵。许慎老先生在《说文》中讲玉有五德,玉之德其实在于人之德。你性情中韧它就韧,你性情中温它就温,你性情中仁它就仁,你智它智你锐它锐你洁它洁。子曰:“玉者,温、洁、润、韧,其声金,其性和,其质纯,与君子无异。”这句话,是我冒充“子”们“曰”的。当然不要说古代的璞玉了,就是中国当代雕刻大师的一些精美的玉雕作品,那价格也让人瞠目结舌,非我等所能企及。一块玉,无论你怎么雕,你雕的是佛,它就有佛性,你雕的是花,它就有灵性,但只要你一雕,唯独就欠缺了神性,欠缺了初始、自然的味道。欣赏玉,我愿意欣赏它原始的状态,欣赏它的质感,所有附着在玉之外的东西全部不存在。许多东西,你赋予它什么,它就是什么,比如茶,它其实就是一片叶子;比如玉,它其实就是一枚石头。最近读到朱熹老夫子的一句箴言:“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之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这句话映射了今人的浅薄,也说到了真正的璞玉应有的内敛、内涵的品质,还是没有离开“质”字。其实除了玉,其他石头我也喜欢欣赏,前些年常到附近的河里捡石头,北方的石头由于少有水的滋润,所以粗粝,后来就放弃了。但每到外地,还是要捡回一块那里的石头,倒不是因为石头有价值,而是因为其中有记忆。
有一些爱好,也就有了一些故事。2009年5月,我去西安参加中国诗歌节,吃过午饭,到西安古玩市场转转,看到一枚和田玉籽料鸡心佩雕件,玉质雕工都看得上眼,但犹犹豫豫,便错过了。回到石家庄,还是惦记着那块玉佩,于是给西安的朋友打了电话,把钱汇过去请他们替我买下来。好在那是一个古玩城,有固定的店面,朋友找到后给我寄来,至今仍然经常带在身上。我的一位兄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从北京来石家庄,恰好是星期天,我陪他去古玩市场,在地摊上看到一个双面雕的和田玉童子,当时他行程匆忙,卖家也不让价,只好放弃了。回到北京后兄长给我来电话,嘱咐我再去找。因为没有记住那位摆摊者的模样,而且摆摊的大多不是本地人,连着几个星期,我一个地摊一个地摊去看,还是没有找到,这成了那位兄长的遗憾,也成为我对兄长的一份歉疚。
早年石家庄棉一立交桥下面有一个旧货市场,我经常能在那里找到一些看似没用却很有意味的东西。有一次我无意中翻看旧书摊上的一个老笔记本,那个笔记本非常精美,是20世纪50年代最讲究的那种精装硬壳笔记本,浅棕色的封面,当时我是因为里边夹着的几片干树叶和几朵干花,觉得好奇而买的,好像也不贵,就一块多钱。日记本的字迹流畅俊秀,一看就是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笔。她是一位老大学生,日记详细记录了她从南方来到石家庄之后的生活和两段爱情经历,非常细腻和详尽,表达也很自如,没有流行的那些概念化的语言,很朴素。我当时觉得,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如果能够记录下来,就是一部不错的小说。这个笔记本一直在我的办公室的书橱里放着,后来与一位小说家谈起此事,他看了笔记本,很感兴趣,我就送给了他。我不知道这位同事后来把那些文字整理成小说了没有,但那位优雅的女士在我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那种纯美得让人心动的印象。日记本的扉页上写有她的名字,后来我还根据她表达的内容猜想过她可能的单位,并且打电话寻找过日记的主人,但没有找到。
再说我的另一个喜好:汝瓷。中国这么多好的瓷器,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定窑、龙泉窑,我们邯郸的磁州窑,等等,说不出有多少种。土皆为瓷,有多少土就有多少种陶器瓷器。我独赏汝窑,是由于它的“变”,也就是变化。汝瓷以玛瑙入釉,用一只汝瓷茶杯品茶,用着用着就“开片”了。开片就是渐渐显现其纹理,“久用之后茶色会着附于裂纹处,形成不规则的变幻交错的花纹,故而手感润滑如脂,有似玉非玉之美”。喝绿茶,时间久了,会发现茶器上面有一条暗暗的金线慢慢浸出来;如果喝红茶,会发现茶器渐渐有朱红线,如果喝普洱,慢慢会发现褐色的纹理;如果这几种茶一起“养”这只茶器,也许渐渐浸出来的就是“金丝铁线”。这些变化突如其来纵横捭阖不可预知,或者张扬或者细腻,或者无序或者均衡,总之会出乎意料。我的脾气急,“养”几只杯子也是在养自己的性子,而且好的汝瓷有个特点,叫作大器开小片,小器开大片。大茶洗,开非常细腻的片,而一个小杯子,却开大片,也就是大的纹理。北宋皇帝赵佶(宋徽宗)喜欢汝窑,但那时受工艺限制,据说入窑百件仅得二三,有点儿过,总之说明了烧造的难度。那时候人工烧造,上千度的高温,把握之难可想而知,足见汝瓷之珍贵。中国有很多奇妙的现象,比如许多很好的东西,像汝瓷、明代的宣德炉,那么好的东西,突然就没有了,汝瓷作为一种官方的瓷器,最后竟然失传了,而且成器的相当少。还有像宣德炉,那么坚硬的金属重器,怎么会在明之后突然就消失了?我的一个朋友在文物研究所工作,考古方面颇有些造诣,他也经常去古玩市场转转,我说:“你告诉我,什么样的是宣德炉?”他对我说:“说真话,我在这个市场上转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宣德炉,有的只是仿造,无非年代远近而已。”
实际上还是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有用的才是最好的。”世界上有许多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对于你没有用,或者可望而不可即,它的好与坏对于你无足轻重。当然,这么多年近朱者赤,我不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好,收藏从根本上说不是眼力的问题,而是经济实力的问题。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好玉,什么样的玉有价值,但我买不起,我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完全不可能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也就是玩一玩,消耗一些时间而已。当年徐光耀先生(写《小兵张嘎》的著名作家)也总去古玩市场,我们就一起转转,他总是买一些很小的雕件,而且他不大在意真假,他的标准是“喜欢”,他说:“我喜欢就是好。”其实一件物什自己能够喜欢,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和尺度,你想想,能让自己喜欢的东西,世界上能有几样?
我自己在家时,想得更多的是生活。有兴趣了,翻过来倒过去“养”几只禅定杯,看着它们一天又一天在变化,很有成就感,觉得很养心很养神。虽然这篇短文里说的是闲情逸致,但这些话跟诗也未必没有关系。如果有,显然是想通过我的雅好来说:我喜欢诗歌,闲暇时也赏石赏瓷,核心都是两个字:“质”和“变”。物在其质,一生求变。
不仅仅局限于石头或者汝瓷,其实喜欢其他一些什么自然界的东西,都好。喜物但不恋物,喜物但不被物所累,触类旁通,对其他艺术,也许就有感觉了。我原来对玉对瓷也是一无所知(现在也知道得不多),没兴趣,随着年龄渐长,想去了解了,虽然买不起,不一定能得到,但正如我的题为《国之木——题海南黄花梨》一诗中所写的:“也不一定看见,/许多时候,想象就是陶然,/也不一定得到,/许多时候,仰望就是拥有。”我总想,学会欣赏,这本身就是一种拥有,如此,内心甚慰。
2020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