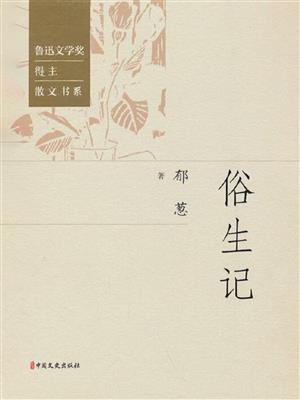端午记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对端午最初的印象,一定是源于粽子。我生长在华北平原一个幽静的小镇,端午在我们那里也被称为“端阳节”“五月节”或者“五月端午”。每到初夏的季节,家家户户都会包各式各样的粽子。粽子一般是三角形或者四角形的,有红豆沙馅、枣泥馅的,更多是直接往里面放两颗红枣,粽子叶也就是比较宽的芦苇叶。先把江米(南方叫糯米)或者黄米(学名叫黍子,一种形似小米的黏米)泡上半天,再一个一个包起来,用细绳捆紧,放到锅里煮,一开始用大火,水开了之后便用文火。江米不好熟,煮的时间会长一些。每当我闻到粽子香味的时候,都盼着粽子快点儿出锅。还有一些年买不到江米和黄米,妈妈就用大米和小米包粽子,那时特别想吃的,就是粽子里面两个很甜很甜的大枣。记得头一年买了新粽叶,吃完粽子以后粽叶是舍不得扔的,洗干净挂起来晾干,等到第二年再用。我还记得妈妈用春玉米叶包过粽子,虽然跟粽子叶包的味道有很大区别,但吃起来依然是那么香甜。
后来,就知道了屈原,那是在我十岁左右读了他的《离骚》之后。当时许多图书是被封存了的,县里的图书馆也长期闭馆。我的父母与图书馆一位阿姨相识,那位阿姨知道我爱读书,经常从图书馆悄悄拿出书来给我读。有小说,像《青春之歌》《红日》《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也有古典名著。当时我读的第一本有关屈原的书应该是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20世纪5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浅黄色的书皮,很淡雅。阿姨给我的时候书还很新,估计是没有多少人借阅过。实际上我当时看《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是不大懂的,但觉得那样的作品很有气势,就把其中我喜欢的段落抄在了日记本上。当然,我更喜欢《离骚》,由于《离骚》是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每每吟诵,都会让我感奋不已。按说十几岁不是理解《离骚》的年龄,但我那时候就感觉,不说它的内容,就是它的音韵,也会让人感同身受,黯然神伤。后来我逐渐了解了屈原,也更多地理解了《离骚》,并且喜欢上了写诗。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叫杨广达,初中老师叫倪洪寿,他们都是语文老师,也都是文学爱好者。当时是不能给学生讲屈原的,但记得有一天放了学,我收了同学们的语文作业(我是语文课代表),交到倪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看到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离骚》,就随口背出了其中的几句。倪老师很惊讶,问我:“你读过《离骚》?”我点了点头。那天倪老师话多了起来,看得出来他有些兴奋,他对我说:“屈原之前中国的诗歌作品多为短诗,自屈原始开鸿篇巨制之先河。《离骚》通篇有两千四百多字,既豪放又抒情,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它抒写了诗人的经历、思想以及空有一腔热血而报国无门的境遇,把抽象的个人品德、政治理念甚至性格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用诗句生动地映衬出来,实际上是屈原生活和心灵的记录,因此也可以称之为诗人的诗歌体自传。而《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向苍天连发一百七十二问,涉及了天文、地理、思想、文学、哲学等诸领域。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那时的屈原身处逆境,放逐山泽,忧心愁惨,他徘徊于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未必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但既然一直被传说,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所涉及的大多是楚国当时的人和事,因此屈原之‘问’,是发自他内心最深处的。这篇包含着屈原思想结晶的《天问》,是他‘呵壁问天’的经典之作。”坦率地说,当时老师讲述这些的时候,我依然还有些茫然,似懂非懂,但从那时起我便从老师的神情中感受到,写诗,一定要有“问天”之作。记得倪老师还对我说:“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我肯定回答是屈原。”这句话,我一直记在了心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人心向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陆续开始解冻,记得最早看到的香港影片就是《屈原》,由著名演员鲍方、朱虹、鲍起静等联合主演,这部影片成为“文革”后第一部在内地放映的香港电影。当时是省文联发的内部电影票,电影在石家庄八一礼堂放映。那天的八一礼堂座无虚席,那场电影的放映时间比较长,深夜走出影院时,脑海里依然回荡着影片插曲《橘颂》的旋律。那一夜我失眠了,眼前总是出现那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人形象。
端午还有一个名字,叫作“诗人节”,这就与我有了更多的精神维系。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和理解能力的增强,我也逐渐懂得,在中国古代,能被称为“伟大”的诗人很多,李白、杜甫自不必说,像白居易、李清照甚至近一些的龚自珍等等,也丝毫无愧于这两个字。但我一直以为,其中最为伟大的诗人,应该是屈原。我所说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离骚》《九章》和《天问》,更在于他用自己的文字和身躯留给了中国诗人和文人一种“场”,一种气场,一种气韵,那种气韵塑造了文人的精神和品质并一直延续至今。屈原的气质、行为、语言都太像一个诗人了——活得写得都像一个诗人,勃然大气,飘逸洒脱。而他最终愤而投江,虽让人扼腕长叹,但如果不如此,也就不是屈原了。所以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我觉得何其芳先生评价屈原的一段话也很精准:“《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之后一些年,我几次到湖南长沙、株洲等地采风。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一踏上楚地,竟然感觉这里的每一条江都像汨罗江。2016年5月,我参加诗刊社“青春回眸”活动到株洲的炎陵、茶陵、醴陵等地采访,28日深夜,我独自坐在湘江边,那时候,这条江似乎是平静的、从容的。望着浩浩江水,恍惚中我似乎看到了屈原的身影,那些经典江河淌走了多少光阴和一代代人的命运,也冲刷了多少历史的辉煌与尘埃。屈原,这位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一直深远地影响着历代文人墨客甚至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每年端午,人们必然想起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自屈原开始,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这无疑开创了诗歌写作的新纪元。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他的浪漫是骨血里的浪漫,浪漫里渗透着近乎极致的豪放。这也是屈原成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的原因之一。每每想起屈原我就感慨:时代造就了屈原的伟大,也必然造就我们这一代人的平庸。想到这里,总是一声轻叹。
说到端午,就一定要说粽子。我查了一些资料,历史上关于粽子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粽”字本作“糉”,“芦叶裹米也”。晋代名仕周处所作的地方风物志《风土记》中有“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用角黍,龟鳞顺德”之说。粽子最初应该是用来祭祀祖先神灵的供品,南、北方的叫法也不同,古时候在北方称为“角黍”,因北方产黍,用黍米做粽,角状,故称“角黍”。南朝文学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叙述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遂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从南北朝以后,民间开始有粽子源于百姓祭奠屈原的说法,说是当年屈原不甘国破家亡,愤而投身汨罗江,之后,百姓莫不感叹哀伤,空有一腔抱负的屈子就这样以一种决绝和不甘离开了楚地,让人悲愤不已。百姓为了避免鱼虾侵食屈原,纷纷将米粮投入江中,期望这些米粮能使鱼虾饱食,而不至于伤害诗人的躯体。亦有古书记载,屈原投江后托梦给百姓,米粮投入江中之后,大多被江中的蛟龙所食,如果用艾叶包裹,再绑以五色绳,则可以免遭蛟龙吞食,这便有了后来的粽子。另有民间传说是另外一种阐释:包粽子实际上暗示屈原是被捆绑着抛进江中害死的,而并不是自杀。关于粽子的传说还有很多,我的姥姥大字不识几个,但她很有智慧,经常给我讲一些民间故事。记得她给我讲的有关屈原的故事是:“很久以前,楚国有一个大官叫屈原,因为他生性耿直,不说假话,得罪了楚王,就把他贬了官,流放到乡下。那些年大旱,百姓饥寒交迫,食不果腹,他便用积攒的钱买了地,种了稻子,有了收成之后便蒸米饭分给当地的百姓吃。但饥民众多,饭碗不够用,有一次他顺手摘了几片芦苇叶,把米包起来蒸熟送给乡亲们,味道居然特别好,大家纷纷效仿,从那时候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以后的粽子。”这当然和传说中的故事完全不同,但都是百姓对粽子由来的不同演绎。姥姥在故事中也没有提到屈原之死,我想那是人们一种善良的愿望:期待着好人永远都活着。民间流传着不知道多少这样的故事,无论故事的情节怎样,但大多与屈原有关。
以后我逐渐知道了,端午节不仅仅是粽子节,知道了其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左右朝政,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等人深知屈原的才华,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而楚怀王庸懦昏聩,不辨忠奸,听信谗言,屈原逐渐被疏远。这对于饱含政治抱负的诗人来说,的确有些残酷,以致屈原在无奈之中,只能感叹世事的不平。当时秦昭王提出秦楚两国联姻,并借此提出与楚王会面,屈原看透了秦昭王此举实为一计,于是极力谏阻:“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而楚怀王之子子兰却力劝其赴秦:“奈何绝秦欢?”楚怀王终于听信了子兰的话赶赴秦国,结果被秦昭王扣下,直至客死于秦。其长子顷襄王继位后,子兰仍然不思其过,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使得屈原只能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达九年之久,远离故国,对国家、宗族之事无可奈何,只有悲伤、悲叹而已。眼看着“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自知国破,悲愤难挨,遂自沉于汨罗江中,以忠贞之躯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理想。
应该说,这样的逆境又恰恰成就了屈原诗歌的风格,使他在空有一腔热血而不得其所的情形之下纵情高歌,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愤懑。其实,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有政治情结,这大概自屈原始。政治使得屈原成为一个生命的悲剧,但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之成为最具有中国诗人独立、入世、率真等典型特征的文人形象。我觉得,在生命和诗歌这两点上,屈原都走到了极致。屈原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他还在自己的诗篇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其中尤其以揭露楚国黑暗政治的篇章更为深刻。
现在回忆起来,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就与端午有关。1981年6月,河北省作协和承德地区文联在山城承德联合举行了“端阳诗会”。当时许多老诗人都还在世,会上,著名诗人田间、曼晴、流沙河等着重就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倡导新诗发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做了发言。那是改革开放以后河北省规模最大的一次诗会。我们那批相对年轻的诗人思想活跃,当时我和边国政住在一个房间,他刚刚获得了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1979-1980),我们更多探讨的是诗歌如何在借鉴与继承之间找到一个最佳路径。那些天,望着避暑山庄的夕阳夕照,听着外八庙的暮鼓晨钟,我有了许多感慨,于是写下了散文《端阳落日》。那篇散文虽然不长,只有三千多字,但凝聚了我对现世及诗歌本身的思索。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又找出当时发表《端阳落日》的那一期刊物,重新再读,虽然文字有些稚嫩,但依然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一个年轻人的理性和激情。
屈原当时为三闾大夫,担负着教育贵族子胄之责。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可谓“尽职尽责”,为培养贵族的后人呕心沥血,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倾尽心力培育的那些贵胄,最终竟然成为自己思想的反对者,这是他从情感上最不能接受的。屈原政治理想的内容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信奉的是民本思想。他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等,颂扬古代的贤臣,他想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对国家的危险性。“彼尧舜之耿介兮,既尊道而得路”,“耿介”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期待。所谓贤臣,就是主张楚君要用品德高洁之人。屈原说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词。屈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涵盖下,真实、正义、不屈服于邪恶,“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显然,他的这些思想虽至纯至善,但恰恰是孤独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一个诗人的理想主义,最终要么毁掉身躯,成就文字,要么身躯和文字都被毁掉。
2016年6月8日,从湖南采风回来不久,记得那个傍晚霞光横溢,不远处的太行山若隐若现,如诗如梦,在那个瞬间我似乎有了诗兴,于是写下了一首《端午记》,其中写道:“端午的时候,灼日寒夜,/三山风薄,一江水远,/日叶正阳,时至仲夏,/端午称为天中,/然而无天。//这一天,一位诗人死了,/死过那么多的诗人,/只有他,死得地冻天寒。/他顺着沅江,向长沙走,/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自知国破,遂自沉于汨罗江,/他死了。/我不想评价那个年代是好年代还是坏年代,/一个诗人以这样的方式死了,/它就一定是一个悲惨的年代。/但这样的年代会被人记住,/它摧残了屈原,也造就了屈原。/我们想象那一夜血雨腥风,乌啼猿啸,/然而不是,那一夜没有声音,/那一夜之后,再没有了声音。”是啊,再没有了声音。那个年代的喧嚣与静寂,都是那么极致。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我想,端午,这个节日是因为一个人,在中国,似乎只有这个节日是因为一个人!那半月的夜晚,我觉得屈子离我很近,沅江的江水,有隔世的微凉。屈原曾经写道:“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我相信,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并不大,甚至是缓缓的,他显然是想说:我试试,我撕不碎这黢黑的幕布,就被它撕裂!然后,我接着写:
今天没有风,风这个词本身就很冷冽,
叹沅江之空渺,
悲楚地之干枯。
哪个时代也没有缺少过写诗的人,
但是缺少用身躯撞门的人,
缺少清醒理性、欲求寡淡,一直用血写诗的人,
我不是,我这一代人,
都不是!
时空博大,人渺小虚无而且瞬间,
记起来2016年的时候,
我站在湘江边,想无论这条河是涨满还是干涸,
从远处看,它都平静。
大江大河知道什么时候放纵,
也知道什么时候回头,
不急不缓就浩荡成了经典。
所以,每当看到湘江的时候,
我就强迫自己想:世界是干净的,干净的。
但是不是,但是不是!
这是这个世界的痛点,触碰不得。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遂去,不复与言……
何问地?何问天?
天地乃不变的天地,
江水为不息的江水,
路漫漫,路漫漫兮……
我在湘江,看高天明月,
竟然依旧是几千年前的模样。
屈原是中国诗歌史上真正走向民间的一位诗人,在他去世后,人们包粽子、赛龙舟纪念他,这种影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企及的。我曾经在湖北江汉地区观看过赛龙舟,当时觉得异常震撼,让我想起来自己的家乡场面宏大的舞龙舞狮。后来我知道了舞狮也有南派北派之分,但在我眼里,都是那么风云壮阔。那时候,看着龙舟疾驰,听着鼓声猎猎,就想起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九章·涉江》)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上,鲜有屈原如此恢宏大气,飘逸洒脱,若他的结局不如此,就不是屈原。惊天之问,忧心愁惨,徬徨山泽,诗人叹沅水、湘江、汨罗,看天地、贤圣、灵异,潇湘九年苦雨,空有一腔高歌。是啊,我一直觉得,真正具有屈原那种精神气度、个性品质、政治抱负、艺术探寻的诗人,不多;如果有,那他也必定是伟大的。
2023年端午,我是在滹沱河边一个静谧的村庄度过的。那天晚上,万籁俱寂,群星璀璨,我感觉,天上闪烁的每一颗星辰都是一位逝去的故人。那时我细数着或者绮丽耀眼或者若隐若现的星星,不知道哪一颗是我心中那位伟大的诗人,这时候,风声松声,暮鼓磬音,融入滹沱河水轻叹一般的音韵,厚土苍茫,一瞬间穿越了岁月千年。
2024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