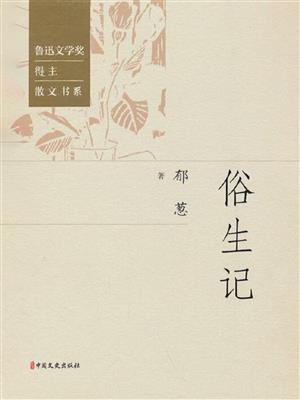人间忽晚
这几年,在诸多节日中,我又多了一个节日:重阳节。每到这个节日,许多朋友便发来信息,那时就让我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已经老了?也有朋友在“六一”那天给我发信息,我知道,实际上这与重阳节发信息的含义是相同的,虽然心理上还不大接受,但毕竟步入老年了。在中国的传统中,父母健在,是不能说自己老的,我的父母都九十高龄了,身体还都过得去,有父母就觉得自己年龄还不算太大,所以前两年我在古玩市场看到一个和田玉老寿星雕件,品质、品相和价格都合适,但我想起那个不知道谁告诉我的习俗:父母健在,身上就不能戴寿星,所以便放弃了。前几年在公交车上还没有人给我让座,这些年有了,因为都戴着口罩,其他人看不清我的面容,我知道一定是自己的某种神态或是动作已经显出了老人之态。是啊,不经意,就老了。那些旧日子,成为粗糙的经历中光斑一样的沧桑。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便是重阳节,“九”这个数字在《易经》中为阳数,“九九”两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因日与月皆逢九,故又称为“重九”。九九归真,一元肇始,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祈福、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习俗,传承至今,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便承载了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重阳节源自天象崇拜,起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之后。史料考证,上古时代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就有祭天祭祖,以感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这是重阳节作为秋季丰收祭祀活动而存在的原始形式。由于在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重阳登高习俗源于此时的气候特点以及古人对山岳的崇拜。重阳节前后的这些天,清气上扬,浊气下沉,菊黄叶盛,无边无际,这时候登高处而望远,便是对年迈的前辈寿如高山的期盼。这一天还放风筝、插茱萸、赏菊、踏青,由于其时秋色斑斓,百果丰实,所以重阳节的内容异常丰富。
一
重阳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的一些习惯和心态的改变。年龄大了,离开编辑部之后,有了很多闲暇,偶尔与朋友们聚会,年龄相近的朋友居多,大家聊得最多的除了艺术圈子里的旧事和艺术本身,更多的是谈酒、谈玩、谈雅兴。我这辈子一滴酒也不喝,也不怎么会玩,朋友知我,说:“郁葱就知道发呆、散步。”我说:“还鼓捣我那些不成不就的文字。”不是文字不成不就,是我自己不成不就。说到散步,这成为现在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早中晚各走三千步。十几年了,风雨无阻。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锻炼身体和休养生息,现在却很在意,这只能说明自己老了,在意自己身体的感受了。我的骨子里有一种刚硬和坚韧,追求至善至美,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做正事时是这样,做闲事时也是这样。朋友问,闲事也有必要往最好里做吗?按道理讲,闲事是闲散状态中可做可不做的事,做闲事是为了换换心情,调整情绪,没有必要太认真。但有时一个人的习惯一旦形成了,就渗透到了骨子里,无论是做正事还是做闲事,其实都有一种性格融汇在里边,比如散步。早年在编辑部的时候没有时间散步,记得《河北文学》的老主编肖杰对我说过:“当编辑一定要注意眼睛,一定要注意大脑,职业病,就坏这两个地方,坏了眼睛就失明了,坏了大脑就失眠了。”结果这两点都被我染上了。工作其实是一种惯性,长期在一种惯性里,反而不容易出什么问题;一旦松弛下来,可能身体某一部位就会不适应。比如眼睛,做编辑的时候,一直没有什么问题,看了大半辈子稿子也习惯了,松弛下来以后,突然就视网膜脱落,看这个世界就很模糊,但时间长了也就接受了,满足于这种模糊,不愿意把尘世看得那么清晰,觉得那个清晰的世界反而更加陌生。为了让身体尽可能保持一种还过得去的状态,于是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散步。
刚开始散步的时候,追求一种超量的运动,上午走七八千步,下午和晚上又各走七八千步,每天行走的步数超过两万步,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觉得疲劳,腿关节也不舒服。什么事情一旦超量,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之后便开始找规律,我是一个规律感、规范感非常强的人,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些程序,这些程序是必须完成的。散步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即使刮风下雨,即使偶有小恙,也一天不间断。散步会让人感觉身体明显舒展开了,如果哪天没有出去走走,便觉得浑身不舒服。我做许多事情是因为其中有乐趣,原来不觉得散步会有什么乐趣,慢慢体会到了其中的味道,觉得再也离不开它了。而且散步也不是纯粹为了锻炼身体,一边散步一边回忆一些旧事新事,感觉有用的就用手机记下来,所以我爱找一些偏僻的小路走,每天走的总是这样的路线。走一个小时也不觉得时间长,想着想着就过去了。遇到一些长辈,就跟他们聊天,觉得许多时候他们叙述的不是生活的经验,而是命运的痕迹,命运的痕迹才那么真实。原来觉得老人们琐细,现在想,他们琐细的生活才是智慧,而且后来发现,不过是时间早晚,我走的路,跟他们基本相同。我曾经坚信我的神态和步态不会老于他们,但后来知道,我比他们还沧桑。
天气好的时候,小区的树荫里总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阿姨(还有两位坐在轮椅上)在一起唱歌,一开始是《一条大河》,后来是《九九艳阳天》,有的也不在调上,阿姨们边唱边自嘲地笑着。也许这些老人一辈子有千般烦恼,但这个时候她们是忘我的。散步到那里时仔细看了她们一眼,竟然在想象着她们年轻时的模样。我知道她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过去,想到她们那些曾经鲜灵、清纯的年华。这岁月,这时光,一代代老去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那时候看周围的树,有的叶子枯黄了,有的还嫩绿嫩绿的。人与这些植物,就这么冬寒夏暖地循环。散步的时候还总遇到一对老夫妻,他们手里拄着拐杖或者推着老年车慢慢踱步,有一段时间老奶奶已经走不动了,过了些日子,她竟然甩掉了拐杖。虽然没有打过招呼,但看着她一天天好起来,从心里为她高兴。朋友说,看你的微博里很多时候说到老人和孩子,我说:“是啊,每天早晨看到路边蹒跚的老人和匆匆的孩子们就觉得,人这么多年,最值得说的就是老人和孩子,说老人说一些经历,说孩子说一些纯真,其他的,又有什么值得可说呢?”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小区散步,偶尔听到路边三位老者的对话:“兰兰还在吗?”“兰兰?”“就是中文系的那个兰兰,孙亚兰。”“还在还在,不在石家庄,跟闺女去珠海了。”“王自蒙呢?还在不在?”“王老师不在了。”“张老师呢,就是那个张云启,课讲得好的那个张老师。”“不在了,有好几年了。”
“也不在了?他也不在了?哦,张老师也不在了……”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之后,我回头看,猛然觉得,夕阳下老人的身影,像一幅沧桑的油画。
年龄大了,更喜欢那些平实、平静、世俗甚至有些平庸的生活,每当走在并不宽敞然而生活气息很浓的街道上时,内心会有欣然和满足的感觉,觉得这才应该是真正的人间。不喜欢高楼林立、灯影交错,不喜欢车水马龙、人声嘈杂,所以在城市里如果有一条很安谧的街道、很幽深的胡同,便觉得与自己的内心很契合。有时候,披着傍晚的余晖走在石家庄的水产街、青园街、维明路,竟然有了几十年以前的感觉:路边卖粉条的、配钥匙的、卖干果的、炸油饼的,等等,一幅幅简单而又亲和的生活场景,让人觉得其实生活不一定非要那么多的深奥和玄奥,你觉得踏实,就正好。那时会记起一则寓言:“一些人往前走,一个老者总是停下来,别人问为什么,老者说:‘不着急,我要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老人是智者,能够“等一等”的人,你看吧,他其实会一直走在前面。于是我总想,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的大事并不多,那就做一些琐事,比如给老人让让路,跟孩子说说话;比如说真话,不狂傲,不自夸;比如把废报纸留给捡废品的人,在楼道里遇到不熟悉的邻居,微笑着点点头;比如在超市别把货品翻乱,不把宠物的污秽留在路上;比如天气肮脏时,别让自己心里也生霾……若如是,则幸甚。
散步时,常常惊叹于那些草的生命力,无论它们是深草还是浅草,每年总会生长;惊叹于许多北方阔叶树的生命力,每年冬天,它们被锯得只剩下了躯干,来年春天,重新长出的枝杈照样蓬勃。所以年龄越大越觉得,人不如草,不如树。散步的时候,我爱迎着太阳走。朋友们说:“你晒黑了。”我说:“大半辈子都太白了,太干净了,黑点儿就黑点儿,也算是一种平衡。”最松弛的时候,应该是和两岁的孙子小布丁一起在石家庄裕西公园散步,那个时候,什么世间俗事,什么人间冷暖,在大脑中都不存在了。带着孩子看着那些树、那些鸟、那些草、那些叶子,跟他在一起跑起来、跳起来的时候,完全忘记了年龄,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孩子或者成了一个真正的爷爷,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忘情与忘我。“早冬的上午,我推着婴儿车,/跟周岁的布丁在裕西公园散步,/看着他天就干净了,/天、地、人,什么都干净。/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和我的身上,/在那个瞬间,/我竟然觉得,/普天之下,尽是孩子。”这是我当时的心境,真实而纯粹。我真心觉得,散步是一个老之将至的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散步的时候会觉得,这大半生的长长短短、起起伏伏,就这样被一步一步地丈量出来了。我说过,写诗就是写自己,那时候,我在内心重复着自己写过的那些文字:大江大河知道什么时候放纵,也知道什么时候平和,不急不缓就浩荡成了经典。这冷暖人生,亦是江河亦是浅草,如沧海时,如桑田时。
二
重阳的时候,我会去看望一些老人,朋友们有时问我节日期间做什么,我总是说:“看年长的人,串闲适的门,写散淡的文。”去看望老人会感受到他们需要你,跟他们聊天,会觉得我的以前和以后都会有他们的影子。去年重阳节去看望几位老编辑老同事,觉得他们满肚子的故事,满肚子的想法,满肚子的学问,但大都没有写出来,那都是诗史文史啊。还有一位长者,他阅历丰富,坎坷曲折,经历了战争和历次运动,饱经沧桑,但他只对我讲过一些片段。我问他有没有记日记,他说没有,一是工作忙顾不上,二是在那个年代写日记是一件不大让人踏实的事情,所以他和他那一代人写日记都很慎重,或者干脆就不写了。后来那位长者去世了,他传奇般的经历也就随之消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一部独特的心灵史和生存史,让我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很可惜。那时我就提醒自己:世事嘈杂,人生匆忙,要离世俗远些,离即兴远些,离当下远些,离这个圈子远些,不一定非要成就什么,记着每一天写几个字,足矣。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激情,有的时候就写,别丢了。
记得我去看望著名作家徐光耀先生,老人九十多岁高龄了。徐老早年经历了战争,那么多年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与痛楚,但他的内心一直无与伦比地坚韧和刚硬,疾恶如仇,泾渭分明。清楚地记得2006年11月在全国第七次作代会上,我在走廊里陪他散步,谈到写作的时候,老人一边走一边对我说:“遇到使自己心动的东西,格外用一些心,格外用一些情,格外用一些笔墨。”这么多年,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后来他在几个场合也说过这句话。徐老是一位博学多识的长者,有着骨子里的自信,不急不躁,有很节制的温和和内敛。这是有底蕴的心性,是定力,是境界,所以才有大作品,徐老七十四岁写出了《昨夜西风凋碧树》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去看望徐老的时候,老人敏锐智慧,对世间万象有着极富穿透力的洞察和彻悟,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宛若洪钟,典型的文人形象,实实在在是一身正气。听我讲述了一番近来写作的心态之后,徐老对我说:“那些世俗的功利,对于你都无所谓了,不要急,不怕时间长,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写出一些能压得住心的作品。”“能压得住心”,这几个字,就成为我后来写作的基本尺度。
还记得有一年重阳节,我去看望书法家、诗人旭宇先生,先生正在抄录《呻吟语·品藻》:“读书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学识,甚气度,甚作用。汉之粗浅,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见三代以前景象?真是真非,惟是非者知之,旁观者不免信迹而诬其心,况门外之人,况千里之外,百年之后乎。”我对旭宇先生说:“这幅字归我了。”遂钤印入囊。像《呻吟语》这样的典籍,读一遍是古人的思想,读两遍是入心的悟语,读三遍就成了自己的感受,有时间了,我就再读三遍。晚年的旭宇,八十多岁开始画画,画画其实也是在画境界、画品位、画内在的学问,所以他的每一幅画都注入了纯粹属于艺术的个性化思维,渗透出一种安详、平和心态下的深度。晚年的旭宇是一位把世人和世事悟透了的贤者,他更加相信天人合一,更加相信顺天应人,也更加相信万事万物皆由天定,因此就更加内敛、温和、超然、智慧,性情显得非常润泽。旭宇先生曾经送给我一幅刚刚画就的山水画,清秀的山影,平静的水面,那种闲适和恬淡,与旭宇先生当下的心境相当吻合,渗透了悲天悯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
老一代的坚韧、真诚和善良是天生的。记得2015年春节前夕,我专程到北京后海看望田间先生的夫人、作家葛文阿姨。快到北京的时候临近中午,我给葛文阿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一会儿就到,没想到路上堵车,一直到将近下午一点才赶到后海北沿葛文先生的家门口。没进胡同,远远看见老人在胡同口站着,老人见到我说:“放下电话我就出来等,等着你来。”当时我眼泪快掉下来了,老人当时九十四岁了,天那么冷,竟然为了等我们在胡同口站了一个多小时。回石家庄的路上我一直懊悔,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提前给老人打那个电话。在葛文阿姨的家中,老人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起了田间先生和省文联、省作协的一些往事和今事,说起了她在意的事、她惦记的事,有的让我感慨,有的让我惭愧和动情。
窗外有一棵有些年轮的树,北方的树在冬天就显得沧桑和孤单,那些枝杈挺在那里,乍一看像是干枯了,但根基扎实,有恒久的底蕴,它们是在默默酝酿着生机。一年一年,这些树有时候成为景致,也有时候成为冬天里内在生命的象征。重阳节时,想起一些老人的时候,就会想起一棵古朴苍劲、枝叶繁密的百年大树。
三
重阳的时候,愿意跟父母在一起。父母都九十多岁了,身体还好。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记得原来叫河北财经学院)。他在银行系统工作,早年一直顺风顺水,很快做到了银行的中层。我小时候去他的办公室,看到墙上挂了一张很长很长的照片,那是他在北京参加金融会议的时候跟当时领导人的合影。他让我在密密麻麻的人中找到他自己,那张照片有几百人,我居然很快找到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做了一个小官员,由于他生性倔强、执拗,个性鲜明,跟那个气场很不吻合,所以从此在工作上总是磕磕绊绊。早年他喜欢舞文弄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蜜蜂》杂志、《河北日报》、《大公报》、《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不少小说和散文作品,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文人的情怀,反而影响了他的仕途。
我同院的发小现在是国外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前年春节回石家庄专门去看望我的父母,他也回忆起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多读书,不做官。”父亲对同院和我一起长大的其他孩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后院住的是机关干部,前院住的是城镇和农村居民。那个大院里的孩子中,有的成了国际上著名的学者,有的成了行业里的精英,但走仕途的很少,这应该是受到前辈们一种精神涵盖和影响,形成一种恬淡、从容的生活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了,就会转化为性格。父亲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宁可乞讨,不说假话。”这样的性格与那个时期的氛围是有差异的,所以他很多年忙于具体的事务和工作,丢了创作,这在他内心一直引为憾事,也就不再纠结仕途的明朗与黯淡了。由于当时“文革”时期的大环境,父亲觉得我还是个孩子,是很限制我读书的。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春节回老家深县(那时为了省钱,我和父亲是骑着自行车回家的,一百多里路),我滔滔不绝地对他谈了一路,谈我读过一些文学作品之后的感受,他不说话,就那么听着。我参加工作之后有一次聊天他才告诉我,从那时起,他知道再也挡不住我对文学的热爱了。他说没有想到我看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并且有了自己的理解,从那时起,他不再阻止我阅读文学作品。还有,虽然父亲当时不赞成我读文学书籍,但他鼓励我读纯美的文学作品。他说文学的功能之一是给人美感,很诗意的作品一定容易让人接受。它不繁复、不芜杂,简单而明澄,这样的故事、情境和思想对于一个开始成熟的孩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前年有一天天还很早,父亲就打来电话,说是辗转难眠,写了一首诗。他读给我听,旧体诗,合辙押韵,格律工整。我对他说:“有几分深刻,但是未必能发表。”父亲说:“没有想给别人看,八十多岁的年龄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没有发表的想法了。”记得那天早晨接到父亲的电话,便不由自主想起了这些旧事。父亲说年龄大了,眼睛看不清,很多字也写不准确了,但我觉得,每当谈起往事来,他的思路就渐渐清晰起来。父亲还曾交给我几张一分、二分、五分的纸币,很新,看起来是刻意保存的,它们已经没有了实用价值,只是那个年代的记忆和痕迹。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没有实用价值的时候比有实用价值的时候更值得珍视。还有几张那个时期的粮票,也是新的。这些我都用过,有的记忆还挺深刻,但这些年渐渐都淡忘了。再看到它们的时候,有一些陌生感和同样多的异样感,是一种沧桑阅尽、恍若隔世的感觉。
又到重阳节了。岁月久矣,老成了山脉,老成了江河。我在夕阳下,像一条年迈的河流,青野碧绿,蝶蜂飞舞,一道折光,辐射在太行山的缝隙。苍天恩典,晚秋丰盈,那是因为我爱:爱人,爱己,爱红尘,爱着善恶冷暖、阴晴黑白,我从万物身上汲取光华。我昂首了一生,而今年迈,便匍匐下来,不看高处:不看太阳和月亮,它们的灿烂,离我渐远。我亲吻草根败叶,覆土尘埃——那曾经被我忽略的另一个世间。夕阳如晦,然千年不堕。这时候我想:其实直到老之将至,我们也未必知道怎样面对这博大的世界,如同我们未必知道怎样面对自己微小的内心。记得在对年轻作者们谈创作的时候我说:“无论如何,给这个世界以美好。”是啊,天地循环,无尽无穷,迟暮了,亦有迟暮时的美好。红尘浮若羽,一年再一年,这时候,我看着自己夕阳下无言的影子,溢满风尘。
202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