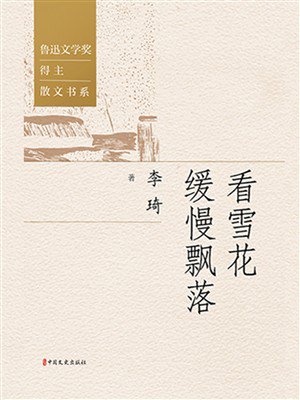《嘎达梅林》与马头琴
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与同名的马头琴曲,我可谓百听不厌。低回浑厚的旋律,简洁朴素的歌词,每次都能伸出手,把我一把拽住。在这样的旋律里,我有种说不准是在下沉还是上升的感觉。我尤其喜欢《嘎达梅林》这支马头琴曲,经常是循环地播放。深情舒缓的琴声雾霭般地弥散。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带着犹如前世的召唤,能让我陷进一片冥想和怅惘之中。
嘎达梅林,一个属于茫茫草原的英雄,正像歌里唱的那样:他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勇敢地反抗王爷和军阀,反抗掠夺和欺压,反抗扼杀人性的权利。最后,英雄末路,嘎达梅林在战斗中献身了。草原上的人民情深意重,他们深邃的目光能辨别是非真伪,厚道的心肠也铭记功德恩情。于是,茫茫草原上,一代又一代的蒙古人,一边拉着马头琴,一边传唱英雄的故事。悲壮的歌声和琴声,像百灵鸟的翅膀一样,飞遍草原的每一个角落——“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歌声忧伤,沉郁,往远处飞,往肺腑里去,带着草原人的心事,一代一代心口相传,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诗。
我曾在内蒙古草原的深处,在一个蒙古包里,听过牧人低声地唱过《嘎达梅林》。
那个傍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里弥漫着草原独有的清香。刚刚喝过酒,那个原本有些羞涩的牧人,就像要开口说话一样,低声地唱起了这支歌。适才还谈笑风生的同伴全静默了。我使劲低下头,因为我实在无法控制奔涌而出的泪水。我相信我听到了整个草原的声音——蜿蜒河水和蓬勃青草的声音;骏马和牛羊鸣叫的声音;古铜色面庞老阿妈的声音;一顶顶栉风沐雨的毡房接住雨水的声音——我还相信,那个叫作嘎达梅林的人,正在以草原人特有的步态,顺着这歌声向我们缓缓走来。他已经从牧人变成了神。我们看不见他,因为我们不过是这里的过客,可是草原人的眼睛能认出他来。我一下子理解了纯正的蒙古族人为什么气度那么安详。他们勇敢、宽厚、慈悲,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坚忍地生存,彪悍的外表下藏着善待一切生命的柔软心肠。他们是唱着这样的歌,听着这样的琴声长大的。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是嘎达梅林的族人,是有着遥远来路和开阔背景的人。他们经受的苦难,他们肩上的风霜,他们骨子里的贵重和悲伤,都赋予了草原歌声与琴声独特的精神内涵。
马头琴是孤独的乐器。即便是在众多乐器的合奏中,它卓尔不群的音色和魅力依旧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当它被怀抱在有心灵的演奏者手里,它的弓弦就好像通了灵,如倾诉如呜咽,或婉转或醇厚,弓弦好像连着整个草原的魂魄和心事。马头琴曲《嘎达梅林》,我听了无数遍,无数次被打动。那种千回百转,那种对于英雄的疼惜和命运的咏叹,那种草原文化的独有的深情和悲怆,那种无边无际的内蕴,常常让我百感交集。
2007 年,我有幸在前郭尔罗斯草原听到六百个孩子演奏马头琴。当六百把马头琴平地响起的那瞬间,我真如受了内伤一样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原想拍几张照片,可是手一直在抖动。我后来用诗句记录了当时的感受——六百匹草原的马驹/突然一起说话/倾诉又如召唤/那小小的演奏者/好像远古的神灵附体/端坐于土地/灵魂却腾空跃起/在云头之上/六百个孩子的血液和骨骼/来自草原和遥远的祖先/六百把动人心弦的马头琴/六百颗穿蒙古袍的星宿/六百双未染尘埃的手/从琴弦上伸来/为我黯淡的日子/拨亮了,六百盏灯。
那一刻真是太难忘了。当天骄阳如火,整个广场,却迅疾弥漫起一种苍凉之气。那原本还是顽皮的孩子倏然间神情庄重肃穆。琴声唤出了他们基因里的草原情结,把他们带进了祖先的故乡,带进了苍茫悲壮的往事里。六百把马头琴的声音和六百个孩子充沛的元气,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气场,让人不由得屏住呼吸。一种时空倒转的感觉,让我仿佛进入了幻觉。我觉得我也在那琴声里变成了一个蒙古族女人——心神安稳地日出而作,眼前是目光清澈的孩子,身边是安静的牛羊。逐水草而居的毡房里,永远有为亲人煮好的热茶——而那些从小就熟知嘎达梅林故事的男人,正在骏马的背上,在辽远草原的夕阳下,如剪影般让人怦然心动——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朴素里包裹着深邃。英雄嘎达梅林,住在歌声和琴声里的嘎达梅林,让我对一个民族心怀敬意。这歌声这琴声,让我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千变万化,无论有多少花哨和名堂,那直抵人心的艺术,永远来自真纯之地,来自博大的襟怀,来自如今已被我们逐渐忽视的两个圣洁的汉字,那就是——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