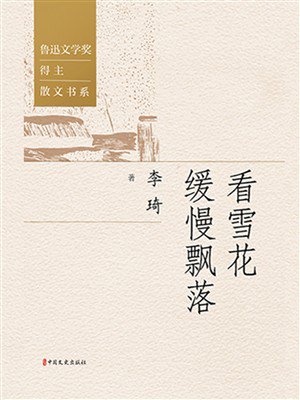歌王远行,世界心动
6 月 26 号那天,一打开电脑,看到迈克尔·杰克逊逝世的消息,头皮一麻。真的吗?急症发作,911 呼救。这些常人的事情怎么会和他有关?难道是真的?!就像一首歌的结尾那样,音符消散,戛然而止了?迈克尔·杰克逊,从此,这世上真的就再没有你了?
我非常难过。
我的周边同事,都是比我年轻的人。对于这骤然离开的天王歌星,显然没有我这样的情感波动。我也不愿把这些个人化的心事,动辄向谁诉说。
连续几天,心绪不宁。我翻出保留下来的那些盒带和碟片(搬家数次,盒带成纸箱扔掉,还是舍不得扔掉当年最喜欢的),先是看到中唱总公司上海公司 1988 年版的《BAD》。封面上的杰克逊,是他所有形象中我最为喜欢的——一袭黑衣,金属袖扣闪亮,黑卷发,黑眼圈,面庞纯洁英俊,眼神反叛,英气逼人。鼻子一阵发酸,这么大岁数了,不愿和谁再说起这些。我给在北京的女儿打了电话。我说,你能理解妈妈,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杰克逊死了我这么难过。到底是我的女儿,她说,其实她也很难过。
杰克逊是占据我重要记忆的一个人。他是我青春时代的一个符号,是遥不可及却和我的生命有所牵连的人。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一所体育学院当中文教师。刚出校门的我,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甚至比那些功成名就来镀金的学生还要小一些。哈尔滨是时髦之城,体育院校自身具备的活力,又特别容易使之成为接受新鲜事物的所在。年轻人本身具备的反叛激情和彼时正当红的杰克逊一拍即合。我记得当时学生宿舍里随处可见他的肖像。学生中有些运动员,经常出国比赛或训练,带回了他演出的录影带,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传看并模仿。那时真是把能搞到的他的演唱会录影看了无数遍。学校里有现成的场馆和现成的艺术体操、舞蹈教师,总有人不厌其烦地示范和讲解杰克逊那些奇妙舞蹈的动作要领。好像那时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响着杰克逊的歌声,都有人着迷地练习着那若有魔力的太空舞(我们当时称为“抽筋儿舞”)。为了让自己跳得正宗,我仗着自己还有点儿小时候练过舞蹈的底子,当学校里跳舞最好的学生到我家来玩时,就忍不住“不耻下问”地一遍遍学习。学生肯定是不好意思说我笨,但真是给人家累得够呛。当年时兴的校园舞会,是释放青春激情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住校青年教师消磨时光的地方。常常是,舞会开始,跳“三步四步”时,气氛还平稳正常,待到音响里杰克逊的音符一滑落,就像一根火柴擦过,燃点顷刻到来。
这时,年纪稍长些、刚才还“三步四步”矜持的老教师们就自觉地悄然退场了。我们则开始在几个领舞者的带领下,一起“抽筋儿”。那真是舞会的华彩部分——大家一会儿机械舞,一会儿太空漫步。男孩子们穿着黑夹克,手上戴着护腕,还有那种露出手指的手套,模仿着杰克逊的神情和动作。尤其是,没有任何口令,某个段落一到,彼此就心领神会,步调一致地或左右移动,或开始向后退着跳。因水平高低,舞姿各有千秋,但集体着魔般的情景,青春的摇晃和尖叫,生命力的迸发,真让人上瘾——我和一些那时的学生至今保持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与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包括喜欢杰克逊),有一些共同的精神密码,是深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夫妇都写诗,我家当年还是一小撮诗人聚会的“窝点”。常有喝得东倒西歪的诗人相互搀扶着半夜来访。那时人际关系相对单纯,一句“我是写诗的”就是路条和身份证。当时来得最多的,是加起来才四十几岁的阿橹和肖凌。他俩都瘦高俊朗,热爱诗歌如信仰上帝(阿橹后来竟能沦为杀人犯,连伤几命,让我至今感到困惑和难过)。肖凌家教优良,艺术天赋好,对音乐的感受力尤其丰富细腻。知道我的喜好,当时并没有多少钱的肖凌,曾买来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的盒带送我做礼物。他到我家来常常是不多说话,两条长腿直奔到当年的双卡录音机前,歪着一头长发的脑袋,一盘一盘地专心听带。他一边听,偶尔还自言自语地评价。我们都叫他“审带的”。
记得我和肖凌、阿橹一起讨论过杰克逊。我们都喜欢他歌声里的纯净和激情(肖凌对于杰克逊,当时已经深为迷恋)。娱乐界歌星在歌声里不倦地关心地球和人类,对我精神和灵魂的震撼,杰克逊是唯一的。黄昏时分,光线柔和,我三楼的家中,窗前一棵老树枝叶婆娑。杰克逊独特的声线,使房间里弥漫着奇异的气氛。这歌声有时柔美灵动,像个没长大的女孩儿,如泣如诉,听得让人心疼;有时高亢激愤,带着利器般的尖锐和颤抖的神经质,让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听他的歌,特别像中了蛊,血液的流向好像都改变了。那感觉一言半语还真是难以概括。
我还记得最初看他录影带的情景,我真是被惊着了!用奇思妙想来形容,简直就是侮辱了他!如此惊世骇俗的视觉奇景,让我一时半会儿竟缓不过神来!那种经验之外的想象力,对我是巨大的冲击。准确地说,看得我一惊一乍,甚至有些毛骨悚然。他怎么想出来的!那些异想天开的制作是怎么完成的!那真是流行音乐的巅峰之作。杰克逊的每一个细胞都与众不同,他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是一个只能仰视不能抵达的天才。我忘了彼时歌王和我年龄相仿,也不关心他脸上的改造工程和正在逐渐由黑变白。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特异之人,用他的歌声和舞姿,用他对于美几近绝境的追求,丰富了我的青春时代。他在遥远的美国,关照了我的内心生活。
这些都成为往事了,随着歌王变成更大的传奇,我们的生活也日渐滑向平淡和正常。阿橹被判极刑离世,肖凌如今已是举止沉稳、声名赫然的董事长。而我,则鬓有微霜,已然迈进天凉好个秋的生命段落了。很久不听杰克逊了。他作为一个符号,已逐渐沉淀在心念之中。每每听到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心里都不舒服。我早已在这个世界还他清白之前,认定他的干净。我记得他这么深,是因为和他相关的那些日子,是那么丰饶而值得回味,他是熟稔而陌生的朋友。他的歌声和舞步美丽过我的生命,他的光芒照耀过我的岁月。
现在流行说自闭,天神一样的巨星杰克逊其实才是真正的自闭者。他面向世界,关上了自己的门。这个五岁起就被迫出来卖艺的孩子,从小失去了童年,失去了安全感。父亲的粗暴,种族的歧视,无处不在的陷阱,身边太多的野心、算计、欺骗和背叛——这些生活河流里最险恶的暗礁和险滩,竟无一遗漏地撞击着他的生命之船。这个看上去绚烂至极、以歌唱为生的人,吞咽下了太多的苦楚和辛酸。我看到面对著名的奥普拉“你是不是一个处男”的提问时,他还可以声音轻柔、羞涩却不失优雅地回答“我是一个绅士”。但是,更多的时候,作为公众人物,他无法巧妙或从容地回应。云端之处的心思无法完成和滚滚红尘的对接。他的才华,他谜一样的生活,他的奢侈和华丽,他的肤色和面容,他的孤僻和怪异,他一次次经历的诉讼和难堪,让他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话题。世界的不负责任,让纯真的他没有隐私,没有退路,茫茫人海,孤独求败。
杰克逊一生痴迷舞台,因为只有在舞台的灯光下,他才是骄傲的王子,是绚烂与光明的统领。歌舞之中,他能让自己释放出无边的能量,具有笼罩一切的迷幻气场。他的每场演唱会都有种让人中毒一般的魔力。上万人如醉如痴,总有激动得晕倒的歌迷被抬出去。而这舞台之神的感觉,能帮助他暂时忘却舞台下的冰冷和黑暗。可演出总是要结束的。舞台之下,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小事——他与孩子的亲昵,他不断变形好像就要融化的脸,连他的内衣,他吃过什么,他用过的垃圾,都逃不过别人的追踪和分析,他成了整个世界的消费品。他的生活在没结束时就已经支离破碎了。
现在,那颗负担过重的心脏不再跳动了。谁能想到他也五十岁了!这个骨子里还没长大或者干脆就拒绝生长的孩子,这个被世俗的邪性挤压得身心畸形的歌王,在弥留之际,以呼救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诀别。五岁登台,五十岁谢幕,这真像是一则寓言。
当我从视频上看到他那座著名的梦幻乐园,看到了那兀自旋转的木马,心中一阵酸楚。大孩子杰克逊花巨资为自己修建城堡,不过是想用倒退的舞步,退回到那个被高价卖掉的童年。心思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的歌王,想坐在旋转马车上,拾捡起自己破碎的童年之梦。他真是个孩子,居然想打捞起失落的生命段落,而后一边尽情地玩乐,一边无邪地大笑,把自己变成万花筒里的一部分,美得耀眼动人。这是多么让人心酸的企图,当然小心易碎。天真的杰克逊,又一次把梦想放错了地方。这个心机深重、怀有太多窥探热情的世俗世界,永远是烂人无数。那些习惯于查点钞票或指指点点的手,能托住你瓷器一样娇贵的美梦吗?
在因为娈童案受审时,他是那么无助和无奈,他声音轻柔地说:
耶稣说过要爱孩子们,并且像孩子那样年轻、天真,如孩子般纯洁、正直。他是在对其使徒说这些的。耶稣的信徒争论他们之中谁是最伟大的。耶稣说只要你们中间谁像孩子一样本真,就是最伟大的。耶稣总是被孩子环绕。我是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的,我秉持这样的信仰,并那样行事,模仿(耶稣)那样的行为。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纯洁和明亮,就像一块洁白的台布,哪怕是一根最小的脏手指,戳在上面,也会留下难看的污渍。
我又一次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那所体育学院的年轻师生们。我们当时迷恋自己心中的偶像,那么羡慕他!其实,和偶像相比,某些意义上,我们这些草民倒可以说是幸运的。我们可以稀松平常地生活,缺少光彩但不乏自由;我们不用包裹着自己,墨镜遮脸,戴着面具出行,因为没有谁非要认出我们;我们可以在街头小馆开怀畅饮,也可以在公园的长椅上静坐一天,没有巨额财产,不必担心有谁惦记盘算;我们可以儿女绕膝,家长里短,在失去了偶像的世界里,继续看着世上的各种热闹……
迈克尔·杰克逊不要我们了。他不用再整容了,不用再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也不用再应付各种各样的算计和诉讼、解释皮肤的颜色和手术的部位了。再没有各式各样心思叵测的询问了,再没有龌龊和不堪的缠绕了。现在,全世界的歌迷在为他流泪,公认他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艺术家!他一生为世界和平、为人类、为天下的孩子唱得最多,做得最多。他一个人支持了世界上三十九个慈善救助基金会,保持着吉尼斯世界个人慈善纪录。而这个最有慈悲心肠的天才,也承受了最大的委屈和糟蹋。
网上说当年告他的那个孩子,终于良心发现道出了实情。一场为了钱的诬告。一切都太晚了!为了捏造的娈童案,最为羞怯敏感的他,完美主义者杰克逊,在全世界的电视转播中,一遍遍出庭受审,无辜又无奈,颜面尽失。那颗高贵敏感的心,为了一个假象,饱受最真实的摧残和屈辱。谎言是澄清了,可被痛苦熬煎、被伤害扭曲的一代天王,早被来势凶猛的恶意彻底地摧毁了!
恐惧和寂寞,忧伤和抑郁,落幕了。
我们,这些受过他艺术滋养的人,帮不上他;他用童心和歌声抚摩的这个世界,对不住他。我想,我至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亲爱的杰克逊,因为你的存在,让我确信,这世界确实有天使来临。悲哀的是,满面尘垢的人们,天使就在身边,却往往认不出来。
爱他的人、喜欢他的人,都希望他去的地方真的叫作天堂。可我还是忍不住说出自己心头的担忧:如果真是差不多的人都去了天堂,那岂不是这个世俗世界的整体上移?那被伤害至深、孤寂忧伤已经透入骨髓的他,真的就有了安全感,真的就不再寂寞了吗?
不知道。
黑孩子杰克逊,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曾拥有世上最深的肤色。五十年后,当他带着忧伤和遗憾、带着手术刀多次留下的痕迹离开的时候,他的脸,已经白得像一块要去包扎伤口的纱布,像一支默默流泪的蜡烛,像一张褪尽字迹的薄纸,像一片伤心游走的白云……
迈克尔·杰克逊,安慰过我们的天使,愿你安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