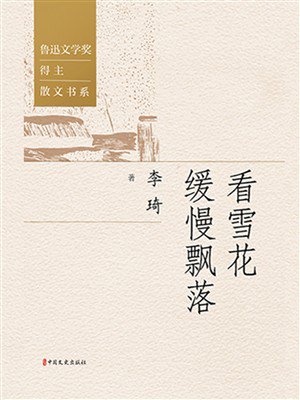望云
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你干什么呢?”“待着呢。”我如实相告。一会儿电话又响了:“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么半天才来接电话!”我在干什么,我在看天上的云朵。我靠在窗前,久久地望着一朵去远了的云,已看痴了过去。我不愿意这时接什么电话,就对着话筒说:“对不起,我现在有事。”“你有什么事?”我终于听清了那温暖的声音是妈妈,就一下放松了,就说:“好,我在看云呢!”母亲太了解这个从小就怪里怪气的女儿了。她交代了我几句就说:“你看吧,别忘了接孩子。”
可我再看不下去了。我顺着妈妈的声音飘进时间隧道,回到了最初看云的岁月——
我从小对天空充满了崇拜和敬畏。那时我是个安静、瘦弱的小女孩。像一枚草叶的我好像比现在更深沉,总像有心事的样子。我常常静静地坐在我的小凳子上,仰着头默默看云。那是多么洁白、柔软的云朵,它们的姿影怎么会那么美丽。它们会走路,也会别的吗?我牵挂、眷恋那些云朵,总觉得它们和我一样,是人类的另一种。它们静静地飘动在我的童年,还是孩子的我形容不出那种曳动的、纯净的美,却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我觉得它们不会是无缘无故地从这里经过,每一块云朵的飘逝都让我有一种惆怅。“它们走了。”我从那体味了人生最初的无奈和忧伤。我成为母亲后,发现孩子确实有孩子的忧伤。一个目光清澈的孩子的忧伤是非常令人心疼的,又往往是大人们看不见的。
七岁时,我在一个夏天的晚上,看到天空出现了彩色的云。那是以深红为主要色彩的云朵,还有几抹橘子皮那样的黄。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一种好看而奇怪的图案。我呆住了。我觉得天要说话了,就要出什么事了。我就跑了进去,告诉了爸爸和妈妈。他们出来站了一会儿说我是在做梦,是幻想。我妈还说你以后不要把幻想和事实搅到一起,还说一个人一定要诚实。没有人相信我,他们还为此叹了口气(成年后这件事还常被作为我胡思乱想的凭证,被屡屡提起)。我渐渐把这件事藏在心底,不愿再和别人说起。
很多年后,在又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男同学。他说,我信。那一瞬间我受到的震动竟和七岁那年晚上一样。我的双眼一下装满了泪水,又一次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后来发生的事就是我嫁给了这个人——这个相信我诚实的人。或者说看重我胡思乱想的人。
上学后,老师在常识课上对云的解释,远远不能满足我的期待。尤其当她说其实不是云彩在走时,我是那么失望。我站起来,提出了古怪的问题。老师慈爱地望着我笑了:“傻孩子,你应该相信科学。”我原谅了老师,因为我爱她。可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坚信:这世界上不只有科学。
十五岁我下乡了,在五七干校当了个欢天喜地的新农民。广阔的原野、新鲜的空气和各种各样的农活儿最初简直是把我吸引了。我热爱劳动,热爱天地之间的那种广阔,热爱那冲刷一切的雨水。我坐在牛车上去给工地的战友送饭,自己仰脸看天不够,还煽动别人看。结果那车翻到了沟里,每个人都洒了一身豆腐。由于我下乡的时间太短,所以,对那段生活的回忆,远不如真正的知青那么沉重悲怆。我只记得,我一生中只有那个时候吃饭最香,只有那个时候,能躺在温暖的麦秸垛上看云,呼吸着麦秸那种温暖清香的气息,看云飞云走,身体的疲劳,现实生活中的迷茫,在那一刻得到了缓解。当年和我在一个干校的许多知青记得,十一连有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子,总爱仰着脸朝天看,他们奇怪,那个又瘦又小的她,在看什么?
看云。
就觉得那云朵是我心灵的亲人。尽管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内心那种情感就是失落和痛苦。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云朵成了永远的慰藉和向往。
我开始注意暴风雨前的天空。那迅速聚集的云朵像是听到家族首领的号令,一扫温文尔雅,变得凌厉而暴躁。它们翻滚着,扭动着,一副要清算一切的样子。那是温柔变成的愤怒,所以有难以估量的力量。它令人害怕,又给人一种震动。它对人有一种压迫,又像有一种召唤。在这时候,我非常想靠在一个坚实的肩头,或许就是这样,我长成了女人。
我就在这不断的仰望中,像一棵树那样,渐渐飘落了青春的叶子。
如今,看惯了橱窗、广告,看惯了街市上的嘈杂拥挤,看惯了一张张充满了欲望的面孔,看惯了滚滚红尘,再轻轻抬头看那天边的云,它的单纯轻盈,它的洁净悠远,它的温柔恬淡,已经有了一种哲学情思,成为一种境界。它把人一下提纯了。你就觉得那天空是你的心灵,云朵正从你受了伤害的心头拂过。它关怀你、疼爱你、指引你。它从不许诺却永不背叛,它不留痕迹却情意绵长。你就这样一下抖落世俗的尘埃,重又干干净净了。对天空、对云朵的仰望,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支撑。
曾有人嘲弄过我:“诗人就会整天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云了雾了,精神病!我就最看不上写诗的!”这的确是位从不想虚无缥缈事的人。记得一次去野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大家那疲惫的心好像重新抽出了嫩绿的枝芽,玩儿着、笑着。唯有他,下了车就大吃一顿,而后倒在面包车里一直睡到往回去的时候。身边的湖光山色尚且全然不看,更不要说那高远的天空了。
一次在我同学的家里,说起了我喜欢看云。我同学的父亲——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目光奇异地望了望我,而后缓缓地说:“我也愿意看云,就是我这辈子看得太少了。”这是一位学问渊博、沉默寡言的老人。这个当年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竟有几乎半生的时间,在中国北方一所寒冷、粗糙的监狱里度过。当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忍辱负重活在四壁黑暗的囚室里,那自由的云朵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以为会为他奔走的朋友,早已划清了界线;他期待尽早来临的昭雪,也遥遥无期。他沦陷在彻底的孤独中、坚硬的生活里,只有那轻盈的云朵,在他最沉重的时刻,默默守望着他。他把它们幻化成妻子和女儿的面容,把它读作远方的书信,把它看成活下去的指望。就在那空对苍天的岁月,一个举止昂扬的青年变成了行动迟缓的老者,一个曾以侃侃而谈为职业的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云朵和风,还有谁知道他那些年的心事?沉重的云朵,你不声不响,却成了悲凉人生的见证。
如今这位老人,正在女儿家安度晚年。他平淡地对待舒适或者不舒适。用他女儿的话来说,我爸从来不抱怨什么,他不会抱怨了。他常带着小外孙去太阳岛,当孩子在那沙滩上尽情玩耍时,他就一声不响地去捡起游人扔下的果皮纸屑空酒瓶。他想让那些在沙滩上享受太阳和风的人,有一片干净的沙滩。累了,他就坐在江边,默默地看江水,看天上的云。
这个老人真实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对云朵浮浅的眷恋中,又掺进了一种苦涩。再望那云时,有了一种醒悟:学会仰望的同时,也该有俯瞰的能力。
说来有趣,天性里的东西,它也会遗传。我的女儿正在不知不觉间越来越像我。
去年秋天,我带女儿坐出租车去办事,中央大街上,车子稳稳地开着。忽然女儿一拽我,指着车窗急促地说:“妈妈你看!”我和年轻的司机都吓了一跳,不知该看什么。女儿陶醉地望着车窗外的天空说:“你看那云彩多漂亮!”我和司机都笑了。我们受了这十岁小人儿的感染,情不自禁地向天空望去,车速明显地减慢了。
那云彩真是出奇地漂亮。一朵一朵的白云叠在一起,极有质感,像是一座奇异壮丽的雪山,茸茸的,又像是一千只天鹅的翅膀,而它的背景,是那湛蓝的、湖水一样的天空。这是经典的北方秋天的天空,它纤尘不染、高远明净。它的美丽辐射出一种气蕴,我们好像看到了人类最初的天空。
“我天天开车,就没想起来看。别说,真漂亮。”年轻司机一边慨叹,一边回头赞赏地看了看我女儿。车内的气氛一下变得融洽、亲切,我们的车就在这蓝天白云下,优雅地行驶着。
下车时,司机居然想不收钱。我谢绝后,他由衷地说:“小朋友,叔叔真愿拉你。”他热情地留下传呼号码,说有事找他。云朵,居然成了我们和这陌生司机的一种默契。
那天回到家里,我翻箱倒柜找一张底片,那是我好几年前拍的云朵。尽管那柔软的、飘动的、蓬松的云变成照片后,已失去了那种生动和韵味。但那毕竟还是云。我想冲洗放大后,送给那位老人,也送女儿一张。可惜无论如何找不到。我坐在一堆乱七八糟中,忽然心有所动:这是天意。美好的东西不能复制,它埋伏在你心灵最深的地方。你只要用心去感念着它,让它长久地照耀着每一个平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