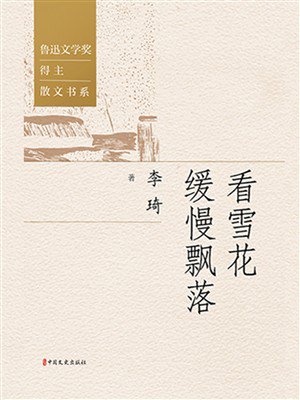雪花飞舞事与人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冬天、对大雪,有说不出的感情。一到下雪的日子,心情就混沌起来,说不出是舒畅还是怅惘。心变成了最薄的瓷器,被片片雪花所碰响。常常,我会默默地、长久地望着这充满神性的特殊的花朵,陷进一种很深的冥想里面,一种感动和温暖渐渐升起。从前的经历、逝去的往事、远方的友人、奇异的联想,都随着那轻盈的雪花扑面而来了。
想起一个小学同学
她的名字就在我的嘴边,我不愿说出自有道理。那天,望着窗外的第一阵雪,我一下就想起了她。在没有她的世界里,我还能在看雪。百感交集。小学时,她是一个特殊的女生,她家是开理发店的,一天到晚乱哄哄的总有许多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初,很少有不用功、爱骂人的女孩子,她却是。她的粗鲁使我们都不太喜欢她,平时玩儿也不在一起。那些淘气的男生都愿意和她打架。
有一天,下课了,我跑到操场上,被正在飘飘洒洒的大雪给迷住了。我就仰起头,一边看雪,一边伸出舌头去接雪花。
她来了,看到我的样子,问,你吃过雪吗?我摇摇头。只见她弯下腰,用手团起一个雪球,大口吃起来,而后挑战般地问我,你敢吗?我摇摇头。她说,我还吃过雹子,吃过房檐下的冰溜子。见我那副被震住的样子,她又接着说,我还吃过纸,连牛皮纸我都敢吃。你呢?她那居高临下的神情今天我还记得。
后来上课了,整个一堂课我都没听进去。我不时偷偷望她一眼,觉得她其实不像我们平时认为的那样不好。她身上有奇异的东西,她可能是个勇敢的人。我还联想到那些当着敌人的面把情报吞咽下去的革命烈士,我想,她也能。
又有一次,我上少年宫演出回来,还没卸妆,一上楼撞见了她。她问我,你在台上害怕不?我说不怕。她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挺爱唱歌的。那正是诚实的年龄,我就说,你唱歌不好听。她凶狠地望了我一眼说,那是我装的。我当然不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她的声音。再说有什么必要装着唱歌难听呢?我有些疑惑。长大后我才懂得,她其实是在为自己遮掩。像所有孩子一样,她也想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少年。
就是一个这样的同学,因为气味不相投,还没等长大我就把她忘了。可后来,偏偏她一次一次地以新闻人物出现,每次碰到她的名字都是触目惊心。在“文革”那种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她先是学坏了,被公安部门拉着游过街,被劳教、关押过。有同学见过刚释放回来的她。她变了一个人,当年的粗鲁和豪气全没了。她老了,嗓子更粗哑了,人也憔悴了。她在大街上碰到我们的一个同学,眼含热泪说,我一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就是小学,咱班同学多好啊!她挨个打听我们。她想洗心革面,过一个女人平静的日子,就嫁给了乡下一个农民。没想到人家最后知道底细,不要她了。走投无路的她,刚烈地吞钉自杀了。
一个冬天的下午,雪飘阵阵,我们几个小学同学在一起吃火锅。说起她的名字,忍不住唏嘘感叹。大家说为她喝杯酒吧,火忽然就灭了。我们面面相觑,一个同学幽幽地说,她想咱们了。
想起我和我的“绿窝头”
我小的时候,自己说了不算,一切得听命于家长。我的母亲一生坚持高标准审美,从穿衣戴帽到厨房的锅碗餐具,都到了讲究得可以的程度,她总是把我们打扮得引人注目。从幼儿园,我就开始在穿戴上体现母亲不凡的眼光。记得我的操行评语上曾比别的孩子多一条——仪容出众。长大后当年的伙伴见到我是那么朴素普通,都忍不住回忆一下说:小时候你可真……
有一年冬天,妈妈为我和妹妹做了一个绿色的毛茸茸的大尖帽子。这种帽子只见过画报上的外国孩子戴过,顶端尖尖的,还带一个白色的大绒球。我和妹妹相差不到两岁,个子一般高,模样相近,又同在一所学校。早晨,我们姐儿俩走在上学的路上,都戴一顶在雪地中分外显眼的帽子,连行人都在看,说这是一对孪生姐妹,真漂亮云云。
我的这顶帽子给我们班那些爱给别人起外号的男生带来了灵感,他们管我叫“绿窝头”。这当年让我深以为辱、怒不可遏的外号现在想起来还真挺形象。那帽子确实像一个夸张的窝头。在我的同学都戴着样式普通的风雪帽时,我的帽子确实太特殊了。记得那时我上学之前总要犹豫一下,一想到那些讨厌的男生,我真想不戴这帽子。可妈妈不让。她说,你想让耳朵掉下来吗?那时的冬天可真冷,不戴帽子就等于是不要耳朵了。于是我就戴着这顶我并不喜欢的帽子上学去了。有一次,一个男生在我后边刚说了一个“绿”字,我使劲一回头,愤怒地盯住他。他讪讪地笑着说,还不让说绿了?接着他就胡乱造起句来,绿草绿地一连串绿。我当时想,我不会再和这样的人说话了。时隔多年,当我变为了成年人之后,我在一家医院的门前见到了这位同学。他来看病。他已经是疲惫不堪的中年人了。我询问了他的病情,他一一告诉我。待到就要道别分手时,他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他说,你还记得你的那顶帽子吗?我刚要声讨他,他居然带着无限神往的神情说,那时候多天真,起一个外号兴奋好几天。我到现在还记得你那顶帽子,大白球一甩一甩的,多好玩儿啊!
我无言。
想起卖糖炒栗子的人
从前,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像冬天,嘎嘎冷。我们都穿得圆圆滚滚的,像五颜六色的糖球。
那时的雪,经常一片一片地下。下得急的时候,就像一阵热烈的掌声。羽毛一样的雪,一会儿就覆盖了整座城市。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就像做梦一样。那梦里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卖糖炒栗子的人。
卖栗子的都是在街上支一口大锅。卖主拿着铁锨,站在大锅前翻来炒去。天太冷,卖栗子的人脚穿那种长及膝盖的毡靴(俗称毡疙瘩),有的戴狗皮帽子,有的戴一顶棉帽。热气、雪花,使他们的眉毛、头发、胡子上都是一层白霜,就像圣诞老人一样。晚上,他们点一盏瓦斯灯,在飘着雪花的街头,瓦斯灯的小火苗一蹿一蹿的。卖栗子的人,袖手站在灯后,左右跺着脚,就像从童话中走出的人。凛冽的冬天,于是添了几许香与暖。
有一天晚上,全家都想吃栗子。我征得爸妈同意后,拿了五毛钱向卖栗子的飞奔而去。站在那口正在冒热气的大锅前,我一伸手,糟糕,钱没了。当时的沮丧真是无法形容。正转身要走,卖栗子的大伯叫住了我:哪能空手走呢,来,装上!我说钱丢了。他哈哈笑了几声,说,钱丢了照样吃栗子!说声谢谢就中。我把又香又甜的栗子捧回家,向大人说了原委。爸爸连忙出门去给卖栗子的人送钱。回来时,爸爸又点头又摇头的,说这个卖栗子的是个山东人,又仁义又犟,钱说啥不要,说买的是买的,送的就是送的。
以后,等我再见到那个卖栗子的大伯,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他还是用那山东话吆喝着——新出锅的糖炒栗子,香死个人哎!
现在哈尔滨的冬天不那么冷了,穿毡靴的早绝迹了。冬天虽然还是有卖糖炒栗子的,我却常常连看一下的兴致都没有。在火苗一闪一烁的灯下高声叫卖,钱丢了说声谢谢照样吃栗子,那是从前的事了。
想起一个风雪之夜
1972 年的冬天。我下乡在某五七干校四营十一连。
那时我们正在挖水线,每天扛着铁锹或大镐,来回走十几里地,战天斗地炼红心。数九寒天,土地冻得硬邦邦的,大镐下去就是一个小印儿。我们经常干得满头是汗。出工下工,一路红旗飘飘,总有人在队伍最前面手捧着主席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很正常。
我们连总举着的那个主席像是薄铁的(演出时,我们偷着拿它做过暴风雨之前打雷的音响),上面是毛主席去安源。毛泽东同志在这张画像上年轻、英俊,又是走路的姿势,与我们的出工下工,挺配套的。
有一天收工回来后,吃过晚饭,各排战评后全连紧急集合,重要的事发生了。
原来,今天大家干得太累了,一听收工令下,饿得支持不住了。负责举主席像的那个班,也忘了自己的神圣职责。现在,我们都回来了,而那个领我们前进的主席像,正孤零零地躺在去安源的路上。
我们紧张地听连首长训话。
啊(第二声)!太不像话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啊!我们却把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忘在荒郊野地里!啊!看看外面这风(此时大风就像电影里的音响效果一样,极为配合地呼啸而过)!想一想吧,同志们,我们还能不能这么安心地吃饭、睡觉,我们还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说到此处,首长哽咽了。
全连静寂。那一瞬,我们全觉得自己错了。当天负责举主席像的那个班,羞愧难当。是啊,我们简直就是忘恩负义。当连首长宣布全连马上出发,说要“敬请毛主席回营房时”,我们心服口服。
那一夜我们步伐整齐,本来一个个已疲惫不堪,但因为是在做一件重要的、神圣的、赎罪的事,所以困意全无。踏着雪夜的月光,一连人马向白鱼泡畔夜行。一路上,天高野阔,北风呼啸。和这么多人在寂静的冬夜行进,我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后边的一个女生悄悄指给我看,说远处那亮闪闪的就是鬼火。她还告诉我,这一带有狼。鬼火闪闪,道路漫漫。开始我们还歌声、口令不断,等找到冻土掩映之中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心中的负担没了,紧张和庄严感也一下消失了。队伍开始放松,有些人甚至接近于放肆。前面虽然还是红旗引路,后面却变成了集体散步。学狼叫的,说笑话的,东倒西歪的,如果不是连长或指导员严肃的目光,我们简直忘了是来干什么的。临近营房时,重新整队,才发现少了两个女孩子——原来,一个女孩子体弱多病,本想请假,又怕让人说有思想问题,强挺着,终于支持不住,掉队了。和她要好的另一个女生宁肯受批评,也不愿背叛友谊,正陪着她一步一步往回挪。
连长指派几个强壮的男生去接她们。当这两个女孩子被找到的时候,她们正在茫茫荒野里抱在一起痛哭,她们看见了狼。
想一想真是后怕,如果不是及时发现了她们,那个荒唐的夜晚,在我们敬请伟人回营房的时候,我们的两个伙伴,就会被狼吃了。
想起喜儿
我记不清看了多少遍电影版的舞剧《白毛女》。样板戏的年月里,喜儿比方海珍、柯湘她们,更具美感,更牵动我的心。尤其它又是我喜欢的芭蕾。
一个多美好的形象,年轻、漂亮,喜欢扎红头绳,会剪窗花,她有自己的大春哥,一份自己的爱情。
初看《白毛女》时,当苦命的喜儿扑在含冤而死的杨白劳身上,悲痛的双肩一起一伏时,我的心疼得一紧一紧的。我忘了自己是在看戏,喜儿用肢体倾诉她的悲愤,我用心分担着她的痛楚。
喜儿被黄世仁这不是人的狗东西霸占了。喜儿逃进了深山,常年的野外生活使喜儿变成了让人惊骇的“白毛仙姑”。
这是奇峰突起的塑造。
追光下,一头白发的喜儿出现在舞台上,我被那种难以形容的凄凉之美抓住了。破烂的衣衫,满头月光一样的白发。当“风雪漫天,喜儿在深山……”忧伤的旋律缓缓响起时,泪水顺着我的脸流淌得无法控制。喜儿啊,我知道你恨难消,仇无边……我知道风雪再大也没有你的冤仇大。我知道你的坚贞和纯洁。我看着银幕上舞蹈的喜儿,竟觉得她像是我的一个遥远的姐妹。
有一个从小和我一起学舞蹈的女孩,清秀纤巧,安静羞怯得像一枚树叶。她长得并不多漂亮,可往人群里一站,却总是最引人注目。我当时不知什么叫清水出芙蓉,她身上就是那样一种出众的气质。她虽然也参加了一个宣传队,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没让她上台。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让她演出了。
那是一次文艺会演。她独舞,正好是跳“风雪漫天”那一段。音乐一起,她无声地移动脚步,那种轻盈优美,就像一棵小桦树舞动在台上。她跳得太好了,整个人都沉浸在音乐和舞蹈之中,一种深深的凄迷之美从她白皙的手臂和伤感的目光中散发出来,观众看得屏息静气。我觉得,她的表情比剧情的要求还悲痛,还丰富,跳到“恨难消,仇无边,心潮汹涌如浪翻”时,她已情难自禁,泪如雨下了。忽然,观众哗然,她昏倒在舞台上了。
原来,她也遇到了黄世仁。这个黄世仁出身贫农,是当时的工宣队长。两个喜儿,都有自己的风雪之夜,都为命运泪流满面。
想起豹子头林冲
重义气,爱宝刀,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与美貌妻子互敬互爱的林冲,是我少年时代看《水浒》最为心仪的英雄。记得有一次我问丈夫,我为什么老能想起林冲呢?
英雄嘛。他说。
这种回答无法让我满意,英雄多了。
是他身上那种秋色深重的悲剧特质?
是他那种切入骨髓的孤寂?
真是说不清。
我父亲喜欢京剧。少年、青年时看李少春的林冲,那唱念做打,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说,那演的真是林冲,阳刚之气,满台生辉,看得人胸胆开张。
脸上刺着字,心里流着血,男人林冲用枪挑着酒葫芦,正走在从小酒店归来的路上,隐痛弥漫在风雪之夜,他的心事何等苍茫啊。
英雄中了小人的奸计,英雄无罪而被发配。前程未卜,爱妻难见,自尊与刚强,牵挂与担忧,愤懑与抑郁,全在那一夜之间化作了漫天大雪。
那天的雪真是太大了。大到压塌了林冲的草屋,使他不得不躲到古庙里。他还不知道,这是命运的一个手势,他因此听到了一桩血腥的诡计。于是英雄一枪一个,杀死三个贼子,无奈之中,上了梁山。逼上梁山的“逼”字用得真是好,悲愤决绝,尽在其中了。
《水浒》中的好汉,诸多是泥沙俱下的英雄。林冲不是。他没有宋江的心计,没有李逵的粗糙,也不像武松那么冲动。他须眉正气,侠骨柔肠,有胆有心。他有一种人生猛醒后的苍凉,是潸然泪下的豪杰,是仰天长叹的英雄。
从宋代到如今,一千年的冬天过去了。一个小说里的人物,竟家喻户晓。夜奔的林冲,那行深深的、宋朝的脚印,总能在我眼前的雪地上出现。
人事茫茫,岁月茫茫,今夜,又是一场大雪茫茫。
想起两个变成了雪花的孩子
几年前腊月底的某天,我工作的那个大院里,像以往一样静谧。
一个女编辑的小女孩儿正在院里玩耍,忽然看见从旁边的家属楼上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她看了一下,像是个大玩具娃娃。她太小了,还不知道有坠楼这样的事情。她更不知道,那飘然落下的,正是她幼儿园的小伙伴。她就天真地跑进去,对妈妈说,一个娃娃从楼上掉下来了,穿红衣服的。
东北的冬天,谁会在腊月开窗?什么样的娃娃会从那么高的楼上掉下来呢?
待大人们赶到,把坠楼的小女孩送到医院,孩子已经死了。
她是被一双大人的手推下去的。
这双手和这个世界的肮脏、和成人邪恶的心计、和许多卑鄙的因素相连,无辜的孩子成了牺牲品。发生的一切如无声电影一样,真实却让人恍然。
记得出事后不久,我见到了孩子的母亲。她穿着深色衣服,在马路的边上悄然走着。她的脸像一张白纸,目光空洞而遥远。我不敢和她说什么,我知道这个双手捧土埋葬了小女儿的女人,她的心头,有一块终年积雪的地方。
今年冬天,又一桩由报纸披露的新闻,使全城人的心紧了一下。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因为绝望,用一条毛巾,在家自尽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孩子的妈妈与老师有一些小摩擦,她们都没有顾及孩子的自尊和安全感,她们相互都觉得自己有理。没有想到眼皮下这个孩子只有十岁,他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家、学校,这一条线的两端之间,孩子站在绝望的钢丝上。幼小的他,想到用减法结束这一切。
报纸想唤醒人们的良知,连续报道着这件事。从小男孩生前的懂事,到孩子出殡那天令人心碎的场面。知名的学者、激动的读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们泪水涟涟地读报,或议论或愤慨,许多妈妈都情不自禁地抱紧胸前的孩子。一位母亲告诉我,她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后,心疼得直抽。晚上,看着自己熟睡的也是十岁的孩子,她感到脊背发凉。这么小的孩子,居然知道自杀了,多么可怕!她一遍遍亲吻熟睡中的孩子,以至孩子猛然惊醒:妈妈,是我梦见你了还是真是你?
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两粒鲜草莓一样的生命,都枯萎在冬天。这让人不由轻轻战栗。想到这世上不知还有多少孩子,生命的乐章刚刚弹响优美的前奏,就被粗暴地打断了。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个世界上的流云、夜晚的星光、快乐的游戏、食物香甜的气味、芬芳的水果、甜美的冰激凌、活泼的小动物,小孩子们喜欢的一切,从此都不再属于他们了。我们这些有罪的大人。
稚气的孩子,变成了伤心的雪花,在他们还未及认识就遭伤害的世界上,飘着飘着,消逝了……
想起远方的朋友
雪,下着。这是时光走动的频率。这样的时候,常常是情不自禁,就想起远方的友人。朋友原本就不多,轻轻一想,全在心上。朋友又不是雪,怎么一到下雪的时候,就格外思念他们呢?
想起他或她亲切的容貌——我的朋友们或额头高洁,或目光温和,都是善良和自尊的人。和他们相识,真是我的幸运。我望着窗外的雪,想起与他们的交往中那些有趣的往事,他们的声音,习惯的动作,他们的毛病,可爱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有一个人总是想冲着太阳打个喷嚏,找不到太阳时,他就找灯。
想起那个远在异国的人。说她是知己,每一个笔画都正确。一生中几乎知道我全部心事、分担我喜乐哀愁的人。她住的地方四季如春,连偶尔天阴一回都让她兴奋。她生活优越却不快乐。在从不下雪的地方,她也不向别人轻易吐露心中的忧伤。她和我一样,爱雪。少年时代,我们经常站在冬天的松花江边,一言不发地看雪花飞舞。别人曾奇怪,两个女孩子怎么会有那么深的友谊。说实话,我们自己也奇怪。如今,在地球的两端,我们相互牵挂。这种牵挂,是永远。
想起一阵美好的歌声。唱歌的人,站在一片烟波浩渺的湖边。风吹起他的头发,他轻抬双臂,歌声如金属落地,又如水袖飞扬。一曲“今夜无人入睡”,把那灰色的夜晚变成了歌剧里的一幕,风声和月色,圣洁而悠远。
想起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安静的酒吧里,我与一人对坐。两杯绿茶,泡着一个温暖的夜晚。说到诗歌和人生,我们竟是那么默契。我面前的这个人,宽厚善良,说话的声音沉着好听。我当时想,要是从没听过一个这样的人对你这样说话,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遗憾。
想起一双秀美的手,这双手为我缝过漂亮的长裙。这是一双职业画家的手,本来可以创造出许多意境超俗的画面,可这双手现在最为经常做的事,是为久病的丈夫端水拿药,侍奉那个越来越乖张的病人,拉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这双手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弱而无力,它要经常擦拭泪水,要不时放在疼痛的胸口……
想起一条羊毛披肩。它来自远东一家俄国小店。我的朋友把它带回时,只淡淡两个字“给你”。一个在意你冷暖的人,才会使你体味到没有他的那种冷。物在人空,我常望着这披肩发呆。友情如河流,不会干涸,可它的骤然转弯,却让人猝不及防,心怀怅然。
就这样,我在哈尔滨的大雪中原地未动,却追随着北风,策马跑过一个又一个驿站。
亲爱的安然的大雪,你的飘落给了我一条道路,一条纯银的、只留下我独自足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