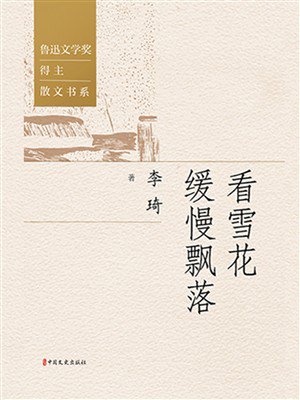罗密欧与朱丽叶
马迭尔冷饮店位于哈尔滨漂亮的中央大街上。这条街因为两旁多是异国特色的建筑,又有一条经过百年风雨、古旧的石头马路,就很有一种情调。有时会让人蓦然产生恍如欧洲的感觉。如今中央大街已是步行街,是旅游打卡地,对外地人来说,算是不能不看的一景了。
老哈尔滨人都知道马迭尔。它原是一个法籍犹太人开的店。这个犹太人有个漂亮又有才华的儿子,在法国学习音乐。儿子回哈度假时,被日本人绑了票。匪徒送来儿子的耳朵,倔强的老犹太人肝胆欲裂,但就是不屈从。于是儿子惨遭杀害。
我二十岁左右时,常去这家冷饮店。我和我的好朋友晓冰对坐在小桌两边,要上两杯酸奶、两个刚刚出炉又香又软的面包,轻轻地说着话,心里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喜欢那里的宁静,也喜欢那里的酸奶。那酸奶全不像今天这么稀薄。它稠稠的,粥状,盛装在一种厚墩墩的乳白色瓷碗中,上面均匀地撒上颗粒的白砂糖。用小勺轻轻搅匀而后滑爽地咽下的那种感觉,真惬意。我有时干脆来两份。
有一天我发现旁边桌坐着两个出众的人。他与她一望而知不是我们炎黄子孙。他们是一对中俄混血儿。哈尔滨人习惯把俄罗斯人叫老毛子,把混血儿叫二毛子。略显粗鲁的叫法中,也有一种民间的随意和亲切。20 世纪 50 年代,华洋杂处仍是哈尔滨的特点。这里外籍人很多,其中以俄罗斯人为主。他们多是“十月革命”后逃出来的白俄,天长日久,已把气候、地理、人文环境与莫斯科颇为近似的哈尔滨当作了第二故乡。所以,与华人通婚者、恋爱者很多。那些血缘遥远、深得杂交优势的混血儿,择欧亚之长,比他们的长辈们更漂亮、更独具一种魅力。
到了 70 年代,这些人大多数已迁居他国了,可是偶尔仍能看到一些孤寂的身影。他们像落叶一样,在哈尔滨的街头飘零着。
我望了他们一眼。真是造物主的杰作啊。这两个人都穿着当时多数人穿的那种普通的蓝衣服,但依旧气度不凡。男的好像比女的小一些,雕塑般的面孔上略带一种薄弱,鼻翼很薄,像我想象中的肖邦。那女子于安静中散发着一种圣洁之美,石膏像般洁白精致。他们默默地对坐着,面前各是一碗酸奶。两双漂亮的大眼睛里,都盛装了无限的哀愁。那个男孩子好像说了句什么,那女子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那呵护、关爱的样子,是姐姐无疑了。
我被他们的美和愁吸引了。以当时的局势,我知道这样的人不会开心。那是反帝反修的时代。作为反修前哨的边疆城市,有些人习惯将这样的人与什么电台、特务之类的联系起来。就是明知他们清白,为少惹是非,大家也是敬而远之。这一对姐弟,正陷在无望中。这样好看、目光良善的人过不上舒心的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有错的。
那天的酸奶于是觉得不好吃。我和晓冰从冷饮店出来,沿着中央大街径直走到松花江边。我们都在惦记着那对姐弟,感慨着人生的无常。夕阳西下,江水像是铺上了一层玫瑰,我们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吹口琴。情不自禁,就吹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眼前晃动着那两个人的身影——苍白的脸庞,蓝色的衣服,忧伤而漂亮的眼睛……口琴声忧郁伤感,顺着江水漂远了……
此后在冷饮店又看到过这一对姐弟。彼此友好地点了头。那个男孩子越发苍白了。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得了重病。再以后,无论是在冷饮店还是其他地方,都见不到他们了。哈尔滨的侨民几乎走光了。他们大多选择了遥远的澳洲定居。这些失去祖国的人,又一次失去了第二故乡。这对姐弟去了哪里呢?那时候,我常常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窗外下着雨,我的朋友一会儿呈示部一会儿再现部地絮叨着,我却完全沉浸在自己对那音乐形象的感知中。阴暗、压抑的气氛,封建家族中的仇恨,恶势力对爱情的无情扼杀,这感情色彩强烈的音乐语言在诉说着……我看到了那个充满仇视、猜疑、人性压抑的时代,我看到了中央大街上那不断驶过的尖锐刺耳的宣传车……我看到了脖子上被挂上一串鞋子的女演员……当英国管和中提琴奏出美丽的爱情主题时,我的眼前竟出现了那一对混血姐弟。他们年轻、美好,是另外一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对着生活的悲惨与残酷,他们相依为命,用骨肉亲情温暖着彼此寂寞寒冷的心。我看到了马迭尔冷饮店那张小桌旁,已经深怀忧伤的姐姐正在温柔地安慰同样忧伤的弟弟……旋律在奔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骤然响起了惊雷。这来自天庭的鼓声,像是对人间邪恶的拷问。当乐曲结束时,乐队全体奏出的强烈的、巨大的激愤中,也有了我的一份。
一切已经成为过去。我已是许多年没迈进那家冷饮店了。没有从前那样的酸奶了,也没有那么动人的目光了。那家冷饮店如今是烤羊肉串茶鸡蛋一应俱全。原来那种奶香和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已被一种混浊的乱七八糟的气味所代替。当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甚至不愿向那里望一眼。我怕蓦然回首,再碰疼那颗好像已经平静了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