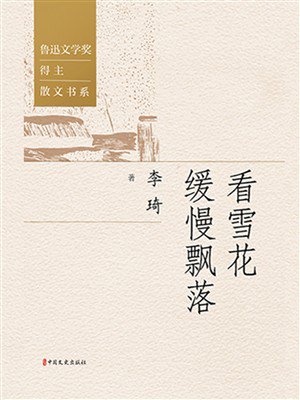随合唱远游
娅伦是个好听的名字,拥有这个名字的人是内蒙古青年合唱团的指挥。我先是听人说起过她,说她是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艺术感觉特别好。因为这个名字好听,我就记住了她。
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她,印象很深。她指挥的内蒙古青年合唱团参加国际合唱节,反响强烈。那些身穿漂亮蒙古袍、有一种特殊气质的合唱团团员,站在那里就像一道动人的风景。和谐纯净的歌声里,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彻底的声音,像火车到达终点那样,这声音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
合唱是美好的。那种由每个人的嗓音汇集起来的奇妙的人声会开拓一个辽阔的空间。声音的相融,意念的默契,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平素少有的和谐、理解。这种和谐与理解从人的心头经过,对人会有一种提升的作用。你一下会觉得,人的声音是这么庄严而美丽,人生的内容这么动人。真是好啊!
少年时我参加合唱,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从唇边离开时,我简直有点儿不信,这么美妙的歌声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发出的?一种激动遍体走过,五月的鲜花在我的眼前次第开放,先烈们悲壮的身影,过去的岁月,一幅幅画面电影镜头般在我的眼前展现,我进入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世界中。
我于是开始喜欢合唱,合唱的形式与内容都有深深打动我的地方。一场成功的合唱音乐会,既体现了人类的激情,又有一种巨大的美感。那一年在电视上收看北京万人演唱《黄河大合唱》,真是有种惊心动魄之感。歌声的风暴,歌声的马群,那种波澜起伏的戏剧性,那种庄严雄伟的史诗感,简直就是一颗歌声的原子弹。我被笼罩在这大合唱的蘑菇云下,有种要放声大哭的感觉。
还有一次,看俄罗斯无伴奏合唱团的演出,真是终生难忘。那种高超的、纯美的合唱艺术,那种高级的和谐,那种合唱团员之间奇妙的心领神会,那种如海水漫上沙滩般缓缓涌上来的美感,驱除了我心头所有与音乐不协调的情绪。我进入了那歌声,惊奇地聆听到人类声音的辉煌与斑斓——钢铁的声音,丝绒的声音……精灵的声音,我见到了声音的雪山!我的耳朵来到了声音的名胜之地,我只能长久地沉默。
热爱合唱,自然也就尊重指挥。我见到的第一位指挥是我小学时的音乐老师。她当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指挥,可是,是她让我懂得了合唱的魅力。我们的歌声跟着她的手势,或强或弱或柔和或刚劲。明亮的汗珠一粒粒从老师的额上浸了出来,她变成了另一个人,矮小的躯体好像在长高,生动甚至奇怪的表情迷住了我们。她有时张着嘴,有些夸张地不出声音地唱,有时又像要睡过去一样半眯着眼,身体斜着,眼看要倒的样子。她的手势时而果断时而柔和,我们的歌声就跟随那双手,起伏飘荡着。那双手哪怕一些细微的动作,也传递着一种令人信服、美妙的信号,那双手带领我们穿越自己的歌声,来到一种让人迷醉而激动的境界。那双手使我相信,歌唱是生命里一件动人的事情,我们是需要这事情的。
比起我的小学老师,娅伦是真正的指挥。尤其是她指挥的不是一群幼稚的孩子,而是一些真正的歌唱者。那些人与娅伦很默契,既训练有素,又满怀激情。他们好像集体通灵了,唱得那么好那么令人感动。歌声一起,一阵神风,抽走了所有的灰尘和杂物。通向美的那扇门徐徐敞开了,一种浑厚的庄严,一种微带凉意的清澈,就在娅伦的手势下、在合唱团的歌声里向外弥漫。那歌声里有光线、空气、雨水和风,有一种对天地万物、宇宙星辰的深深的爱情。这些具有独特精神风貌的蒙古族人,让人想起星汉灿烂的夜空,想起无边无际的草原,想起地平线,想起长鬃飘拂的野马群,想起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光荣。我满怀敬意地记住了这个合唱团,是因为他们让我的耳朵有过一种高尚的感觉。
蒙古族的娅伦皮肤白皙,比起她的父辈来她已经非常城市化。她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典雅,说话爱打手势。那双手很漂亮,光洁、修长。用这样一双手述说音乐语言,如指挥战役般指挥美好的歌声,让人舒服。
据说娅伦是我国第一个学合唱指挥的研究生,正在北京学习。我想,这样一个人,北京一定要想法留住她。可我不知为什么,有种担心,她要是真留在北京,那个叫作内蒙古的辽阔的地方就少了她,那个带给我美妙感受的合唱团就不再是由她担任指挥了,那会多么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