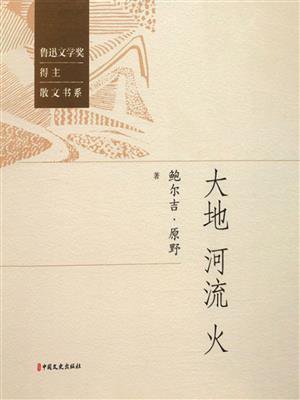石头
即使把石头碾成齑粉,也找不到它的门。石头,我们怎样进入你的内部?像掰开杏看到杏核、砸开核桃见到核桃仁那样。把岩石凿开一个洞,即山洞,也进不到石头里面。而洞里面的石头仍然排列着沉默坚毅的脸,它们什么都不说。
组成世界的东西其实很少,有被我们称作天空的空气,还有泥土、河流、草木、火和石头。大地上比泥土更多的是石头。石头,你能告诉我们你是什么吗?
人把石头磨成平面,见到花纹,甚至显露出风景。在大理石的内部,藏着云烟、丘壑,有宋人笔意的漠漠云林,这里有人间的气息。石头何时留下了这些记忆,记这些做什么呢?不能怀疑,世间所有的美景都藏在了石头的内部。人在大理石上看见的图案只是它一个断面,或者叫一个瞬间,切掉这个断面,出现的是新的断面。它到底有多少断面,记录了多少风景呢?它有无数断面,只是不予人见。
石头组成我们所说的大山。“组成”这个词或许不对,山是一个整体,它分裂过,却无须组成。人的想法是进入山的里面——不仅仅是掏山洞——让石头敞开,接纳我们。我知道,石头的每一个分子都与其他分子牢固地结为一体,而不能像水那样透明。是的,水与水的分子也不可分割,但水可以装进壶里,掬在手上。水让人看到它的正面和背面,石永远不让人看到它背后的东西。我觉得问题出在人的眼睛上。人的眼睛只能看清一部分——也许是一小部分东西,当然这已经很好了——但目光看不清木头的质地和石头的质地。人的目光在所谓夜里会被屏蔽。也许,有的动物看石头如同看果园枝头上的果子,石头里的花纹、翡翠甚至金子在它眼里都清晰如图画,只是对它没什么用处。翡翠对狐狸来说并不比羊粪更有信息上的价值。
帝王用石头建造宫殿,再用石头建造陵墓,石头以其坚固威严和沉默为帝王提供生与死的场地。对石头来说,帝王如同一只小虫在它上面活过并死去。与时间并行的不是水而是光与石头。光每天搜查大地,甚至搜到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它要找的东西。光刺破空气,赋予万物色彩又让色彩退去。然而光无法穿透石头,石头没有门。石头里储藏了数不清的时间,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去了哪里?什么东西里能装下这么多时间?或许它储藏在石头里。故此,石头永远不开门,故此石头沉重。虽然被存入石头的时间已被压缩过,但仍然太多并沉重。
石头里的铁矿是红色的时间。那些与火有关、与阳光与血有关的时间被打包变成铁。与植物有关的时间变成了铜矿。铜可黄可红,不经意间会流露绿,植物的时间露出了一些粉末。水晶是关于水的时间的压缩体,它透明并可以透视星相。不知道藏在石头里的玉是谁的时间。玉太神秘,它也是石头,但前面加一个玉字,人称玉石。玉几乎要脱离石头变为世间一切美物,玉雕的蝈蝈,几近于蝈蝈,但比蝈蝈值钱,它是玉。玉温润,凉沁,光滑,细腻。羊脂只是羊脂,细如羊脂的玉却是一块石。石头通灵,这是上大人曹雪芹说过的话。可是,玉储藏了谁的经历与时间?史上那些君子淑女已远去,上苍不欲他们的精魄离开此世,藏于石中,此为玉的前生。“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离骚的这两句诗为鲁迅所爱,写下来挂在床头。人问:高丘指谁?无女是怎样的含意?鲁迅不答。高丘不是哪一个丘,也不一定是楚王。无女到底无哪一个女,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人的一生都有一段惋惜,值得反顾流涕,为高丘也为无女。那些高洁的人、醇和的人、温润的人的时光都被苍天收藏起来,放置某处。上苍戴着丝绸手套收藏他们的时光,包括他们的忍耐、涵养、笑容与永不摧折的理想,收之入石,成为玉。玉颜色青白,无味,摩挲经久出血络。玉是英雄美人的时光。英雄不光是武人,还应该有庄子、王羲之、苏轼等人,还有没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活过的时间压缩在玉里,是玉的光,或质、或渺茫的云纹。
山峰上的岩石在等待时间弯曲。等待光像树一样在田野生长。石头的话被风、鸟儿、河流说过来,石头在静默里目睹白云坍塌。石头并非牢不可破,金子在岩石里奔跑。蝴蝶飞进石头里找不到飞出来的路。草履虫在石头里安家。石头能跟我们说句话吗?你不开口是在信一个什么样的承诺?那是对谁许下的承诺?如果鸟儿用叽叽喳喳传达石头的话,我们听不懂,风声和水声里的语义都不为我们所知,最后对石头一无所知。石头的姿态与人类毫无关系,仿佛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世纪甚至不同的光年里。世上一日对石头只是一秒,它还有亿万斯年的时间等着它悠闲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