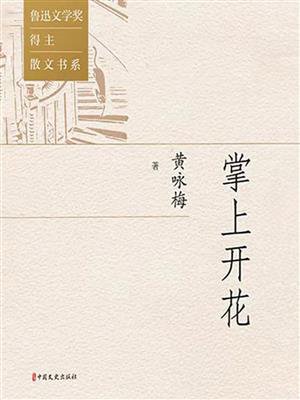围炉煮旧
在我们家,我是唯一一个在他乡生活的人。从读大学开始算起,三十多年往返于异乡和家乡之间,行李箱从少年拖拉到中年。虽然住过的也不外乎桂林、广州、杭州几个城市,但与家人的聚散场面,足足可以拍成一部年代剧。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春节竟逐渐成为我们一家人忆旧的聚会了。辞旧迎新,相比起来,好像我们更留恋那些辞去的旧,或者说,我们对那些旧的共同记忆愈发清晰起来。旧时光是过去时的,新生活是将来时的,如果不是人的记忆和情感在迎来送往,它们根本不会照面。而岁月,就在它们的不断照面中逶迤游走,在游走中沉积下人生的况味。
今年春节,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我早早下单,给父母买了一套网红烤茶炉具,放在阳台的那张四方老木桌上。陶瓷材质的复古炭炉,玻璃壶里的六堡茶咕嘟咕嘟细声煮着,浓酽的茶水一泡接着一泡,就像我们的往事,一串接着一串。坐在木头小板凳上,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围在一起,不时地,烤炉上还会烤一些红薯、花生、板栗或者红糖年糕之类的“古早”食物,当作茶点,热乎乎,香甜甜,恍惚间有一种昨日重现的错觉。只不过,围坐在茶桌边的人,发肤都已经被时间一再爬过——父母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已不再年轻。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一惊一乍的表达,即使说到旧日一桩桩或惊怪或悲伤或搞笑的事情,也只是时而唏嘘,时而欢笑。俯仰之间,我偶尔用目光瞥过每个人身上,会生出一种温暖的安慰。仿佛来到这个冬夜的幸福时刻,我们是跋了山涉了水,仿佛我们是被时间劫持过后的重逢。
因为一个叫梁大富的人从我们的话题里跳了出来,今年,我们多了一个重返石鼓冲的节目。
我姐说,前些日子在街上碰到了招弟,简直认不出来了。招弟是谁?母亲在心里算了算,对我说,你大概是没什么印象的,那时候你才四五岁,招弟是梁大富的女儿啊。这个名字一下子点亮了我的记忆。“梁大富,冲凉不脱裤”,这句儿时的顺口溜,居然顽固得像“床前明月光”一样,还在。
在我读小学之前,我们家住在市郊石鼓冲的一座小山上,独门独户,上下山要沿着一条泥土阶梯爬个十来分钟。这条泥土阶梯,一层一层会经过几户原住民家。我们家不是本地人,父亲大学毕业后因为华侨成分的缘故,支边到广西,落实政策后才得以落定到这个城市。外来户与原住民之间多少还是有些隔阂的,但好在那时候大家都在一心一意解决温饱问题,穷困使人心思单纯,我们跟那几户人家相处融洽。唯独梁大富那家,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愿走近。听父母说起来,我们住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近五十岁的人了,又矮又瘦,穿得破破烂烂,几乎不跟人说一句话。而且,他神出鬼没的,有时好一段日子不见踪影,有时又几乎天天在家。我们小孩子为他编句顺口溜“梁大富,冲凉不脱裤”,是因为他总在屋门口的那个水龙头下洗澡,全身上下仅穿着一条阔大的短裤,光天化日,也不忌讳路人,一只干葫芦劈开做成的水瓢,接满水就往身上泼。“身上的皮肤又黑又皱,就像在浇一株干枯的石榴树。”父亲想到那情境还印象深刻。是的,他家门口是真有一棵看起来营养不良的老石榴树,结果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会去偷来吃。
“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那个梁大富啊,冲凉不脱裤子能洗干净吗?”我哥一问,我们全都笑了起来,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站在龙头下冲凉的梁大富。
说实在的,除了这句顺口溜,我对这个人再想不起太多。70年代,这般大庭广众之下洗澡,不会判有伤风化的罪?“所以大家都怕他。我都不敢正眼看他。”母亲说。
父亲告诉我们,梁大富是西江上的船员,一年里多数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概因为走船的人在船上洗澡都那样,上岸也改不了这个习惯。
噢,原来如此。
父亲说,其实他是个好人。
我们山上的那间小屋,左右无邻,屋背是山林。夏天的时候,不时会有蛇钻进我们家。父亲是个瘦弱书生,对付一下蚊虫和马蜂窝之类的倒没问题,但是面对吐信吹风的蛇,现在说起来都心有余悸。大概是我三岁的时候吧,梁大富帮父亲对付过一条正昂起头,在我家饭桌底下吐信的银环蛇。父亲捕蛇的事情,我听过很多次,有的细节还写进过小说里,但这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银环蛇有毒,父亲认得出来,迫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的是,当时我正坐在饭桌上,如同无知无觉的人质。母亲只能在门外朝山下喊救命。很快,光着膀子、穿着一条阔短裤的梁大富跑了上来,手上拎着一支粗竹筒。他先是朝那蛇扔东西,草帽、衣服、鞋子之类的,将那蛇的注意力引向自己。父母则在一边喊话,安抚我,将我的注意力牢牢固定在饭桌上。等到那蛇身游出桌底,梁大富几步冲近前,用力把竹筒准确地摁在了它的脖子上,瞬间制服了它。那条银环蛇,在梁大富的指导下,父亲将它去毒泡酒。四十多年来,我们家搬了几次,那瓶酒都紧紧跟随着我们。因为从小就看着那瓶酒长大,我倒并不觉得害怕。那条蛇蜷缩在玻璃瓶的底部,身体比擀面杖还粗,它盘踞得安详,颜色还鲜亮,蛇鳞还泛光,眼帘紧闭,看上去就像在冬眠。很多次,我看到父亲将那酒瓶抱出来,检查里边的酒下降了多少,又总会不忘用一块布擦擦玻璃,晃一晃,好像在跟那蛇打招呼。那瓶酒,不知道是忌惮蛇毒,还是作为一次蛇口脱险的难忘纪念,父亲从来没喝过一口,倒是被时光一点点地偷喝掉了大半瓶。
这么说来,梁大富还救过我一命,这个除了名字外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的人。
“那他现在在哪?”
“早就走掉了。”
也是凄凉的。80年代后期,我们这个小城,像港台流行歌一样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香港遍地有金捡,他儿子就真的跟着一群人,从西江码头上船,说是要去香港发财。一去便杳无音信。等不到电话普及到家庭,没过几年,梁大富就生病了,走掉了。这些,都是我们搬离老屋后发生的事情,母亲也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偶然从老邻居的口中听说的。
席间,一阵沉默。我从阳台的栏杆望出去,西江水倒映着大桥上的彩灯,一跳一跳的,灯柱顶端特意为欢庆春节挂上的红灯笼,把水面都映红了。江面上仿佛流动着一个城市,看起来比岸上更为热闹。从前,梁大富那个儿子就是沿着这条水路出发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地跟他的父亲道别,还是满脑子幻想着遍地黄金的新世界,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阔绰地回家孝敬父亲,只是夹在人群中,兴奋地跟父亲挥手“拜拜”?
望着脚下的河水,我逐渐走神。这条贯穿我们这座城市的西江,川流不息,迎来送往,在高速公路还没有开通之前,它还是主要的运道。跟那个年代里很多离乡的人一样,我出发到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城市广州,就是从西江码头登上“红星号”客船,顺着西江,一夜到珠江。二十四岁,对未知的新生活既兴奋又不安。是父亲送我去的。客船刚开进广东境内,他就拉着我到船尾,指着那个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的方向,郑重地跟我说:“现在梧州就叫作你的故乡了。”作为一个异乡人,我经历过的离别有很多很多次,但这次黄昏的离别深深印在记忆里。父亲这句话以及他说话时船尾螺旋桨搅起的阵阵巨浪,每当我想念这个城市这里的亲人,必定会在心中响起,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第一次为我定义了故乡,更重要的是,从那以后,我开始一次次经历送别的时刻,一次次体会分离的滋味。次数的增多并不意味着熟能生巧,相反,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甚至觉得送别变得越发艰难。在汽车站台边,在高铁闸口处,在机场安检口,我送父母,或者父母送我,从唠叨的叮咛逐渐变成无言的沉默,从依依不舍到复杂的不忍。最近几年,我都以父母年纪大了行动迟缓为理由,拒绝他们送我到站台,但他们从来都不肯,好像目送我消失在站台是为人父母必须完成的仪式。为了缩短送别的时长,我总是掐算好时间,几乎踩着点到达车站,有好几次,因为时间实在紧迫,我匆匆与父母道过别,便一路小跑进入安检处,留下他们在小车内透过玻璃窗看我消失在人群中。我发现这种道别的方法最轻松。往往是,当我惊魂未定地在位置上坐下,给父母拨个电话,内容全都在讲差点误车的惊险和刺激,就好像离别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甚至假装没有离别这回事。不过,当我安静下来,独自看向窗外,疾驰的火车将楼房、树木、河流以及整个城市迅速抛下,想到自己又一次将父母抛在原地,眼泪会掉下来。
一颗剥开的板栗放到了我的手上。“烤熟了,热着吃才香。”母亲挑出炉子上最先熟的那颗给我。小小一颗,却烫。我握着它,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没头没脑地说:“谢谢爸爸妈妈,把你们女儿养那么老。”一时间,母亲不知道怎么接话,气氛变得有点奇怪。我姐忽然拍了我一下,夸张地说:“我才没老呢,别把我算进去。”我笑着攻击她:“更年期了都,还不算老?”我哥接过话,表扬母亲:“啧啧,老妈,你们真厉害,把儿女一个个养到了更年期。”大家都笑了。父亲举起一只工夫茶杯敬母亲,我们也跟着举茶杯敬父母。空气中流动着木炭的气味、煮茶的陈香以及一种我定义为幸福的芳香。我想,这个围炉之夜必会是我日后无数个寒冬夜行的慰藉和动力。
第二天,姐姐的车在楼下等我们,说要带我们去石鼓冲转转,去看看那间山上的老屋。小城不大,车程也就不到三十分钟,很奇怪,自从搬离那里,我们就算很多次聊起,但却没想过回去看看。车子路过的那些地方,我大致还能认出来,医院、学校、菜市口……最后,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母亲指着那里一条安静的小道说,这里就是石鼓冲路口了。啊?怎么是条小道?我印象中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过去每天背着大书包上学放学,走得又饿又累。
等到车子兜兜转转找到当年那个上山的入口,我们都傻眼了。那座小山已经被劈掉了一半,就像梁大富那只葫芦水瓢一样,劈掉的那半边,就是通往我们老屋的一层层泥土阶梯。老屋,以及我们坡下的那几户原住民的家,荡然无存。望过去,那地方朝天升起了几栋淡黄色外墙的高楼,就像我们现在在城市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那种高层住宅,墨色的窗框在墙体上打着整齐的格子,空调统一困在一溜木框子里呼吸。参照剩下的那半边小山,高楼远远高出了我们每天哼哧哼哧爬十几分钟才能到达的老屋的高度。而那时候,我们一度认为再没有比我们住得更高的人家了。
停好车,我们四围走走,想努力捡拾些往日的痕迹。事实上,我们连走近那个地方都不能,楼盘将那半座山以及山下的一大块平地都圈了起来,我们只能透过种满凌霄花的围栏看进去,有花园,有泳池,一个老人推着婴儿车缓缓走着。小区的电子门禁前,两个保安正站在左右两盆硕大的金橘盆景边,腰上的对讲机不断发出一些电流声和含混的人声。我们竟然连老屋的照片都没留下一张,想到这个大家觉得很惋惜,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看看。离开之前,我们只好在小区门口拍了张合影,身后的背景,只有我们知道,是遥远记忆中的那间消失了的老屋。
围炉忆旧的温暖,那些纷至沓来的往事使我们变得更加亲密。在离开家的前一个夜晚,临睡前,我像过去喜欢做的那样,坐在父母的床尾,将脚伸进被窝,跟他们说说话。东拉西扯,也谈一些未来的计划。这是我跟父母最亲昵的时刻,这种时刻我会觉得自己变得很“小”,“小”到可以躺在他们怀里,“小”到可以胡说八道一些话。“妈,要是时间能停下来就好了。”“妈,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就好了。”这些无厘头的撒娇,我知道,是我在他们面前最大限度的松弛,或者某种虚弱的最大限度的坦露。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我轻轻收拾好行李,要出门赶最早的那趟高铁。这次在我的坚持下,好不容易跟父母商量好,只送到电梯口。不知道是因为昨晚聊太久,他们睡得太迟,还是因为安眠药的作用,他们还没醒。我悄悄走近他们床边,他们的鼾声在我听来像一首欢快的曲子,节奏诙谐。我忍住了笑,将手探进被子里,摸了摸床褥,暖暖的。在准备提着行李箱走出门口时,我忽然想起了他们养的那只大胖猫,又转回身,走向猫笼,伸手进去摸了摸垫在猫身下的棉布,暖暖的。猫的喉咙震动出咕噜咕噜的欢喜的声音。
在站台的前方,我等待的那辆列车呼啸而来,而另一条轨道上,一辆徐徐开出的列车朝它迎面而去,过往交错掀起了一阵强大的气流,新的生活劈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