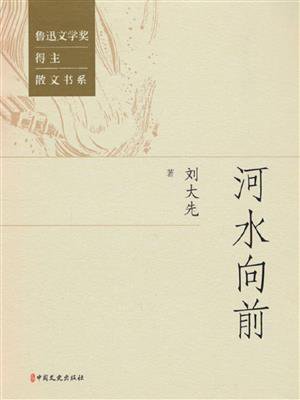青春做伴
一个人无论是权势显赫、声名远扬,还是卑微低贱、流离失所,无论是泯然众人、平淡无奇,抑或乖张邪僻、为世难容,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光华夺目、蓬勃葳蕤的时候,也是形成人生基本路径与模型的时候。就像罗曼·罗兰所说:“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我的青春时代是在芜湖度过的。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与生命中最光洁单纯的岁月联结在一起,在成长期塑造了我的情感与观念底色,以至于后来的所有选择和路向、光荣与失落、理想与追求,都打上了这座城市濡染的痕迹。在离开多年后回眸,内心里竟然隐约地怀有一种类似故乡般的甜蜜与惆怅。
1996年9月,我拖着一个大藤箱,从六安乘坐长途汽车去芜湖报到。现在因为有了沪陕高速和芜合高速,路上时间被缩短了一半,乘坐高铁的话居然只要一个小时。但在当时,车子在国道上晃晃荡荡要走大约七个小时,才到长江边上一个叫作二坝的地方,等着从裕溪口轮渡过江。
那时候我刚刚十八岁,从未到过江南,见到江岸开阔,绿草如茵,并没有感到一点点疲倦,心中只是兴奋不已。江水浩荡,轮渡仿佛一个隐喻,标示着一段崭新的生活即将在我面前展开,那是从原生环境中脱身而出,获得了自我与自主的自由感。
我的大学位于市中心赭山脚下、镜湖之畔,翻过宿舍边的围墙就是被称作“小九华”的广济寺,门口是一条小吃街,生活交通都非常便利。芜湖处于吴头楚尾之地,因为多湖塘沼泽,鸠鸟翔集,古称鸠兹,是江南鱼米富足之地,与长沙、无锡、九江并称四大米市。这是个婉约秀气的小城市,金马门、北门到马塘区一带的老城区,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划,但并不显得杂乱,倒是透着小家碧玉的模样。
沿青弋江到江口形成商业中心地带,号称“十里长街”。我刚到芜湖的时候,从冰冻街至女人街一带的长街,依然是小商品批发市场,曲巷阡陌,还是旧时模样。有些老巷甚至还可以偶然见到青石板街,两边是桐油板门的老店铺。
初见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但芜湖也并非只有这些历史的遗存,得地理之优势,近代以来发展为安徽最大的货运、外贸、集装箱中转港,芜湖造船厂、海螺型材和奇瑞汽车也都是叫得响的品牌。刚进校时,学校有个乐队叫“新人类”,唱重金属摇滚。每逢周末,就在西门附近由防空洞改装的地下娱乐宫里开演。几个穿皮马甲、带金属饰片的裤子,光头或脑袋上缠着布条的哥们儿抱着木吉他在那儿吼。他们第二年就因为毕业而解散了,却开启了我对于未来新世界的想象与向往。
一般人原先是把青弋江和长江交汇处的中江塔当作芜湖的地标建筑。张艺谋拍摄的画家潘玉良的传记电影《画魂》中,潘玉良离开芜湖,最后一个镜头就是给这个塔的。某种意义上,潘玉良可以看作芜湖的一个文化象征。把一个妓女当作芜湖的象征,并无任何贬义或不敬。事实上,潘玉良从江边的清倌人到驰名中外的艺术家,她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曲折的文化隐喻:一种屈辱中的奋进,软弱转而刚强,终成正果,留给人们的背影是乘船东去的青春的背影。我看过潘玉良的《春之歌》《静物》系列,颇得印象派莫奈神韵,又带有中国画传统的线描手法,简洁明快,甜美沉静——那应该是风雨过后的释然和圆融。
潘玉良的经历是一个富于诗意的绝妙故事——现实永远比虚构要复杂得多。故事的侧面是这个城市的风流,连浮华都显出了分量。不过浮华不过是表面,底子里芜湖是个重商尚文的城市。在我所走过的小城中,她称得上人文阜盛。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因欣赏芜湖的山水胜境,而在赭山广济寺中的滴翠轩内读书居住,研究诗文。现在安徽师范大学的赭麓校区内还有一个“松风阁”,便是源自黄庭坚的诗帖。赭山深处,那苍翠的松柏之后,有抗日名将戴安澜的墓,还掩映着安徽公学的遗址,它曾被人称作“安徽的北大”。1905年,陈独秀在赭山皖江中学堂和安徽公学教书期间,曾主办过《安徽俗话报》,传播革命思想。彼时与他一起在芜湖称得上一时俊彦的,还有李光炯、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章士钊、柳亚子等著名人物,他们留下的前卫之风,渗透在这个城市变革的影迹之中。
我上学期间,正是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的高潮,家里经济情况不好,课余期间总是找各种打工的机会。早上一般四点多就起床了,拎着热水瓶去教室或者图书馆待一天,晚上到人家去代家教,回来再到操场跑八千米,冲个冷水澡睡觉。一点都不觉得累,只觉得充实和快乐。暑假也不回家,在城中村租个房子打工,几年时间我跑遍了芜湖的大街小巷,像了解自己的发型一样了解这个城市的所有细节,它的隐秘的所在,它的脾性和它玲珑剔透的气质。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芜湖十二中当实习老师。校内有个大成殿,巍峨庄严,改作了学生的阅览室,里面有一块芜湖县学记碑,是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真迹。我觉得这个阅览室就可当作这个城市的不彰显而气自华的标志。
许多年过后,偶尔在回忆的时候会想,芜湖的气质是什么呢?
是一种鲜衣怒马、白衣飘飘的青春感觉。芜湖并不是开风气的那种城市,但绝对是开放的、敏感的,如同一个对外界充满好奇的少年。她灵秀轻盈而又生机勃勃,不拒绝任何变化,又有一颗真纯的内心。那是一颗自觉向上的青春之心,待久了,芜湖就成了青春做伴的故乡。
离开芜湖后,我到北京工作,很少回去,每每有机会,都会被一种近乡情怯的矛盾心情所阻隔。十几年后,我被母校邀请作为杰出校友给新报到的学弟学妹们做讲演,发现自己在这座曾经熟稔无比的城市已经不辨东西。城区扩大,建筑簇新,第一次过江的二坝已经成为鸠江区的一个镇,而现在的人们无须再等候轮渡了,长江大桥早已开通,芜湖甚至有了直达北京的高铁。
晚上一个人到以前曾经无数次徘徊逡巡的长江大堤上散步,看着长江滔滔东去,一如当年。想起与同学在江边唱过的Beyond的歌《无悔这一生》:“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息自强。”那是青春的信念与志气,像这个保持了清新与活力的城市一样,它没有消失。走到外面的世界,依然是一张不带风霜、朝气蓬勃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