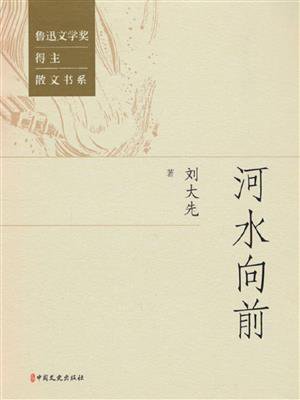北京生长
冰面冻得很实,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河面在午后的阳光下发出青灰色,偶尔可以看到小小的白色冰堆,那是钓鱼人开凿气孔时钻出来的碎末堆积而成。涌出的水重新冻结后,颜色要略深一些,青黑的水色,踩上去依然是梆梆硬,整个潮白河似乎都已经凝结成了固体。
远处零零散散有一些放鞭炮的人,时不时有沉闷的爆炸声,旋即消散在空气中,显示出天地间的空荡。除夕刚过没几天,正是料峭的时候,没有风,赭褐的堤岸上疏朗的树木如同铁铸般纹丝不动。
西南方向是高耸的燕潮大桥,这是一条新架的索桥,一边是燕郊,一边是通州。它对我来说是全然的新事物。我上一次来野游时,这里还是莽莽苍苍充满野气的地方。那已经是至少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我搬离通州之前,与老郑、大头一道。
他们是我的室友。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合住在杨庄的一个小区,紧挨着通州西站。那是一个老旧的小站,常常可以看到运送矿石与煤块的列车慢慢驶过。我不知道那些货物会被运往何方,在初来乍到的岁月中,夹杂着对陌生地方的好奇和新鲜环境的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可能也一样。
21世纪的最初几年,北京的地铁只有三条线,京通高速还很顺畅,早晨去建国门上班,坐班车只需要二十多分钟。我们都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不知不觉在一起度过许多光阴。我们结伴去平谷的玻璃台,去密云水库边吃垮炖鱼,到怀柔爬箭扣野长城,清早起床花四个多小时换乘各种车辆去爨底下,跑到房山看一座古老的佛塔……这些地方是北京的周边,扩大了的北京。
最常去的还是北运河的岸边,有时候是在傍晚的夕阳中,有时候是深夜的寒风里。荒草疾风,河水舒缓无波。2006年,宋庄新开了一个美术馆,举办纪录片展,去那里,还要费尽周折地找车。夜间结束时候,走在小堡空旷的街头,运送渣土的工程车卷起烟尘,一副开榛辟莽的城乡接合部模样。
宋庄处于北运河与潮白河之间,老郑不知道从哪里买了一辆二手皮卡,带着我们沿着曲折窄小的乡间公路一路向东,去潮白河边兜风。那些路还是北京郊野早年的样貌,跟华北其他地方的乡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经过支渠一座水泥桥,看到锈迹斑斑的生铁闸门立柱,仿佛还是“大跃进”时代的遗留物。潮白河畔的垂柳和白杨在晴空下,折射着跟一千年前同样的阳光。
夏日悠长,仿佛时日无尽,一切都在波澜不惊之中,但是世界已经慢慢起了变化。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对周围事物熟视无睹,它就变得既陌生又熟悉。时至今日,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在故乡的时间,似乎对它了如指掌,实际上不明所以,可能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到它的内心,只是在周边晃悠。
北京的内心很难一言以蔽之。我在建国门上班多年,单位对面就是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的古观象台,明清两代都是皇家的天文台,但我从来没有登上去过。这大约就是灯下黑。有时候午间休息,我会与同事沿着贡院西街往总布胡同散步,交叉口的地方就是赵家楼饭店,现在是部队的地产。略微对现代历史了解的人都知道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地。东总布胡同是北京的第一条马路,1913年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捐资修建。那是一条19世纪风格的街道,行人与建筑之间没有隔阂,行走中的人同两边的平房亲密无间。明朝时候叫“总捕胡同”,是总捕衙署的所在地。尽管时光变迁,今日依稀可见灰墙红门四合院的老北京影迹,静谧而安详。
总布胡同离老北京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住过很多名人,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好友逻辑学家金岳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费正清,人口学家马寅初,文学家张光年、刘白羽、萧乾、赵树理、严文井,画家董希文……这是一个缩影,北京内城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累加了无量记的历史,以至于当我们想在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需要剥开沉积岩一样的时间叠层。
人们印象中的老北京大多数都是对于旧北平的影像与文字记忆,它们由一系列典型的意象组成:鼓楼上响起的鸽哨,皇城根下四平八稳的京腔京韵,卤煮火烧驴打滚、豆汁焦圈门钉肉饼的护国寺小吃,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四合院……平民的踏实自在与悠闲趣味,同神秘威严的皇城禁地形成对比,成为被刻意雕琢与渲染的京味儿。
然而,我知道它们都是一种逝去了的念想,一种怀旧情绪里的恋地情结,承载了关于家园和文化的想象。但即便在旧时,北京也并不是单维度的,四合院间穿插的紫禁城、大宅门、寺庙道观与祭祀坛台,代表了它另外的一面,那由八百年前建城伊始便集聚的权力、贵胄、武功和信仰的层面。在1949年后,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建立的各种大院与单位,则又是一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混杂之城。
更何况还有我们这些新世纪到来的异乡子弟。
我所见到的北京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初中毕业的小姑跑到北京玩,留下了爬长城的照片,上大学的舅舅到北京游学,在天安门前留影,他们给我的印象同书籍与电视中看到的差不多,那是高度精练了的象征性文化符号。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继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又一个巨变的时期,人口、信息与金钱的流动,让这个城市迎来了波澜壮阔的生长期。
及至我开始定居北京工作,北京还在90年代的延长线上。在从通州无数次的通勤路上,我目睹了八里桥周边兴起的地铁站,不知不觉中八通线开通了,四惠道边光秃秃的河岸不知道何时竖起了一座仿古的牌坊,高碑店的乡村建成了焕然一新的民俗街区。
在准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各种基建项目和文化设施开始蓬勃兴起,于我却是后知后觉。我那时候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业余时候去亚运村那里的一家媒体兼职,从外网上扒拉英文资讯,翻译整合成中文文章,发表在香港注册的杂志上,根本没有心思去关注外界的变化。老郑去美国探亲,在得克萨斯的农场上挥舞着镰刀砍草。大头报考了英国大使馆的文员。我在电脑上安装了Rosetta Stone软件,自修法语,并没有明确的意图,也不知道学了又有什么用,就是精力旺盛的副产品。
我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赶去三里屯参加天涯网友的年终聚会,带上海过来的同学去北海游玩,去蓟门桥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家中拜访,接待来自福建的一个会计,他对于宋词的鉴赏让我敬佩莫名……很多时候,去这些地方是外来游客的保留节目,万人如海,我们都像微不足道的旅人。我们的北京,在王城的四野。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分房子的福利,二环旁边龙潭湖边的房子虽然也才三四千块钱一平米,我们也买不起,甚至没有那个意识。老郑后来在昌平一个村庄买了一个房子,我和大头换乘几次地铁到西三旗,再找公交车,从上午走到下午,才赶到那个叫作踩河新村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北沙河北,都快到北六环了,但那也是北京。我去过的更远的地方是长哨营和喇叭沟门,已经快到河北丰宁了,白桦树林中的满族乡,据说当年是专为向京城皇家供应造扎枪用的杨木杆的军事后勤基地。大头的房子靠近台湖,那个地方产一种莲藕,秋冬季节会有外乡人到开冻的淤泥中来挖。我的房子在常营,据说因明朝开国将领常遇春的兵营得名,是穆斯林比较多的地方,小区的前方还有一座清真寺。我们四散开来,异乡的种子落在北京的田野生根。
郊野的生活节奏不快,远远赶不上北京的生长。它的生长速度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更为显著,在我出国一年半于2011年再回来时,明显感觉到地铁拥挤不堪,有时候甚至都挤不上,到了冬季,偶尔还会看到乘务员用膝盖顶着帮乘客推进去,就像在东京地铁上的情形差不多。越来越多的人从燕郊赶到CBD甚至金融街去上班,有的时候通勤需要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北京地铁的线路已经十倍增长不止,它们作为城市的血管和肠道,吞吐着血肉,更新着肌体,依然免不了会时不时发生一些梗阻。
被人像货物一样推进充满各种体味的车厢,肢体镶嵌在肢体之中,簇拥着难以动弹,无疑不是很好的体验。自己驾驶汽车,上下班高峰拥堵在如同停车场般的高速公路上,同样让人难以忍受。房价在2008年之后飙升,是异乡人最为沉重的负担。租房子则很可能面临房东不定时加价或者以各种理由要取消合同、流离失所的苦楚,抢夺共用盥洗室的焦灼。我没有租房子的经历,但是在百子湾、石佛营见过衣着光鲜的白领那凌乱简单的住所,在皮村见过农民工简陋的工棚。交通、住所、医疗、子女教育……大城市的烦恼不止一端,缘何人们还要趋之若鹜呢?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大城市具有虹吸效应,人们麇集而来,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这当然并没有错,但不过是从经济理性上进行的抽象概括。在具体的个人那里,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同我一样,不过是在命运的无奈中抓住有限的机会,就像大风吹过山岗,树木的种子能落到什么地方并不由自己说了算。落在哪里,就拼命扎根、发芽。在那种远离原生文化的奋斗中,一个人会体会到自己英雄般前行的担当与精进,会有脆弱与孤独的时分,也会有欣喜与奋发的时刻,他(她)从精神到肉体,慢慢都会跟这个城市发生一种亲密性的关联。
刚来的时候,我对北京的冬天一无所知,甚至都没有羽绒服。宿舍的暖气烤得我鼻子干燥出血,我觉得空气浑浊,总是把窗户打开,东北人大头就会觉得头被冷风吹得疼,为了窗户的开关我们还吵过好几次架。有一个隆冬清晨,当我走过车公庄的过街天桥,赶去一个打工的地方时,寒风吹彻积雪,穿过单薄的衣服,眼泪不由自主地冻出来,那时候我才深刻感受到北京的风有多硬。早先我在江南会冲冷水澡到元月窗外飘雪,到北京第二年适应暖气后就再也无法接受刺骨的冷水,回到南方老家已经吃不消门户大开的寒气了。我确乎被北京改变了,于我而言,它不再是屏幕或者明信片上的风光与地标,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21世纪初年的北京目睹了无数人向自己走来,而它也正是在新鲜血液的关注中飞速成长。我曾经对北京在20世纪的城市意象流变做过一番考察,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它显示出颟顸迟滞的面孔,城市里住满了老官僚与新学生。在本土文人和外来的旅行观察者眼中,它一度呈现出死气沉沉的面貌。抗日战争时更是沦陷在日寇手中,它那多年首善之区所形成的隐忍与顺从,更是让它饱受耻辱与摧残,灿烂的文化只留存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与想象之中。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龙须沟那样的乱葬岗臭水沟才会被改造成一个宜居的处所。皇宫成为普通人都可以观览的景点,广场则成为群众聚集的空间,从复兴门到木樨地的“新北京”也完全是一派人民城市的风貌。作为首都与政治文化中心,它打破了“南贫北贱,东富西贵”的格局,扩张了“大圈圈里套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着个黄圈圈”的结构,代表着全新的国家形象,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
在改革开放的初年,“京味”被发掘出来,成为某种地方性文化的特点。我曾经参加过北京语言大学合作的一个课题,研究京味文化的演变和“新京味”的流变。但北京既是地方的,却也从未局限于地方。那些怀旧式的文艺作品中的大宅门往事或者小市民生活,那些典雅雍容的腔调或者平易顺畅的美学,只是一种文化景观,并不能引起我更多的兴趣。在地方文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掌故,比如魏公村是维吾尔(Uighur)的音转,中关村原先是专埋太监的“中官村”,望京本是北方进入辽国的最后一个驿站,可以遥遥望见京城了……诸如此类各个地方都有的风物地名传说。这些知识增广见闻,饶有兴味,却不能引发人的共情。
我相信,北京在被称作燕都、渔阳、广阳、幽州、燕京、中都、汗八里、京师、顺天的时候,并不是今天所说的那种“京味”——它只是晚近不到四百年间的一种阶段性的现象,接续了早年的遗产,经过了五方杂处后的创变。这种创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北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兼容并包和融合创新。如今徜徉在大望路附近,谁也不会想到它在建国时不过是一条沙石铺就的小路。华贸中心的前身是国华电厂,金地中心原址是一个酒厂,二十年间,天翻地覆,长出了流光溢彩的国际化写字楼与装修豪华的购物中心。石景山的首钢搬走之后,开辟了冰雪汇和科幻产业创新中心,酒仙桥的老工厂成了798艺术区,定福庄那些建于50年代的房屋被改造成了1919创意产业园,那些早期工业化时代的遗迹烙上了崇高美学的色彩,直观地呈现了新世纪北京的迭代升级。
北京有那么多的不好,至少在我看来,本地菜很难吃,春天风沙遍地,夏日燥热难耐,秋天萧瑟而短暂,冬季漫长又寒冷。但有这一样好就行了,所有人来自所有地方,谁也不会特别在意谁,谁也不是中心。这带来了难得遵循自己心意生活的自由,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各种角落驻足,构成了与新时代北京同生而共进的主体。他们多样性的生活让这座古老的都市充满活力。大头原来是学计算机情报的,但后来攻读了儒学。老郑本科时候是学中医的,研究生考到北大学比较文学,后来做印度研究。这些都不是符合世俗期待的选择,北京的博大提供了容纳的空间。这里有富人惊人的财富,也有穷人无望的挣扎,有平庸无趣的小市民,也有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有坚固的科层制,也有无限开阔的自由。万人入海,才能融有一身之藏。
身在其中的人往往很难窥破所处环境的真相,对于一个地方只有离开后的回望才会重新加以认识。当我在2021年离开北京,一年异地的生活中,时常会想到它。也许,对于北京爱恨交织的情感,一直潜伏在伴随它生长的过程之中。这一年的末尾,我得知了老郑骤然离世的消息。自从大家从通州分开,我们很少联系,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这个消息依然让我长久无法释怀。那种复杂的情绪并不容易厘析清楚,就像我以为我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回望之中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个分子。
离开通州的最后一个夜晚,收拾停当已是深夜。我在小区的路上游荡了一会儿,坐在一架秋千之上轻轻地摇荡,想着,我们都已经是北京的血肉,是我们赋予了它骨血与精气。
当我再次回到曾经与老郑游荡过的河边,不免想起以前的种种。他是那么强壮、豪放、生机勃勃的一个山东大汉,没想到会突然消失了。我们在这里欢笑,哭泣,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如果他要是同游,面对脚下的坚冰,一定会想法子找个乐子。
我搬来一块石头,对着一处冰面使劲砸下去,一下,两下,只是留下了白色的印迹。远方一处河流洄弯处,阳光在冰面上晒出了一层薄薄的浮水,也许那里会最先融解吧。河边的柳树也会再次发荣滋长,北京则还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