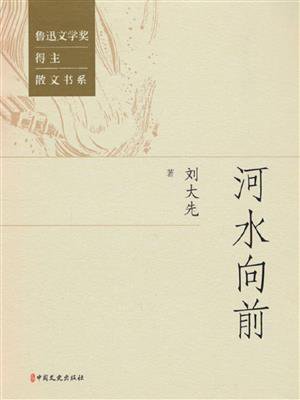125 街
到纽约之后,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白天到学校上课或者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到136街租的宿舍睡觉。我曾经跟朋友概括为“白天116,晚上136”——地铁1号线的116街是哥伦比亚大学,137街则是城市学院站(City College)。
尽管中间只隔了二十个街区,但是116和136显然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二十个街听起来似乎很长的样子,其实走起来顶多也就是二十分钟——而把它们分开的就是125街。125街是个东西贯通的大道,站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125街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北面有个Mink Building,上面写着“Where downtown meets uptown”。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哥大也就是上城了,但是如果从文化心理上来说,过了125街才是真正的哈莱姆的上西区。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125街绝对是个值得做个民族志的地方。在我没有来之前,就听到有关此地黑人的种种可怕传闻。不过136街并不是黑人的聚居地,这里大多数住的是拉丁裔的二代移民,除了在周末喜欢开着大音响开派对之外,倒也老实。
第一次去125街,是一个从俄克拉荷马过来的朋友喊我一道去那里的一个店买东西。他带我绕了半圈,顺着阿姆斯特丹大街走到125街,我很奇怪为什么不从城市学院那里直接穿过去,他说那里不安全。半路看到一个建筑上写着“哈莱姆之心”,却是个救火队。然后就是著名的阿波罗剧场,据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他去世的那段时间,整个125街都是直播车。此时经过还可以看到附近的墙上都是涂鸦签名,最大的当然是:迈克尔·杰克逊!这一块就是哈莱姆区的中心了,街道两边遍布着各种各样贩卖图书光碟、印度香料的小摊和各类人物。
经过第七大道是一个小广场,我看到一个穿着西服、挺胸向前、颇有些革命风范的雕像,夜色中看不清。走近了发现,雕像底座写着Jr.Adam Clayton Powell。坐在上面的两个老瘦的黑人冲我挤眉弄眼喊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就在那里自得其乐地呵呵笑。我打算过去细看一下雕像介绍的文字,室友不让我过去,说这里是流浪汉的天堂,我们走快点。Powell是第一个进入国会的非裔,1945年至1971年是纽约曼哈顿哈莱姆区国会议员,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和劳动委员会主席。2002年,他被非裔学者阿桑迪(Molefi Kete Asante)写入一百个最伟大的非裔美国人名录中。
哈莱姆区名声在外,到现在,在我们这些外来者眼中还是个充满危险和怪诞事物的地方。真相什么样子,谁知道?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个器宇轩昂的高大女黑人,仿佛祭师一般头戴巨大的纱巾,手抱一本厚书,穿着奇艳,拖了个行李箱。室友说,这不知道是从非洲还是从哪里来的呢——好像这个女人的出现恰恰证明了此地果真如他所说,是个怪胎遍地的所在。
其实哈莱姆的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也并不很久,直到20世纪初年,这里其实还是富人区。最初在这里定居的是荷兰殖民者,然后是法国和北欧的殖民者后裔——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弗兰德式老建筑,以前荷兰富人的住宅,如今充满了墨西哥、波多黎各的移民和我这样的亚裔留学生。
好莱坞电影勾勒一般人对于纽约的浪漫与自由的想象,但是当我每天走在路上,看到那些肥胖无比、走路两个屁股都几乎要挤得咯吱咯吱响的黑人时,现实会直接暴击而来。我也因为拜访同学去过几个贫民黑人家中,氛围总让我感到压抑和恐惧,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理偏见造成的。正好这期间第八十二届奥斯卡颁奖,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叫作《珍爱》( Precious )的电影。这是个残忍的故事:1987年的哈莱姆,底层的黑人少女,肥胖、丑陋,被母亲无端责骂,被父亲强奸生子,然后,她还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从学校里逃离,却无法逃避生存的环境;心灵短暂在幻想中抽离,身体却只能无休无止地在现实炼狱中饱经折磨。
女孩的名字叫作“珍爱”,这是语言命名对象征世界的反讽。她并没有被任何人珍爱,她被同样是底层黑人的街头男孩毫无来由地羞辱。家庭也不是港湾,社工带来的温情无法进入腠理。那个惹人讨厌的母亲说:“我活得太累了,你是为爱你的人而活。”珍爱说:“爱没有给我任何好处。爱殴打我,强奸我,骂我是畜生,让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让我恶心。”
皇天无亲,天地不仁;没有体恤,缺乏关爱:这就是残酷生活的本来真相。我本来不喜欢此类“被嫌弃的××的一生”式的苦难叙事——这种惨剧的哀痛及至麻木的经验,在中国的历史与源远流长的苦情戏中,已经出现得太多。《珍爱》还是能让我注意,主要是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无数类似于珍爱以及她的母亲那样的臃肿、木讷、行动缓慢的黑人。以前通过片段知识结撰出来的有关黑人的不无偏见的刻板印象,在謦欬相闻中慢慢改变,对于从耳闻得来的想象渐渐及于亲身观察的同情。
如今的哈莱姆与《珍爱》里的三十年前自然有所不同,但是显然没有那么大,依然是少数族裔的聚集地,只不过可能多了些拉丁裔混居,当然中国人也不少。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低阶层、低收入、少数族裔、有色人种。
不过中国人大多是留学生或者做生意的移民,勤奋苦干,仿佛是新一代的模范公民“陈查理”。其他族裔就我个人所见,基本陷入一种绝望之中。我的邻居们似乎大部分没有工作,整天游手好闲,也没有钱去酒吧或者其他娱乐场所潇洒,只能在门口闲晃聊天。晚上很晚,他们还三三两两地在街上晃悠——不是波德莱尔说的巴黎街头的有产阶级的或者艺术家哲人式的“游手好闲者”,它们仅仅是晃悠,没有目的,没有激情。这样的环境与1987年珍爱的生活环境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三十年过去,好像人物还像那些人物,氛围还像那个氛围。
《珍爱》改编自一位街头艺人兼黑人学校的教师萨菲尔写于1996年的小说《推动》( Push )。导演丹尼尔斯说:“黑人在美国永远是少数族裔,永远是二等公民。别看现在美国有了一个黑人总统,但是非洲裔的黑人还是备受歧视。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别的公共设施的享受上,都要比白人差上好几个档次。我拍摄这个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原著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二是希望人们来重视黑人的生活、黑人下一代的教育和心理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萨菲尔的这本名为《推动》的小说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亚历克斯·哈里的《根》。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移民而言,祖先和家族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他们是如何被运送到北美大陆来做奴隶的,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当下的生活。”
这话是不错,但是所有的“当下的生活”其实都是有“根”的。比如我们在《珍爱》中所看到的父亲强奸女儿的情节,这种骇人听闻、让人齿冷的兽行,如果仅仅从个体精神人格或者黑人群体伦理方面来看,固然不无道理,却仅是肤浅的人云亦云。很久以来,有关黑人的好色、野蛮、暴力、道德匮乏的刻板印象已经通过舆论领袖和大众传媒日益深入人心了。如果不去寻找其深层的根源,那不过是在为这个世界的话语侵犯多加了一层帮凶而已。
孤立地看许多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的当代社会现象,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而其实它们的根源早已植于历史的某个节点,如同潜伏的病毒,草蛇灰线,绵延至今,时或不时地在岁月的苍穹下肆虐张扬。它们平时掩藏在社会的皮肤之下,踪迹不见,一旦当特定的温情面纱被撕破,它们就会露出狰狞乃至恐怖的面孔。当代社会生活的无数侧面都显示了这些文化无意识的存在,125街的当代现实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1862年9月,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第二年又正式命令解放奴隶。但是黑人并没有得到政治权利,也没有得到土地。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了对南方的军管,并扶持废奴势力进入州政府,但是黑人的生活却不比战前好:一方面是突然得到公民权,但是经济上根本没有独立,无法维持生活;另一方面,白人种族歧视反而变本加厉,以至于出现了像3K党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整个19世纪后期,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受到州和地方歧视黑人的法规和惯例层层约束和限制。在日常生活中,美国黑人常常被隔离开来,不能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甚至在一百年后仍然和奴隶一样被剥夺各种权利,他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与国家的发展并不相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似乎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是当年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平权法案》如今面临重重危机,贝尔大法官甚至提出重写当年作为民权运动成果的经典布朗案,因为该案的判决虽然在纸面上推翻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制,现实中却承诺了很多,实现的很少。
回到《珍爱》中父亲强奸女儿的情节上来,我和专门做美国少数族裔研究的一位教授聊过,她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美国的黑奴时代,黑人男女是不允许正式结婚生活在一起的。当然,奴隶主很快发现奴隶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是一种奴隶制的稳定因素,能降低黑奴为争夺女人而发生的打斗,并能削弱他们逃跑的意向。但是,如果奴隶家庭形成牢固的纽带,又是与他们的地位不相适宜的,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威胁,并会在出售奴隶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奴隶主试图将奴隶的家庭纽带保持在不至强大到干扰奴隶制本身的限度内。他们不准奴隶使用姓氏,甚至连奴隶使用“我姐姐(妹妹)”或“我母亲”这样的称谓都可能遭到惩罚。
这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黑人文化中家庭观念的淡漠,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家庭观念与主流文化比如基督教文化中家庭观念的差异。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乱伦在其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严厉的禁忌。延及今日,虽然掺杂了诸多当代更为复杂的性别、经济、欲望,以及欲求不得满足与寻求弥补等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奴隶制在形成这种道德伦理观念中所起到的深刻的作用和影响。这是种族主义隐形的历史遗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并不是说合乎趋利避害的正义,而是说都可以从历史的复杂语境中得到合理性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才是一切有为的变革的开端。《珍爱》里的黑人父女的乱伦放在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话语中,只不过是一个细小的节点,如同衣服上的一个毛刺,但正是这个毛刺,骚扰着、刺激着整个机体,让它瘙痒、隐痛、不舒服。不理顺这个毛刺,就休想安宁。
125街就是纽约的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