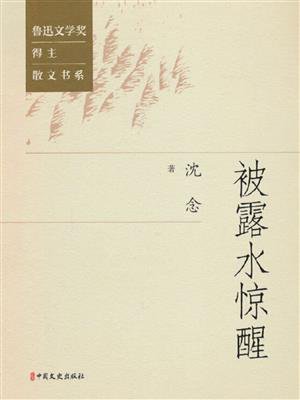流水函关
是黄河这条道路引领着我抵达这里的。
东西南北中,行走中原大地,万物都沿着黄河这条曾经的历史中轴线而生长。从这里,黄河进入中游峡谷的下一段,北为晋北,南为豫西。黄河也因山就势,硬生生将南北走向的水流折弯成东西走向,完成凌空俯瞰时“几”字的弯钩书写。这是潇洒的一笔,这条大河流到这里,有了节奏、矜持,也有了坠落、跨越。行走的水,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源头昆仑山和星宿河,经黄土高坡到豫西塬上,走多远,就走出多少条道路。最初的道路必然就像这条九曲回肠的河流。或者可以这样替黄河代言:每一条道路都经过且通向我。
我该怎样描述“这里”。此刻,它是离三门峡市区三十六公里的灵宝市,是灵宝市往北十五公里的王垛村。再往前追溯,是夸父逐日渴饮河渭弃杖化为邓林之地,是紫气东来、鸡鸣狗盗等故事传说的起源地,是战国秦孝公从魏手中夺取的崤函之地……如果我愿意,还可以说出数十上百种关于“这里”的定义。
人们称谓“这里”为函谷关,它的名字就是它的身世。东去洛阳、西达西安的故道,所要穿越的崤山至潼关段,几乎都是在山涧峡谷之间,人行此中,如入隧道般不知深险,古称函谷,险隘之意,如此贴切的命名再没改变过。有传说是西周,武王伐纣至于牧野,大胜而归,置关于此,又专设司险管理关塞;也有一说是秦孝公战胜后选择了最险要的这一段来重兵把守。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的战场,可不是要建一个好看的景点、划一个瓶颈似的边境,而是兵家必争、胜负定夺之地,是国君与枭雄一争高下、开创与终结一关定论的象征之地。这也才有了“天开函谷壮关中,万谷惊尘向北空”“双峰高耸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战场”的浪漫诗性与现实抒怀。
如同黄河在我抵临之前就已经流淌多年,这座耸立眼前的关楼栉风沐雨,变了颜色,成了时间里的事物。我当然是这样以为的,但人们告诉我这只是80年代后期起在原址上新修扩建的。现代旅游,将它打扮得阔绰而招展。所剩无几的原址,风雨历经的原址,却留在了黑白图片中。寻古访古却不可得古的人,会滋生怎样的失落?我却又释然了,它既是一个旅游园区的核心,也仅是诸多景观的一分子。如同历史上有关它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身影构成,却又只是一颗大宝石上的一个切面。风云际会,屡毁屡建,屡建屡毁,是它必然的命运。但就在这里,即使剩余一片空旷,留下的只有片瓦独木的想象,那也是荡气回肠的。
我从广场上穿过,脚步急切,仿佛要赶赴着消失的时间去抢先一步。北邻的黄河,奔流不停,没有人能走到水的前面,又怎能超越时间呢?绕过园区高耸的塑像,飞檐翘角的楼阁,保持年代原貌的屋舍,重点保护的纪念物,我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地踩在被熙攘人流踩过的步行道上。移步即景,道道帷幕拉开,却还不是我想要见到的古关遗址。园区里栽种了很多树,玉兰、木槿、国槐、小叶女贞,我欢喜地辨认着它们,却忘记询问哪是最古老的一棵。人若能站成一棵树,也是幸福至极的。又有些恍惚,仿佛所有的树都是过去的人,每一次枝动叶摇,都是微笑或沉思。也许从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它们,而是市井喧嚣、袅娜炊烟、南来北往的口音、疲倦却压抑不住兴奋的面孔。
无楼不成关。没有关楼,也成就不了这片被时间永生讲述的土地。
我是绕了一大圈然后从西侧登上关楼的。关楼四面,独西边的砖墙斑驳、风蚀得显明。青砖砌垒的缝隙透出潮湿浸磨的花白。我回头抬望,几棵高大的柏树枝条旁逸斜出,半面墙被重叠的庞大树影所遮蔽。是否成为这面墙尤其风蚀的原因呢?没有人回答我的疑惑。关楼是双门两层,东西走向,楼上有两座三层悬山顶四阿式的木塔,遮风挡雨,塔尖雕刻着一对相互凝望的丹凤鸟。关楼是这片新广场上的唯一建筑物,耸立、气派、庄严,建筑风格倒不多见。古代的生命故事,多是发生在河流、古道之上,或是边界的关楼。函谷关的特殊地理位置契合了它们,南接秦岭,北倚黄河,东西或绝涧或高塬,它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揪心之处,就在于那么多人想通过它、占守它。它是阻滞、关闭,也是畅通、开放。
在这里,有一件事是不能回避的,那便是历史的追溯。无论藏在哪个角落,历史的风扑面而来,情绪的力量在历史的托举下,让去往函谷关的路变得跌宕起伏。已经没有了路,那条我想看到的历史之路,被广场上崭新而巨大的石板所覆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修建,关楼只是历史的指代物的化身,过往痕迹被抹去。直到眼前被一尊黑色石碑身后的函关古道所打开。在古代,那只是一条在沟谷中蜿蜒的土路。有记载说这条曾经崎岖狭窄、蜿蜒相通的路全长十五华里,沟壁有五十米高,坡度有四十到八十度,有的地方仅两米宽,仅能容一辆牛车通过。车不方轨,马不并辔,人行其中,如入函中。并非夸张的描述,可以想象出它在军事战略上的利害。战争从遥远的春秋战国就开始了碰撞,直至秦国一统,函谷关扮演着决定胜负的关键角色。西汉贾谊在名篇《过秦论》中议论:“于是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好一个“逡巡而不敢进”!函谷关之险也暴露在“不敢”二字里了。
然而到了公元前209年陈胜义军过关交战,刘邦绕关灭秦,项羽使黥布破关,怒而焚关,函谷关又为秦的灭亡画上了一个终结的句号。自此往后,进退之间,是“逐鹿中原”,也是“入主关中”,这八个字里藏着千钧重量和血腥杀戮。再去拨开时间的密叶,沿经“安史之乱”中的桃林大战,闯王李自成激战斩敌明兵部尚书孙传庭,1927年冯玉祥北伐驻防,直至1944年5月中国军队阻挡日军侵略西犯的函谷关大战,都绕不过此地。太多与函谷关勾连的历史细节需要赘言叙说,铁打的雄关流水的战事,山河之险,悬隔千里,长治久安的险固倚仗,得失之间均因这里而起。这里,并非只是一座青砖砌起的城楼,而是一条真正通往时间深处的道路。也许它从来都是道路,如同它倚临的黄河,连接的不只是一个个地点,而是可追溯的来处、可前行的去往,是立体变幻的时空,也是后人用来想象自我的原点。
这条看不见的道路,更远的地方,是远方,也是远去。
过函谷关,从一个向往,忐忑的未知,就此变成了一种情绪。函谷关留有秦、汉、魏三处,汉关在洛阳新安县,魏关因三峡拦洪大坝修建而被淹没,秦关的历史当然是最长的。通往秦关的路不断被覆盖,也不断被呈现,是延伸的呈现。走到这里,仿佛已经走了很多年,应该徒步,不只是看看路途的风景或肤浅的探察,更是要从历史的踪迹中学会思索。鲁迅在1924年的暑假来过这里,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邀请他到西安讲课,归途中他来到了灵宝县。他在日记中写下:“九日晴,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做纪念。”那是一次短暂的停留,“略泊”二字里,他会想到些什么呢?他历来以为思考是大于世俗生活的。是欣喜、怜叹?是流连、彷徨?古关是帝王将相的觊觎,征服的对象,荣辱成败的要塞,也是平头百姓的向往,富庶安逸之门,仿佛是经由此地,过关斩将,鱼跃龙门。生活是人书写和创造的,函谷关的历史亦然。鲁迅离去,那二枚黄河石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唤起他对函谷关的回忆吗?
从古道上走过太多的出关者,但有一人不能不提。他的到来被记载在公元前491年的农历七月。当时的函谷关令尹喜,据说他某天清晨起床第一眼看到了东方的紫气,“知有异人过是”,他等来了这位八十高龄的老者——东周守藏史老子。这位又名李耳的老人骑着青牛,被他的崇拜者热情地挽留下来著书立说,也就有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也许连函谷关也没想到的是,在经历那万千厮杀争夺之后,被封堵在深井里的血液如岩浆般依旧汩汩流动,帮它加持的还是当初这位眉宽耳阔、目如深渊的老人。一块精致的黄河石被供奉在纪念祠屋的一侧,千客万来的手掌在石头上抚摸而留下一层光芒的覆盖,已无人探究石头的年代和书桌的真假,却只为老子完成著述出关后的“莫知其所终”而好奇与叹惋。
叹惋那散落时光里的,与一个人、一座关、一条河有关的秘密。谁能说,任何普通渺小的生命,不会经由这片流经黄河的土地而变得绵长、宝贵和荣耀。万生万物,万情万事,所繁衍的,不都是讲述不尽的黄河故事?
黄河在北,隆起的土塬隔阻了函谷关的视线,静寂中流声传来。古关与长河,都把各自烙刻在对方的骨骼之上。这条大河,微微发出声响,都是振聋发聩的轰鸣。我所抵达函谷关的短暂时光,能亲密地感应到从四方八面汇流而至的那些流声。流声里,有风貌之变,也有愿景之欢,桩桩美好落色为图——筑坝建库后的水波清粼,生态改良之后的天鹅栖息,挣脱贫困后的喜乐安宁……中原大地上的万千气象、幕幕大戏皆可沿着这条大河遇见。河流之上的备忘与注脚,被时光拍打的浪花卷起,众生命运虽有千差万别,然而黄河故事依旧到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