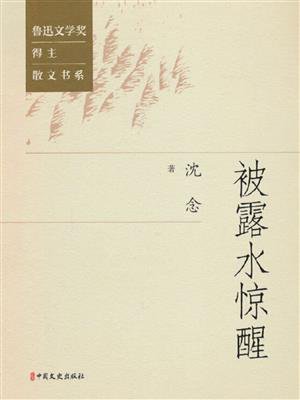无界之地
那是一道不为人察觉的蓝线,将西峡老界岭上的分水岭观景台一分为二。
神奇的是,方寸之地,如同中轴般的蓝线,晴蓝色的标尺,却是界线的存在。像一座隐形的屏风,或如一堵透明的城墙,把空山来风阻隔在了蓝线一侧。
河南老作家李天岑拉着我的衣袖,让我感受风从哪里来,风又如何不见了。
站在海拔一千八百九十米的分水岭上,因为这道蓝线,我成了一个天真的孩子,惊喜地从线的左边跳到右边,又从右蹦向左。如果这是界线,此时我就是一位越界者。这一边,是风很劲道地吹向我,闭上眼睛,衣服、头发、皮肤,被席卷的风吹拂着,颇有御风而行的轻盈。那一边,是风平息了,藏匿了,退却了,阳光灿烂,松林静止,睁眼四探,风都回到了丛林深处,回到山岭被岁月摩挲过的万千褶皱之中。
每条褶皱,仿佛都是一道神奇的蓝线,是时间刻在大地上的裂缝,藏着不同的来历与过往。
地处豫西南边陲、豫陕鄂三省交界的老界岭,是“世界地质公园”伏牛山上的一个隆起,形成于十八亿年前的震旦系,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分界岭。大地行走,被冠“分界”之名的山川河流不少,但老界岭与众不同。它是中央造山系缝合带保存最完好的地质遗迹标本,有着“中华脊梁”的美誉。也有人感慨“天上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就是隔着这道山岭,两条哺育华夏文明的河流虽不相见,却能倾听到对方的心跳。跳动的,是波涛、骇浪,是时光的历史,也是每一滴水的传说。
那个叫小吴的年轻女孩,是景区新来的工作人员,她眼波含笑、温声细语地讲述老界岭的“出生史”。我听明白了那个传说: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就隐居在伏牛山,“老”既是历史久远的确定,也是一位特立独行者的介入。而“界”的来历,地理上有着清晰的指认——是中国南北的界山,是南阳和洛阳两座古城的界山,也是长江、黄河的界山。这个“界”,是耸立,是标识,是南北气候的过渡,也是动植物在此生养栖息的自然分庭与无缝衔接。长江、黄河流域以岭为阻断,喊山喊水,相逢又分别,溪流、河流,支流、干流,各奔东西,又各得其所。
我关心的风从何而来缘何消失,很快也从地理特征上找到了回答——来自中国北部、西伯利亚平原的寒冷气流自北向南流动,与自南向北流通的沿海湿热暖气流相遇,万里迢迢,山高路阻,平均海拔高于北部山脉的老界岭变成了一道屏障,劳顿奔波的两股气流行进至此减弱殆尽,相逢一笑,握手言欢,就有了山岭上的北面有风、南面无风的奇特现象。
这奇特,是一道蓝色弧线的奇特,是秦岭—伏牛山逶迤延宕归于老界岭的休止,也成就了西峡地貌最深广和厚重的褶皱。这奇特,裹着山石骨架、土木肌肤、河流血浆,裹着变化跌宕、风霜雨雪,也裹着万物生长、日光流年。此时此刻,风起风停,思绪也飘飘落落,古往今来那些经历过同一时刻的人们,在听不到任何声音的凝固瞬间,是否都是完成一次对生命的指认,展开对世界和给万物命名的想象。
遗憾的是,站在老界岭上,左眺右望,却没看到水的踪迹。奔腾与湍流、蜿蜒与潺湲在这里消隐了。老界岭像一个巨大的迷宫,把水都引流到视界之外了吧。要知道,西峡河流众多,奔赴长江的丹江水系的一条主干流鹳河,就在境内穿山绕林,纵南贯北,而大小河流五百多条,像羽翼状地匍匐在崇山峻岭之间。这些羽翼般的水流,汇成三千一百五十七平方公里的水源区,让西峡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第一大县,占到了河南省的百分之四十。盛大的水与惜惜溪流,要奔赴遥远之外的水,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水,在这道“界”前止步,分道扬镳,不能相认。水的命运在此被分界。但谁又能说,它们不会在天空、大海见面,在人的身体里相遇呢?
原以为分水岭是老界岭的制高点,却被告知对面的主峰犄角尖海拔两千二百一十二点五米。犄角尖上有八角凉亭一座,被丛林拥围点缀,颇有诗情画意。这个与河南境内最高峰平起平坐的高度,是老界岭的得意,也是西峡的气势。秋光洒落,南方山岭的葱郁热情与北方的苍浑隐忍,一并呈现,如经纬一次镶金嵌银的漂亮编织。向远方致意,视界所囿,西起陕西商洛、东至方城垭口的莽莽伏牛山只可看见模糊的轮廓。人在天地间的渺小,看见是最不可述说的,但在眼界、心界之外却有着无尽的想象。
观景台上,有两个别具匠心悬空固定的画框,人立于框中,以山岭为背景,拍出的肖像之作皆报以满意且惊喜的赞叹。有飞鸟入框,又很快一掠而过,在山岭背后消失。它也是这里最无顾忌的越界者。从山谷到天边,飞鸟眼中,没有界限,也没了大地的身影。任何“界”在飞翔的翅膀之下都形同虚设。人没有翅膀,脚下踩着的每一片落叶,发出清脆的折断之声,提醒着人们身居何处。回望上山的索道,车厢吊在半空,循环往复,早已把山间风景看遍,也成了被人看的风景。索道也是一道“界”,行走被工具取代,足迹被天空抹去,时光陷入寂寥。
山中四季更替,颜色渐变,一夜之间,一场风雨之后,你是无法精准找到那个时间界点的。季节深处,有界亦无界。正如深秋此刻,秋后无霜叶落迟,千年银杏、国宝连香、杜鹃、红豆杉、七叶树等植物散落在起伏坡岭,鹅黄、淡黄、橘黄、银灰,镶着水绿、亮绿、碧绿、墨绿。色彩的层次与差异,是大自然的巧心与天赋。没有哪一个季节是最美的,也没有哪一个季节是不美的。小吴笑着说,她是疫情刚结束后来老界岭报到的,经历的夏天秋日,各有其美,又美美与共。毕竟这里考证出种类繁多的植物达到了两千二百多种,二十三万亩面积的老界岭,在这个数字里堆垒着一个南北植物共生的多样性植物基因库,熏染出季节之美,也制造着休闲避暑的“天然氧吧”。
茂林修竹,山岭沉寂,却压不住植物们内心的喧腾。老界岭盛产的一千二百多种天然中药材,算是植物中的另类。数量已然庞大,更令人羡慕的是纳入药典目录的名贵中药材有一百五十多种,认证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山茱萸产量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七十,成了声名在外的“山茱萸之乡”。药凝天地之气,既是治病、救命的,又承载着医圣之源。相传后世奉为医圣的南阳人张仲景多次沿山访病采药,是在西峡找到了五味子、朱砂根、柴胡等草药,尤其是寻到了山茱萸。山岭沟谷大概都回应过这位曾“踏破铁鞋”的医圣如获至宝时的欣喜呐喊吧。山路上脚印深深浅浅,留下他很多的逸闻:遇老猿切脉治病得万年桐木回赠,制古猿、万年古琴两尊;以袪寒药材、羊肉熬煮,用面皮包成“娇耳”帮穷人治冻疮耳,后被人们仿效成包饺子过年以示感激与纪念……远在湘水畔,也有他的故事流传。某年疫疠流行期间,面对许多慕名前来求医的贫苦百姓,当着长沙太守的他,心中是隐隐作痛的。他也许是最没有官老爷作风的官员,脱下官服就成了宅心仁厚的医者,热情接待,悉心诊治每一位病患。求治者越来越多,他起初是公务结束之后回家中把脉问诊,后来索性在府堂之上坐堂就诊,被后世传为佳话。这位越界者,后来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跨越理论与实践的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大量有效方剂的记载,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临床诊法,不就是中医的灵魂所在,打破并疏浚身体内的界限与壅堵。
从依山而建的仲景宛西制药厂离开,不能不惊叹医圣所留下的有形无形的财富。这里建起了百草园和山茱萸、地黄、山药、丹皮、茯苓、泽泻六大中药材基地,研发出了上百种中成药产品。药材好,药才好,这是西峡山野的骄傲。淡微的药香从百草园散出,也是从山野的一草一木之间生发出来的。我嗅着草木芬芳,探寻着脚下的路,那些向远处生长的路,要通往何方?有的是年复一年踩出来的古道,也有后来为了游览便利修的栈道。沿着它们中的任何一条,都是踩在时光的脚印之上。
老界岭所属太平镇的党委书记打趣地与我们“算账”:新鲜空气、优质饮用水折算成“年收入”,比城里干部实惠得多。这笔别处无法产生的收入,背后支撑的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八的森林覆盖率,是平均每立方厘米三万六千个的负氧离子含量。观景台宣传展示的奇峰、怪石、云海、雾凇、犄角尖佛光等,是摄影家的守候与游客的偶遇。山岭变身“海”中岛屿,日光穿透薄雾,金光如离弦之箭,落在老界岭上,就成了清风松涛,拂晓绿遍山冈,夜静星繁,倾听一片萌芽。这也是城里干部“嫉妒”的。太平镇上,开门就见山,见山就是景,活在风景里的人才是幸福的。
到西峡两日,在这北方之南,或说是南方以北的地方,都是沿着伏牛山脉这条界线在行走。古史记载中的西峡,“秦楚孔道,豫陕咽喉”“陆通秦晋,水达吴楚”,且“山产百货风行,千里万商云集”,是秦朝商鞅的封地。这位变法者也是一位越界者,但他更多的是在设计并立起规则之界。也许他至死也未能明白,界之所在,也不是非此即彼,也并非界限清明,世界本是一次圆融贯通的交汇。
云朵在日光下飘移,把简朗的影子投在山岭上,如悬挂着又一道抽象派褶皱。只有站在高处,才能看清褶皱的模样,理解褶皱的存在意义。西峡正因这些褶皱而有了可叙说之处——
山南水北,是古鄀国属地,楚国都城丹阳的白羽邑,有着争议的屈原出生地;屈大夫“扣马谏王”、秦楚丹阳古战场等传说与遗址,重阳文化发源地的积淀勾织着历史的纵深;以恐龙蛋化石原始埋藏状态为特色的恐龙遗址,折叠成亿万年计的沧海桑田,留给我们探察天体演变、地球灾变的一条时空秘径。我仔细观察那些在玻璃柜里展出的恐龙蛋化石,被命名诸葛南阳龙的骨架标本,来自白垩纪的礼物,消失者留下的备忘与签名。
褶皱是魔术师,手中的红布一抖,重现眼前的山麓下的那些自然村庄,在宁静缤纷的秋色里,流动着被时光之手改变的新农村风貌——丁河猕猴桃小镇,六个村庄近三十平方公里绿水青山的成片种植,生长的就是“金山银山”;五里桥白庙村的农游一体,映现在庭院夜色的喜悦灯火里,而那条流光溢彩的“星光”大道,点亮的是乡村旅游振兴的未来;二郎坪的养蜂业、双龙的百菌园,踏上的是脱贫攻坚带动两千多贫困户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让人感慨的还有一条与伏牛山脉平行的文化之脉,串联起西峡、嵩县和陕西商洛等地,涌现出当代文学史上乔典运、阎连科、贾平凹等名家、大家。老界岭有界,西峡却是无界的。大自然永远是最神奇的所在,中原大地上的包容、厚德、和谐,一种偏爱,造就西峡的山水人文于无界之中,如同岁月的潮,退到远方,也涌向远方。
界碑,界限,疆界,边界,界石,界河,越界……我在这里领略“界”的差异,峰与石,林木与草蕨,人与自然,时光与生命,自由与限定,又都是同一个世界。当我们沉浸其中,会发现生之悲欢离合,如同老界岭上的草木一秋,水滴石穿,万径人踪灭,春风吹又生。世间万事万物,看似有界,亦无界,眼中有界,心中无界。人所执守和跨越的,追逐与放弃的,拥有与失去的,都是在“有界”与“无界”之内酝酿积存,在“此界”与“彼界”之间涅槃重生。
索道下老界岭,脚重新踩在大地之上,天空的蓝与分水岭上的蓝于眼前闪动又退去。无界之地,遮无可蔽,山岭间的清风和色彩涤荡胸中情绪,块垒瓦解,齑粉纷飞。发发呆,或是出神,都那般美好,如同聆听老界岭讲给喧嚣尘世的自然课。时光长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经历着什么,拥抱的依然是大地之上共同仰望的浩大星空。西峡之行的收获恰是在一次老界岭的攀山越岭之中显影。这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个流连的身影,每一寸泥土之上萌茁的生灵,发出酣梦中的呼吸,都在讲述中被记刻和叨念,莅临者也因此享受着越界之后内心盛纳广袤的欢欣,像是在做好飞翔姿势之后,等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