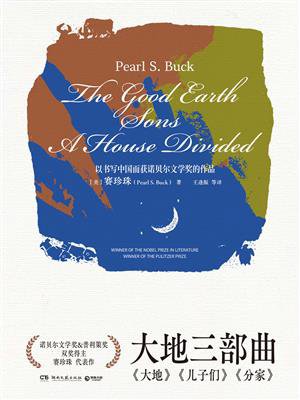十一
王龙用两块银圆付了三百来里路的车费,而收钱的售票员还找给了他一把铜钱。路上,车刚停,一个摊贩便把货盘伸进了车厢的窗子,王龙用几枚铜钱买了四个小馒头,还给女儿买了一碗粥。这比他们那时好几天吃的东西还多。虽然他们饿得急需食物,但吃的东西一到嘴边却变得毫无食欲,他连哄带骗,男孩子才肯下咽。但老人坚持着用没牙的牙床吃着馒头。
“人一定要吃,”火车隆隆向前滚动时,老人兴奋地说,对周围靠近他的人非常友好,“我不在乎我的傻肚子这些天没吃东西已经变懒。我一定得吃。我可不想因为肚子不愿意干活就白白死去。”人们对这个微笑着的干瘪的小老头突然发出了笑声,他的白胡子稀稀疏疏地长满了下巴。
王龙没有把所有的铜钱都用来买吃的。他尽可能留着,以便他们到了南方可以买席子,搭栖身的窝棚。火车上有些男人和女人以前到过南方;有些人每年都到南方富有的城市去干活,为了节省饭钱还沿街乞讨。王龙习惯了火车上的种种奇妙之处和车窗外田地飞快旋转的惊人奇观以后,便开始听车上这些人在谈论些什么。他们正以炫耀聪明才智的态度聊着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首先,你要弄六张席子,”有一个人说,这个人嘴唇粗糙下垂,像个骆驼嘴似的,“席子是两枚铜板一张。可是你得学乖,举止别像个乡巴佬,要是那样,一张就会要你三枚铜钱,那可不值得,这些我都清楚。我不会上南方城市人的当,哪怕他们是富人。”他扭扭脑袋,看看周围,想听到人们的赞赏。王龙急切地听着。
“然后呢?”王龙催促那人说下去。他蹲在车厢的地板上——那种车厢只不过是一间木头造的空屋子,没有可以坐的东西,风沙穿过地板上的裂缝钻了进来。
“然后,”那人放大了声音说,声音高过了下面铁轮的隆隆声,“然后你把席子连在一起搭个棚子,再出去讨钱,要紧的是用泥土和污物把你自己涂抹一下,让人看了觉得你可怜。”
王龙活到现在还从未向别人讨过钱,他不喜欢到南方去向陌生人讨钱的想法。
“非得讨钱吗?”他重复问道。
“啊,那当然,”“骆驼嘴”说,“你要吃过饭再去。南方人米多得很,每天早晨你可以到粥棚花一文钱吃饱肚子,白米粥能吃多少吃多少。那时你可以舒舒坦坦地去讨钱,讨了钱买豆腐、青菜和大蒜。”
王龙从其他人身边挪开一点,转身对着墙,偷偷用手在腰里数数他剩下的铜钱。够买六张席子,每人吃一文钱的粥之后还剩三枚铜钱。他感到宽慰,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但是,伸出一只碗向过路人乞讨的想法仍然使他不安。让老人和孩子去乞讨,甚至让他女人去,这还可以的,但他自己有一双手啊。
“男人有两只手,就没有活干吗?”他突然转过身问那个人。
“有,有活干!”那人蔑视地说,往地上吐了口痰,“要是你肯干,可以拉富人坐的黄包车,跑的时候你会热得流汗,站在路边等的时候你的汗会冻成冰贴在你身上。我宁愿去讨钱!”他胡诌了一通,王龙也不想再问他什么。
不过,那人说的一番话对他是有好处的。火车把他们载到终点站,下车以后,王龙已经盘算好了。他把老人和孩子安顿在一家宅院长长的灰墙脚下,让他的女人看着他们,自己便去买席子。他边走边打听市场在什么地方。起初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这些南方人说话的声音又尖又脆。好几次他向别人打听而又听不懂的时候,别人就不耐烦了,于是他学着去找一些慈眉善目的人。这些南方人是急性子,很容易发脾气。
他终于在城边上找到了席子店,他像知道价钱似的把铜钱在柜台上一放,扛了席子就走。孩子们一看见他便哭叫起来,他看得出他们在这陌生的地方感到害怕。只有老人愉快而惊异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事物,低声对王龙说:“你看这些南方人,长得多胖,皮肤多么白嫩油润。一定天天吃肉。”
但是过路人谁也不看王龙这一家。在通往市里的石子大路上,人们来往不断,只顾忙自己的,从不看一眼旁边的乞丐;每隔一会儿就有一队驴子经过,小蹄子在石路上踏出清脆的嗒嗒声响,它们的背上驮着一筐筐盖房子用的砖块,或者一大袋一大袋的粮食。赶驴的人骑在最后一头驴的身上,手持一根鞭,一边吆喝一边在驴背上甩出啪啪的鞭声。赶驴的经过王龙时,个个都向他投以蔑视、高傲的目光。他们穿着粗糙的工作服,走过站在路边露出惊讶神情的一小堆人,那模样比王子还要高傲。这是赶驴人的特殊乐趣。他们觉得王龙这一家非常奇怪,因此走过他们时便甩响鞭子,划破空气的清脆鞭子声吓了他们一大跳,赶驴的见他们吓成这样便哈哈大笑。两三回以后王龙恼了,他离开路边去找搭窝棚的地方。
他们后面的墙边,已有一些人的窝棚搭了起来,但谁也不知道墙里头有些什么,也无法知道。这堵灰墙伸延得很长,砌得很高,靠墙根的小窝棚看上去颇像是狗身上的跳蚤。王龙仔细观察那些已建的窝棚,然后开始不停地来回摆弄席子,但用苇管做的席子很硬,不好定形,他失望了。
这时阿兰忽然说:“我会做。我小时候做过,还记得。”
她把女儿放在地上,把席子拿起来这么拉拉那么拽拽,然后搞成了一个垂到地面上的圆形棚顶,高低适合人坐在底下而不碰到头。在垂到地面的席子边上,她用附近的砖头压住,又让男孩子去捡了一些砖头。窝棚搭好之后他们走进里面,把她留着未用的一条席子铺在地上。然后他们坐下来,算是有了个住处。
他们这样坐着,面面相觑,似乎不相信他们前天才离开自己的家园,现在已经在三百多里之外了。那么远的路至少要走几个星期,而且,不等走完有的人肯定已经死在路上了。
这时,他们深深感到了这个地区的富足,在这里,看来没有挨饿的人。王龙说“让我们出去找找粥棚”,他们几乎是高高兴兴地站起来的。他们又一次走了出去。
这次,男孩子边走边用筷子敲打饭碗,因为碗里立刻就能装上吃的。他们很快发现为什么窝棚都靠着那堵长墙:墙北头不远有一条街,街上走着许多人,手里拿着碗、盆和空罐头盒之类的容器,正在朝为穷人设的粥棚走去,粥棚设在那条街的一头,离墙不远。于是王龙一家人混进这群人当中,一起来到两个用席子搭建的大棚,每个人都向大棚开口的一面挤去。
每个大棚后面都有用土坯垒起的锅灶,那样大的灶王龙从来没有见过。灶上放着铁锅,铁锅也大得像小水池似的。当木头锅盖掀开时,煮着的好白米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冒出一团团喷香的热气。人们闻到这种米香,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他们一大群人全都向前走去,又喊又叫,母亲们又急又怕地喊着孩子,唯恐他们被人踩着,婴儿也不断地啼哭。这时掀开锅盖的人喊道:“人人都有,大家轮着来!”
但是,什么都挡不住这群饥饿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像动物一样争抢着,直到抢到。王龙陷在人群当中,只能紧紧拉着他的父亲和两个儿子,当他被拥到大锅前面时,他把碗伸了过去盛粥,盛满之后扔下铜钱。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站稳身子,粥盛好前绝不能被人挤出去。
他们又回到街上,站着吃他们的粥,他吃饱了,碗里还剩着一点,他说:“拿回去晚上吃吧。”
但附近站着一个人,像是这地方的警卫,因为他穿着特殊的蓝镶红的衣服。他厉声说:“不行,除非吃下去,否则不能带走。”
王龙不明白,说:“我已经付了钱,吃了还是拿走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人接着说:“这是规矩。有些狠心人,来买救济穷人的粥——只出一文钱——他们把粥带回家里去当馊水喂猪。米是给人吃的,不是喂猪的。”
王龙听到这话非常吃惊,他喊道:“有这样的人!”接着他问:“为什么有人这样给穷人吃的?是什么人给的呢?”
那人答道:“这是城里的富人和绅士给的。这样做有的是为来世做好事,救人性命,积阴德;有的是为名声,让人说他们的好话。”
“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好事,”王龙说,“有些人一定是出于好心才这样做的。”那人没有回答,王龙便又为自己辩护说:“好心人总是有的吧!”
那人懒得再与王龙说话,他转过身,哼起一种懒洋洋的小调。孩子们拉了拉王龙,王龙便带着父亲和儿子回到他们搭的那个窝棚,躺了下来。他们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这是从夏天以来他们第一次吃饱肚子,而且他们也太困乏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定得设法弄点钱,因为头天早晨买的粥已经用掉最后一枚铜板。王龙看着阿兰,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不是像看他们光秃秃的田地时那样失望了。这里,街上有吃得很好的人来来往往,市面上有肉有菜,鱼市上的桶里有活鱼,这样的地方绝不可能让一个人和他的孩子们饿死的。这里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家乡,在那里,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吃的东西了。阿兰坚定地回了话,仿佛这就是她熟悉的生活:“我和孩子们可以讨饭去,老人也可以。看到他满头白发,人家会给的,看到我们不一定。”
于是她把两个男孩子叫到跟前。毕竟他们还是孩子,只要有吃的便把什么都忘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们跑到街上,站在那里观看路过的人。她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个碗,这么拿着,这么喊叫。”
她把空碗拿在手里,伸出去端着,悲凄地叫道:“好老爷——好太太!发发善心吧——做好事积阴德呀!你扔一枚铜钱,救救快饿死的孩子啊!”
两个男孩子和王龙都惊异地望着她。她在什么地方学会这一套的?关于这个女人,有多少事他还不知道呀!看着他惊异的眼神,她说:“我小时候这样讨过,而且讨得到。那年也是这样的荒年,我被卖去做了丫头。”
这时一直睡着的老人醒了,他们给了他一个碗,四个人一起出去沿街乞讨。阿兰开始喊叫,把她的碗伸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她把小女孩塞进裸露着的怀里,孩子睡着了,她走的时候孩子的头一会儿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随着她伸到人们面前的碗而不停地摆动。她乞讨的时候指着孩子大声喊叫:“好心的先生,好心的太太,给点钱吧——这孩子要死了——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吃的呀——”女孩子看上去也确实像已经死了,她的头一会儿摆到这边,一会儿又摆到那边。于是,有些人——好几个人——不情愿地丢给了她一些小钱。
但过了不久,男孩子把乞讨当成了游戏,老大还有些害羞,乞讨时竟腼腆地咧着嘴发笑。他们的母亲发现以后,把他们拖进窝棚,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顿耳光,气愤地责备他们:“你们能一边说饿一边发笑吗?你们这些笨蛋,活该挨饿!”她打了又打,打得自己的手都疼了,他们满脸眼泪呜呜哭泣。她让他们再出去乞讨,对他们说:“现在该懂得怎么要饭了!你们再笑,我还要狠打!”
至于王龙,他走到街上,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出租人力车的地方。他进去租了一辆,说好价钱是当天晚上付半块银圆,然后他便拉了人力车上街。
身后拉着这么个两轮木车,他觉得人人都把他当傻瓜。他那笨拙劲就像第一次套上犁的牛一样,几乎迈不开步。可是要挣钱谋生,他还非得拉着跑不可。在大街上,不论什么地方,人力车送客人都得跑着走。他走进一条窄胡同,那里没有店铺,只有一些私人住家的门关着,他在胡同里拉着车走来走去,想熟悉拉车的窍门。他感到绝望,想想还不如讨饭去,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穿得像教员似的长者走出来向他招呼。
王龙一开始就想告诉他自己是个新手,不会拉着车跑,但那老人是个聋子,一点都听不见王龙的话,只是平静地挥手叫他把车杆放低,让他上车。王龙照他的意思办了,但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觉得必须按那老人的意思做,他是个聋子,而且他穿得很好,看上去很有学问。老人在车上坐直,对他说:“去夫子庙。”然后他直直地坐在车上,显得非常平静,那平静的神态使人无法再问。于是王龙仿照别人的架势往前拉车,他根本不知道夫子庙在什么地方。
他边走边打听。那是一条很拥挤的街道,小贩们提着篮子走来走去,女人们都在市场上买东西,另外还有马拉的车和许多像他拉的那种人力车。街上到处摩肩接踵,根本不可能拉着车跑,所以他尽可能快走,但总觉得他后面的车在笨拙地咯噔咯噔跳动。他惯于背东西,不习惯拉车,没等看见夫子庙他的胳膊就疼了,手也磨出了泡来,车把和锄把磨的不是一个地方。
到了夫子庙门口,王龙把车杆放低,老先生走出来,在怀里摸了摸,掏出一个小银圆给了王龙,对他说:“我一向就给这么多钱,你嫌少也没用。”说完他转过身向夫子庙里走去。
王龙根本没有嫌少,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这种银圆,也不知道能换多少铜钱。他走到附近一家能换钱的粮店,店家换给他二十六枚铜钱,这使王龙对在南方挣钱这么容易感到惊奇。站在旁边的一个人力车夫在他数钱时凑过来问他:“只给二十六枚呀。你给那个老头拉了多远?”王龙告诉他,那人喊道:“真是个抠门的老头!他只给了你一半。你开始跟他要多少?”
“我没有要,”王龙说,“他说‘过来’,我就去了。”
那个人同情地望着王龙。
“真是个乡下人,还留着辫子!”他向周围站着的人喊道,“有人说要他去他就去了,这个傻子里的傻子,根本不问‘你给多少钱’!要知道,傻瓜,只有拉白皮肤的人可以不争价钱!他们脾气像生石灰,他们说要你去你就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相信他们。他们都是笨蛋,什么东西什么价钱,一点都不懂,只会像流水一样花口袋里的洋钱。”周围的人听着,都哈哈笑了。
王龙没有说话。确实,他觉得自己在城里人当中显得低贱无知。他一声不吭,拉着他的车走了。
“不管怎样,这些钱够我孩子明天吃的了。”他心里固执地想着。但这时他想起了晚上还要付车的租金,现在实际上连一半都不够呢。
那天上午他又拉了一个客人,这次他跟人讨价还价,讲妥了价钱。下午又有两个人叫他拉车。但到晚上,他数了数手上所有的钱,付过租金后只剩下一枚铜钱。他非常痛苦地往窝棚走去,心想:做了一天比田里活还苦的工,只挣到一枚铜钱。这时,他对土地的思念像洪水一样涌入他的心里。这一天倒是奇怪,他一次都没想到过他的土地,但现在,想着他的土地躺在遥远的地方等着他——他自己的土地——心里便平静不下来。他就这样想着,回到了他的窝棚。
他回到窝棚以后,发现阿兰一天讨到四十个小钱,差一点有五枚铜钱,大的男孩子讨到了八个,小的讨到十三个,加在一起够付第二天早晨的粥钱。只是他们要把钱收集在一起放的时候,小的哭着要留下自己的,他喜爱自己讨来的钱,夜里睡觉手里还攥着,谁也不给,后来还是他自己拿出来交了他那份粥钱。
老人什么都没有讨到。他一整天都非常老实地坐在路边,没有开口。他坐在那里睡觉,醒过来就看看路过的人和车,看累了就又睡去。他是长辈,谁也不能说他。他看到自己双手空空,只是说:“我耕地,播种、收割,我是这样来装满饭碗的。我还生了儿子,儿子又生孙子。”
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就像一个孩子那样相信他现在不会再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