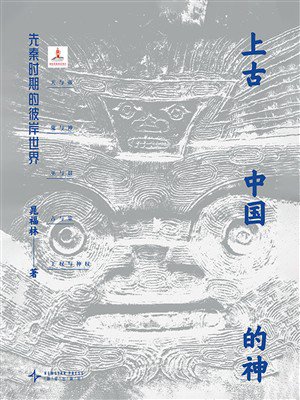前言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们就喜欢在河岸边冥思苦想。《论语》载孔子站在河岸看着逝去的流水,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 他慨叹时光流逝,去而不返。后来的庄子站在秋水浩荡的河岸观望对岸,说道:“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2] 他没有关注流逝之水,而是慨叹彼岸之远而模糊不清。一般来说,彼岸即指河湖江海之对岸。在佛教用语里则指一种超脱生死的境界,与“涅槃”相近,指脱离尘世烦恼,修成正果之处。如唐白居易诗云“闻君登彼岸,舍筏复何如” [3] ,僧皎然诗云“脱身投彼岸,吊影念生涯” [4] 等,“彼岸”皆指脱离尘世的境界。彼岸世界不仅是人们死后的世界,而且是极远的人不能至的所在,说它是渺茫的诗与远方,亦不为过。
在人们的印象里,彼岸世界多指一种虚拟的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迹不可至的极遥远处所,也指人们死后的世界,后来的“天堂”“地狱”之类的概念与此颇有关系。中国上古时代,在很长的时段里,神与鬼原本是不分的。人死为鬼,先祖既是鬼,又是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人们的观念里,“鬼”的地位下降,“神”的地位上升,两者才趋于分离。在以后的观念中,神所居在天上,鬼则居于荒郊野外或某个偏僻之处。然而他们皆生活居住于彼岸世界。先秦时期的人们认为上天是彼岸世界一个伟大所在,神异之人可登天梯而上达于天。据说昆仑山和高大无比的树木皆有天梯的功能。《山海经》谓有十名神巫皆可“从此升降” [5] ,《诗经》谓“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6] ,可见著名的周文王是可以陟降于天地之间的。《山海经》一书所记不少神奇的国度,神人和奇异怪物甚多,它们皆生活在人们所虚拟的彼岸世界里。
听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说,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有著名的哲学三问,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解答前两个问题已是非常麻烦,第三个问题则更难回答。包括“我”在内的人们要到哪里去呢?当然在此岸世界里。要去生活,要去奋斗,然而所有人最终必然要到彼岸世界里去,正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泰)山,或轻于鸿毛。” [7] 他看出了人从此岸到彼岸世界跨越的价值与意义,提出了为伟大事业奋斗的思想。人在此岸世界为伟大事业而奋斗,死而无憾。那么,死后呢?表面看来可以得到长眠安息,但在虚拟的彼岸世界里,人不仅可以过日子,而且还可以完成在此岸世界未竟的事情。《牡丹亭》剧里的杜丽娘与梦中情人幽媾于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她死而复生,经过奋斗与有情人终成眷属。《李慧娘》剧里的李慧娘在冤死后还魂,救出她喜欢的裴公子,并怒斥奸相贾似道。虚拟的彼岸世界在传说中,与此岸世界似乎只一线之隔,桥若不能过,还会有喜鹊帮忙搭一座桥让牛郎与织女相会。彼岸世界的神仙羡慕此岸世界的繁华,也可以到此岸世界来体验生活,七仙女和修炼成仙的白蛇的故事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通人,也可以看见在彼岸世界的亲人,苏轼梦见逝去十年的妻子,见她在“小轩窗”旁,“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江城子》)。《聊斋》一书可谓是写尽彼岸世界风景的伟大作品,其间的鬼狐神灵,无不折射着此岸世界的景象。人们对于彼岸世界毕竟还有许多清醒的认识,所以陶渊明有“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之说,陆游有“死后元(原)知万事空”(《示儿》)之叹。
先秦时期人们所虚拟的彼岸世界十分广泛和复杂。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所载的鬼的居处与人并不遥远,似乎某个黑暗的角落就是他们的居处,他们可破墙穿屋,就在人们附近。当然,在先秦时期人们所虚拟的彼岸世界里,祖先神灵和一般的鬼神还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重点。礼书所载频繁的祭典和琐杂的仪节,就是一个证明。本书所涉及的只是先秦时期人们所虚拟的彼岸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此岸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是关于彼岸世界探索的基础。人们对于虚拟的彼岸世界的丰富想象和探寻,永远不会停息,古往今来对于彼岸世界的幻化描绘,不仅反映了人们想象力的丰妍,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思想的发展、探索力量的进步。
晁福林
2024年9月7日
[1] 《论语·子罕》。
[2] 《庄子·秋水》,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六下,中华书局,1961年,第561页。
[3] 《和李澧州题韦开州经藏诗》,《全唐诗》卷四四一。
[4] 《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全唐诗》卷八一六。
[5] 《山海经·大荒西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7页。
[6] 《诗经·大雅·文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六,中华书局,1980年,第504页上栏。
[7]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