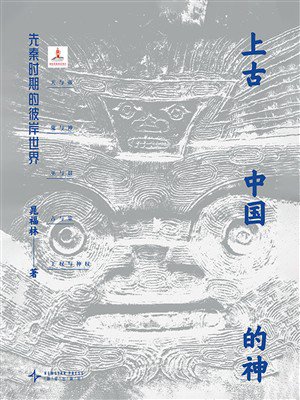附录
《山海经》的“天虞”和“天台”
《山海经》一书载上古传说,时代渺茫,不易索解。今就其所言“天虞”与“天台”二事,试作解析,以供专家研究时参考。《山海经·南山经》的“天虞”当读为“天吴”,系传说中的水神。《大荒南经》的“天台”一条,“高山”当与其后的“海水”相系连,意指天台之广阔。兹就这两个问题,试说如下。
一、“天虞”
《南山经》有“天虞之山”,郝懿行据晋人所撰《广州记》,认为即夫盧山,“天虞、夫盧字形相近,或传写之讹”
[1]
。按,这两个字不易讹误,郝说疑非是。“天虞”疑当读为天吴。虞、吴两字古音同字通,如《论语·微子》“虞仲”,当即吴仲,清儒刘宝楠说:“‘虞’‘吴’通用。……仲雍称吴仲雍,故或称虞仲。”
[2]
《史记·孝武本纪》“不虞不骜”索隐云:“何承天云‘虞’当为‘吴’……与吴声相近,故假借也。”
[3]
清儒钱大昕说:“古文虞与吴通,汉碑亦有‘不虞不扬’之文。今《封禅书》作‘不吴’,乃后人据毛诗私改。”
[4]
在《山海经》中,“天吴”见于《海外东经》,谓“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其形象是“八首人面,八足八尾”;又见于《大荒东经》,是一位“八首人面,虎身十尾”的“神人”。两个记载一致,可以肯定天吴是传说中的水神。依《山海经·大荒北经》“风伯”为司风之神的例子,则水伯当是司水之神,古人常将风雨连称,《大荒北经》即谓“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之说,疑“水伯”也是像“雨师”那样的司雨之神。若此则可与《南山经》所谓祭龙神之说相符合。《南山经》说:“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作为“龙身”之神,与传说降水的龙神(亦即水神)是一致的。难能可贵的是,殷商卜辞中有以犬祈雨的记载,与《南山经》所云“其祠皆一白狗祈”相合。《甲骨文合集》第31191片,这版卜辞包括四条卜辞,依次是“三豚此雨”“
 犬一此雨”“二犬此雨”“三犬此雨”。这四条卜辞皆贞用豚或犬求雨的事。卜辞中的“此”字当用如“则”,是承接连词。
[5]
卜辞问是用三豚为祭品就会下雨,抑或是用一犬(或二犬,或三犬)为祭品就会下雨。总之,《南山经》的“天虞之山”,天虞当即《海外东经》及《大荒东经》作为“水伯”的天吴。《南山经》所说用“祈”的方式处理“白狗”,用以祭祀“天虞(吴)”,清儒毕沅说“祈”字当读若“
犬一此雨”“二犬此雨”“三犬此雨”。这四条卜辞皆贞用豚或犬求雨的事。卜辞中的“此”字当用如“则”,是承接连词。
[5]
卜辞问是用三豚为祭品就会下雨,抑或是用一犬(或二犬,或三犬)为祭品就会下雨。总之,《南山经》的“天虞之山”,天虞当即《海外东经》及《大荒东经》作为“水伯”的天吴。《南山经》所说用“祈”的方式处理“白狗”,用以祭祀“天虞(吴)”,清儒毕沅说“祈”字当读若“
 ”,袁珂引用此说为释。
[6]
于省吾论证了文献典籍中“
”,袁珂引用此说为释。
[6]
于省吾论证了文献典籍中“
 ”字假借为幾、刏、祈等,这个字在甲骨文中作“
”字假借为幾、刏、祈等,这个字在甲骨文中作“
 ”“
”“
 ”等形,意指“刏物牲或人牲,献血以祭”。
[7]
甲骨卜辞中有
”等形,意指“刏物牲或人牲,献血以祭”。
[7]
甲骨卜辞中有
 犬祭神的记载,如:“丁丑贞,甲申用羊九、犬十又一,
犬祭神的记载,如:“丁丑贞,甲申用羊九、犬十又一,
 至于多毓用牛一。”
[8]
意思是:丁丑这天贞问,甲申这天是否用九只羊、十一条狗,采其牲血以祭多毓,还要用一头牛为祭品。这个“
至于多毓用牛一。”
[8]
意思是:丁丑这天贞问,甲申这天是否用九只羊、十一条狗,采其牲血以祭多毓,还要用一头牛为祭品。这个“
 犬祭神”的记载,与《南山经》所谓“祠皆一白狗祈(
犬祭神”的记载,与《南山经》所谓“祠皆一白狗祈(
 )”若合符契,颇可以相互发明。
)”若合符契,颇可以相互发明。
另外,《大荒西经》载:“有人反臂,名曰天虞。”郭注说“亦尸虞”,郝懿行说“据郭注当有成文,疑在经内,今逸”。 [9] 依《山海经》称“尸”之例,“尸虞”若当为“虞尸”,即天虞之尸。《南山经》所言“龙身而人面”,《大荒东经》所言“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应当就是祭典上巫师所扮的“天虞之尸”的形象。
总之,《南山经》的“天虞”当即《海外东经》的“天吴”。理由是,其一,虞、吴二字古通;其二,“天虞”被作为水神而被祭祀,要取“白狗”之血(祈,
 )以祭。“天吴”作为水神,与天虞是一致的。
)以祭。“天吴”作为水神,与天虞是一致的。
二、“天台”
《大荒南经》载“天台高山”,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作“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王念孙据《太平御览·地部》十五所引无“高山”二字,说“高山”二字衍。袁珂先生从之。 [10] 愚以为,此说虽然有《御览》引文为证,不为无据,但并不能证明原文必错。“入焉”者,表示进入此处。《大荒南经》谓:“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郝懿行说:“盖海所泻处必有归虚,尾闾为之孔穴,地脉潜通,故曰入也。” [11] 袁珂引专家说以“海侵”现象的变化为释, [12] 但“海侵”变化当第四纪冰期结束时,恐与《山海经》传说时代距离过远,郝懿行以“地脉潜通”而海水进入为释,比较可信。袁珂曾斥之谓“海水入山,盖古人臆想” [13] 。愚以为《大荒南经》所载或当读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意指“天台”之上亦有高山海水。《大荒北经》“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顺山者,顺水出焉”,可见,“顺水”当在两山之上。在古人想象中,广袤无际的天台上有高山,或者说高山耸入云天,犹在天台之上,都是可能的。屈原讲他自己遨游于天,“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不周以左转”,在天上路过了昆仑和不周山,《楚辞·惜誓》“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14] 可见战国秦汉时出现了天上有众山的概念。而这样的观念,在商和西周时期人们思想素朴、尚不十分浪漫的时期应当是不会出现的。综上所述,《大荒南经》所载之语,当读作“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庶几近乎原意。
[1] 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第24页。
[2]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727页。
[3] 《史记》卷十二,第466页。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5] 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65年,第307页。
[6] 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第23页。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
 》,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8] 《小屯南地甲骨》第1089片。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页。
[9] 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第365页。
[10]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37页。
[11] 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第351页。
[12]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28—429页。
[13]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72页。按,袁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此书增订本时,盖认为此说过苛而删去此语。
[14] 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43、45、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