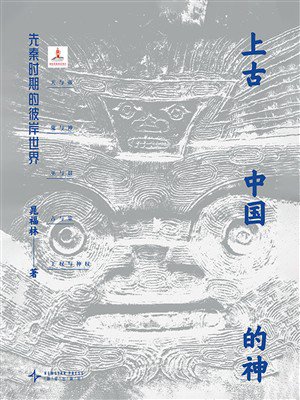《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帝”观念
《山海经》关于“帝”的记载,是我们认识上古先民“帝”观念的宝贵资料。此书的《山经》部分多记帝在天下居住之处以及帝都的情况,而《海经》《荒经》则多记帝的世系与功勋。这与《山海经》各部分写成的时代早晚有直接关系。《山海经》所载“冢祭”与“禘祭”反映了上古先民祭祀情况及天神观念,“帝”之观念应当衍生于此。在《山海经》里“黄帝”只是诸帝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被定于一尊。
在上古先民的思想观念中,“帝”观念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帝”与“天”原本是合一的,直到周代才完全分开。研究“帝”观念的直接文字资料,现在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代以前者则主要靠《山海经》一书。《山海经》虽然编定于汉代,但却是汇集上古传说的宝库。此书虽然如顾颉刚先生所言,“是一部幸免于西汉儒者改窜的古书” [1] ,但毕竟其所述的内容与写成的时代悬隔较远,所以研究上古史事与观念的专家多取谨慎态度,不大利用其材料来说明重大问题。通过分析考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山海经》所记内容的宝贵,关于“天”“帝”等的记载多有他书未载的重要内容。
一、《山海经》中“帝”的基本情况
关于《山海经》里的“帝”的具体情况,为观览方便计,特列下表:
表二 《山海经》所载“帝”的情况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①此表“出处”所标某“经”后的数字,是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一书的页数。
②经文“席”字,郭注:“席者,神之所冯者也。”郝懿行说:“席当为帝字,形之讹也。上下经文并以帝冢为对。此讹作席,郭氏意为之说,盖失之。”见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卷五,第214页。按,黄帝称有熊氏,所葬之山称“熊山”盖与之有关。黄帝死后以山为冢而葬,如熊山、騩山、禾山、尧山。《中山经》说文山、勾檷用高规格祭品祭帝。
二、“帝”之居与“帝”之都
分析上表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认识,那就是《山海经》里的“帝”常居住和活动于高山之上;这些高山,最著名的是昆仑山,其他有崇吾之山、峚山、槐江之山、轩辕之丘、天山、青要之山、鼓钟之山、讲山、熊山、騩山、高前之山、毕山、禾山等多处。在上古先民的心目中,“骏极于天”(《诗·崧高》句)的高山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帝应当居住生活于此。仰望耸入云端的高山之巅,感觉山巅处就如同天上。居住于高山之巅的“帝”,就像居住在天上。 [2] 《西山经》又把帝称为“天帝”(住在天上的帝),其理由应当就在于此。
帝居之高山多有美好的生活环境,如有玉,有圃,有棋盘棋子,有像房屋一样的大树,有粮仓,有可以做酒的好水,有苑囿,有桑树,有琴瑟,有洗浴之处,有仙药,有可以登天的称为“建木”的大树;还有各种服务者,如有为帝服务的五采鸟,有负责巡夜的天神。《山海经》里的“帝”还有妻室女儿。总之,人世间最高领袖所拥有者,“帝”也都拥有。
《山海经》里的“帝”不仅常居于耸入云端的山上,而且其常居之处被称为“都”,我们可以对这些“都”进行一些分析。
帝常居之“下都”:昆仑山。
如《西山经》有“下都”,谓“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西经》也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郭璞注谓“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是可信的。所谓“下都”的“下”意当即与上面的“天”相对应,“下都”或当为在地上(而非天上)之都。但这个“下都”,在昆仑山之上,已经距天不远。可以推测,在先民的想象中,这个“下都”与天上的“都”应当相差不多。“帝”的下都位于昆仑山。这座昆仑山上的帝的“下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引用顾颉刚先生据《山海经》和《淮南子》的相关记载而进行的概述来做全面的观察。顾先生说:
在中国的西面,有一座极高极大的神山,叫作昆仑,这是上帝的地面上的都城,远远望去有耀眼的光焰。走到跟前,有四条至六条大川潆洄盘绕,浩瀚奔腾,向四方流去。山上有好多位上帝和神……这个城叫作增城,城里有倾宫、旋室等最精美的建筑,城墙上开着很多门,城外又浚了很多井。每一个城门都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还有猛鸷的鸟兽虫豸,因此能上去的人是不多的,指得出来的只有羿和群巫。山上万物尽有,尤其多的是玉,处处的树上结着,许多器物都是用玉制的。……这真是一个雄伟的、美丽的、生活上最能满足的所在。 [3]
关于昆仑山的地理方位,说法纷杂,不啻有数十种之多。我国西北地区的不少雄伟高山都符合《山海经》里所说的昆仑山的条件。有专家说是今山东的泰山,也不无道理。可以说《山海经》里的昆仑山的具体方位要具体坐实为某一座山是很困难的,从其出现的历史时段上看,我们毋宁说昆仑山是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心目中的雄伟神山, [4] 它位于那个时期人们的心里。
帝之“密都”:青要之山。
《中山经》有“密都”,谓“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郭注:“天帝曲密之邑。”意思不够准确。密与宓为古今字。《说文》训宓为“安也”。段玉裁说:“密行而宓废矣。《大雅》‘止旅乃密’,《传》曰:‘密,安也。’《正义》曰:‘《释诂》曰:密,康、静也;康,安也。转以相训,是宓得为安。’” [5] 依密字古训,“密都”意当指天帝安康居住之都。
“泰泽”中的“帝都之山”。
《北山经》载:“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广员百里,无草木,有金玉。”按,这座“帝都之山”,顾名释义,当即其上有“帝都”之山。它的位置在“泰泽”之中。“泰泽”之称在上古文献中仅见于此,疑当即“大泽” [6] 。《山海经》里“大泽”多见,较大面积的湖泊似皆可称为“大泽”,《西山经》《北山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等皆有相关的说法。 [7] 此“大泽”之所在,或谓即“古之瀚海”。作为水域的“瀚海”,有贝加尔湖、呼伦湖等说。所谓“大泽”又或谓在今河套地区,或谓在今黑龙江省的嫩江地区 [8] 。这些说法,似皆有些过远,且“瀚海”之说出自汉代,与《山海经》的时代相左。揆诸上古先民活动区域,此“大泽”疑当在今山西境内。《左传·昭公元年》有“宣汾洮,障大泽”之说,意即疏通汾河、洮水,修筑“大泽”之堤坝。据说这是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时候的事情,春秋时人犹能道之。从“大泽”的位置看,这个“帝都之山”,疑即山西境内的太岳山(又称霍太山),此山在长治盆地和太原盆地中间,这两个盆地,上古时代多水,皆可称为“大泽”,并且,《左传》已称其为“大泽”。相传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时候,有“霍太山之神”的传说。 [9] 可见,霍太山乃是自古以来的神山。要之,《北山经》所说的这座在“泰(大)泽”之中的“帝都之山”,很可能就是在春秋时期被视为神山的太岳山(霍太山)。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都”之称不古,甲骨卜辞和金文中未见。在上古文献里,始见于《左传·隐公元年》,谓“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都”之观念,是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这个时段出现的。可以推测,《山海经》把“帝”常居之处称为“都”,以及对于“帝”都的安排,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所进行的工作。这对于《山海经》的成书时代的推定应当是一个参考。
三、《山海经》里的“冢祭”
关于《山海经》所载祭祀情况,专家少有关注。其实,这方面的内容正是我们探讨上古先民的思想与观念的重要而珍贵的材料,特别是其冢祭与禘祭更值得重视。《山海经》的祭天礼多表现于在“冢”的祭祀。上古先民,常常选择山巅处作为祭天的地点。这种祭祀,可以简称为冢祭。冢祭以《西山经》中的一个记载最有系统,谓:
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 [10] 羭,山神也,祠之用烛。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在华山的山巅处的祭祀,要用太牢。主祭的人要斋戒百日,要用一百头牺牲、瘗埋一百件瑜(美玉)、一百樽温酒、一百件缠着丝络的玉圭 [11] 、一百件缠着丝络的玉璧为祭品,其余的十七座山的祭祀所用长有兽毛的牲牷都用一只羊为祭品。向作为山神的“羭”祈祷是用火烛。这段话先说“华山”,再说其他的“十七山”,最后提到称为“羭”的山神,层次很清楚。 [12]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关注“冢”字之意。冢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坟墓”和“大”“顶”三种意蕴。郭璞云:“冢者,神鬼之所舍也。”不直接取坟墓之意,只谓冢是鬼神之居,这样来解释,虽然比清儒吴任臣直接说“冢犹墓意” [13] 为优,但还是不够准确。华山固然可以是鬼神之居,但别的大山何尝不是如此呢?按照《北山经·北次二经》所说,其十七山皆有山神,“其神皆蛇身人面”,皆享用祭祀,可见是山山有神。依郭璞之说,应当是山山皆冢,而不必单指“华山”。要之,经文所言“华山,冢也”,这里的“冢”字之意当指华山之巅。《尔雅·释山》云“山顶,冢”,《尔雅·释诂》“冢,大也”, [14] 是为其证。 [15] 我们理解“华山,冢也,其祠……”,可以说是在山下遥望山巅而祭,但如此说,不如说在山顶祭更合适。因为既然《释山》明谓“山顶,冢”,那么,要说单祭一处山顶,就不若说到山顶祭祀为妥。并且后世帝王的封禅礼也要到山顶祭祀,也可反证说某山之冢的“祠”,是到“冢”祭祀。
比较典型的关于“冢”的记载还有《中山经》的一处:
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太牢之具、糵酿;干舞,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 [16]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在升山山巅处的祈祷之礼,要备好太牢,太牢的牺牲都要用丝络悬挂吉祥之玉。除了备好太牢以外,还有用糵酿好的酒,还有拿着干楯的舞蹈,放置好鼓;牺牲上用丝络悬挂一件玉璧。要陈水为祭品,因为水中有天的倒影,符合天象。要用肥的牺牲祈祷,用一只黑犬祭上天,用一只雌鸡祭下地,祭典上刺杀一只母羊取血以祭。这些牺牲上也悬挂吉玉,要以缯彩为饰,还要劝神享用。
《山海经》祭于“冢”的记载还有《中山经》如下的几处:
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
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
骄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瘗,婴毛一璧。
文山、勾檷、风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用(毛?)一吉玉。
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毛一璧瘗。
堵山、玉山,冢也,皆倒[毛]祠,羞毛少牢,婴毛吉玉。
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婴毛一吉玉。 [17]
这些经文里的话需要进行一些解释。所言某山“冢也”,意指某山之巅。在山巅进行“祠(祈祷)”的祭品,皆有“太牢”或“少牢”。祭祀时若牛、羊、豕三牲齐备,则称为“太牢具”,若只有羊、豕齐备则称为“少牢具”。“县(悬)以吉玉”的意思与“婴毛一璧”相类似,都是指在牺牲上用丝络系上玉饰。
分析在诸山的“冢”的祭祀与其他的山上的祭祀,两者的区别在于,冢祭的祭品规格最高、最为齐备,一般都是“太牢具”或“少牢具”,而其他的山的祭祀都是比不上的。例如上述“历儿”之冢的祭祀用太牢,并且“县以吉玉”,而“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所谓“桑封”即桑木作的木牌,比之于冢祭所用的“吉玉”,显然是等而下之的。在“历儿”山的冢祭要具备“太牢”,而其余诸山的祭祀只用一羊,差别也很明显。
山顶处距离“天”比较近,“骏极于天”的高山之上就如同天上。我国北方地区分布广泛的红山文化的大型墓葬皆位于山顶,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红山文化的七座大墓皆位于山顶,墓周围有石砌的围圈。 [18]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大墓,是在山顶处筑成边长20米的大型方坛,在其东侧是由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的圆形祭坛,其外圈直径22米,内圈直径11米,堆砌积石成三层叠起的巨型祭坛。专家指出这是“圆形和方形坛址的群体组合” [19] 。在这样的祭坛上的祭祀,既是祭天也是祭祖,汉儒所说“祭天则以祖配之” [20] 的祭礼,在这里似乎看到了它的远古面貌。南方地势低平地区的先民,为了缩短与“天”的距离,不惜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堆造出“山”来。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发现有被称为“山”的“高台土冢”。这些“山”全部是人工搬运堆土筑成,例如太湖流域的“反山”高7.3米,“草鞋山”高10.5米,“张陵山”高8.4米,“福泉山”高6米,“寺墩”高20米,其“山”上皆有随葬显示权力的玉钺、琮、璧等器物的良渚文化大墓, [21] 应当是部落首领的墓葬。在这些高台土冢上多发现燎祭遗迹。例如福泉山顶所发现的祭坛,自下而上共有三级台面,“整座祭坛包括土块和地面,都被大火烧红”,“另有两长条红烧土块堆积,……土块也内外烧红”,高台附近另有五个积灰坑,坑中堆积着山上大火燎祭后清扫的草木灰。 [22] 分析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位于山顶的大墓和祭坛,可以说《山海经》所述在“冢”的祭祀情况与之是接近的。
《山海经》所称某山“冢也”,意指在某组山中此山为最高者,是为顶端、山巅,而本组的其他诸山则没有它高。所以选择在这座山的山巅处祭祀,应当是在先民的心目中此处是距离“天”最近之所在。在此祭天,天神最容易享用各种祭品。关于在“冢”的祭祀,《山海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所祭的神灵,但可以推测,它就是祭天之礼。在后世的祭礼中,祭天为最隆重者,《山海经》在冢的祭祀符合这一规律。我们来看《山海经》里在“冢”祭祀的诸山的情况,如苦山之上有“帝台之石”,应当就是禘祭的石台。少室山有称为“帝休”之树木,可见天帝曾来此休息。再如堵山,其上的神称为“神天愚”,主管风雨之事。又如玉山,是“司天之厉”的西王母所居之处,亦与“天”有密切关系。再如尧山,径以尧帝命名。 [23] 总之,在《山海经》里凡是称为“冢也”的诸山皆与“天”若“帝”有关。在山巅处祭祀,所祭对象非天莫属,主管风雨之事的称为“神天愚”者,就是天神,在山巅处祭他,就是祭天神。这种在山巅祭天的涵意,用周代人的说法就是“因天事天” [24] 。
这种在山巅处祭天神之举,流传到周秦两汉时期逐渐形成君主的封禅礼,战国时人对于上古时代部落首领祭天还有一些记忆。《管子·封禅》篇列举上古封泰山的说法是有七十二家之多,记得起名字的有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十二家。 [25] 这里所说的以封禅礼祭泰山,指今山东泰山,其实从《山海经》里可以看到上古祭山非必在泰山,只不过是春秋战国时人将所有部落首领的“冢祭”,都搬到了“泰山”而已。
四、《山海经》里的“禘”祭
可以推测,在山巅处的祭祀,是燔柴焚烧祭品而享天神的“禘”祭。《山海经》里和在“冢”的祭天礼差可比肩的是“帝(禘)”祭。这有如下三条记载:
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具);合巫祝二人舞,婴一璧。
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用一璧,牛无常。
熊山,席(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一璧,干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26]
从祭品规格上看,称“帝也”诸山的情况与称“冢也”诸山者完全一致,并且騩山称“帝也”,又称“冢也”。可见“冢也”“帝也”的含义是相同的。可以推测,在高山山巅处的燔柴祭天,可以因其祭礼位置而称为“冢也”,亦因为燔柴的祭祀方式而称“帝(禘)也”。以上三条经文所提到的“帝”必当读为“禘”,因为它不可能以某山作为人称的“帝”。
为什么经文要把祭礼称为“帝(禘)”呢?
这需要从“帝”的造字本义谈起。在甲骨文字中,“帝”的本义,过去多以为象花蒂之形,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主张它与古代的尞祭有关,帝、禘、尞、祡等字的古义皆有密切关系,其本义即束柴尞祭于天。 [27] 对于此点,诸家多有所论,以陈梦家所说最为详审。他说:“卜辞尞字象然木之形,或省去火焰之形,或于火焰外更增一火的形符。《说文》:‘寮,祡祭天也’,‘祡,烧祡焚燎以祭天神’,《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风俗通·祀典》篇:‘槱者,积薪燎柴也’。凡此尞(燎)、燔、祡、槱等皆所以祭天神,所以《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祡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些都是焚烧积薪以祭天神。” [28]
卜辞里有的帝字应当读若“禘”,用作祭名。多有所见的“方帝”,意即盛大的禘祭。请看相关记载:
贞,方帝(禘)一羌、二犬、卯一牛。
……午卜,方帝(禘)三豕又犬,卯于土(社)牢,祈雨。
己亥卜贞,方帝(禘)一豕、一犬、二羊,二月。 [29]
这几例中的“方帝”的“方”本有“大”之意,在古文献里每与旁相通,可以读若旁,意为大也、遍也。清儒马瑞辰释《诗·大明》“以受方国”,谓:“《广雅·释诂》:‘方,大也。’《晋语》‘今晋国之方’,韦昭注:‘方,大也。’《尔雅》:‘方丘,胡丘。’方与胡皆大也。又方与旁古声义并同,旁亦大也。方有大义,方国犹言大国也。《笺》训为四方,失之。”
[30]
王引之谓《尚书》所云“汤汤洪水方割”“小民方兴”“方行天下”“方告无辜于上”等的“方”,“皆读为旁,旁之言溥也,遍也。《说文》曰:‘旁,溥也。’旁与方古字通,《商颂·玄鸟》篇:‘方命厥后。’郑笺曰:‘谓遍告诸侯。’是方为遍也。‘汤汤洪水方割’,言洪水遍害下民也。‘小民方兴,相为敌雠’,言小民遍起相为敌雠也。……‘方告无辜于上’,言遍告无辜于天也”
[31]
。马瑞辰和王引之的这些说法甚精当,我们可以据此而推测卜辞“方帝(禘)”,意即大禘,举行盛大的禘祭。这三例卜辞所言的羌、羊、犬、豕皆为禘祭时所用之牺牲,把这些牺牲放在火堆上烧,肉的香味随烟而上升于天,使天神闻到而喜欢。此犹如《诗·生民》篇所言“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上帝闻到升腾而上的浓烈的确实好闻的香味,就如同吃了祭品一样高兴)。甲骨卜辞里的“帝(禘)”就是焚柴以祭天神之祭祀,焚烧牺牲而让天神歆闻香味的最佳地点当然是在高山之巅。甲骨文“岳”字亦是一个参证。这个字多作“
 ”形,其下从山(或曰从火),其上从羊。
[32]
意指在山上焚羊(羊,代表所有种类的牺牲)以祭天神。这样的山高耸特立,所以岳即指高山,或有专家释岳专指太岳山若嵩山者。《诗·商颂·长发》序云:“大禘也。”毛传:“大禘,郊祭天也。”
[33]
此处所云的商人祭天的“大禘”与甲骨卜辞的“方帝”之意应当是一致的。
”形,其下从山(或曰从火),其上从羊。
[32]
意指在山上焚羊(羊,代表所有种类的牺牲)以祭天神。这样的山高耸特立,所以岳即指高山,或有专家释岳专指太岳山若嵩山者。《诗·商颂·长发》序云:“大禘也。”毛传:“大禘,郊祭天也。”
[33]
此处所云的商人祭天的“大禘”与甲骨卜辞的“方帝”之意应当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相关的认识概括如下。《山海经》在高山山巅处的祭祀对象原本是“天”,后来部落首领被视为神而居于天上,因此,祭天亦是祭作为天神的部落首领,这些天神因为享用燔柴以祭的“帝(禘)”祭,所以被称为“帝”。“帝”之称本身就意味着是天神, [34] 但《西山经》还是将“天”之称挂之于“帝”的前面而称为“天帝”,强调其天神之特色。这是早期“帝”的性质的一个表现。作为天神的“帝”本身就意味着高尚和神圣。人世间的部落首领去世后上升于天成为伟大的“帝”,再进一步,“帝”之称就“兼摄到人王上来了” [35] ,而这一步却是经历了漫长时段才完成的。在商代的甲骨卜辞里,“帝”与“天”本无严格区别,实际上是以“帝”作为“天”的代称。我们从《山海经》里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端绪。
这里可以附带说明的一点是,“帝”的称谓何时由死谥变为生称,是个待研究的问题。从《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尚书·尧典》所载“五帝”的情况看,在传说时代似乎就将部落首领生称为“帝”,《山海经》亦支持此点。但这些文献所载俱为春秋战国时人的说法,能否代表远古先民的实际说法,当有疑问,可存以待考。部落首领的称谓,起初盖皆以其名为称,如尧、舜然,后来所上尊号则难以推测。愚以为可以考虑的另一种解释是称为“酋”。酋本有终极、会聚之意,并且通假为遒、猷。 [36] 周初时习称的“猷”,常用作发语词,如《尚书·大诰》和《多方》:“王若曰:猷。”以发语词为释,固然是通顺,但愚以为它还可以假为“酋”,意谓诸位首领。《诗》所言“先公酋”(《卷阿》)、“大猷”(《巧言》),《礼记·月令》所言“大酋”,皆有首领之意。到了秦汉时期,“酋长”则为习用之词。盖远古先民呼唤首领为酋,酋长辞世被视为天神而享用禘祭,则逐渐冠以“帝”称。若此推测可信的话,那么就可以说,《山海经》所称的“帝”,除了表示禘祭者外,作为人称使用者,应当是较晚的事情,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帝”称的。《山海经》的此类“帝”称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人以当时语而述古的结果。
五、从“天帝”到“黄帝”:“帝”的观念之变迁
将《山海经》里单称的“帝”作为“黄帝”的省称,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袁珂先生曾经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指出:《山海经》中凡言帝,均指天帝,而天帝非一,除《中次七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尧而外,其余疑均指黄帝。 [37] 现在看来,这个论断尚有再讨论的余地。
《中次七经》所载“帝女”,袁先生以巫山神女当之,主要依据是帝女所居之山为姑媱之山,而《文选·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云“赤帝女曰瑶姬”,盖因为一载“姑媱之山”,一云“瑶姬”,涉媱、瑶二字, [38] 因此牵涉为一,说这个帝就是赤帝。这恐怕不足以成为证据。后世传说对于前事多有附会之处,以《襄阳耆旧传》来判断《中次七经》所载帝女即赤帝之女,是比较牵强的。断定《中次十二经》所言“帝之二女”即尧之二女,又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上古传说,多有踵事增华的情况,越说越具体,越说越像实有其事。袁先生所举的这两个事例,都是后世的附会,不足以断定《山经》这两个记载的“帝”即赤帝。
我们应当将《山海经》称“帝”的情况做一简单分析。
首先,单称“帝”者,见于《西山经》者7(其中一处称“天帝”)、《北山经》者1、《中山经》者15,共计23处;见于《海经》者5,见于《荒经》者2。从数量对比上可以看出《山经》占了大多数。并且《海内西经》所谓“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一处记载内容与《西山经》所记完全相同,且无《西山经》所记详细,疑为《山经》之语而误入者。
其次,述“帝”的居住及都邑情况者,皆见于《山经》,而《海经》《荒经》则只偶述帝臣之事。
再次,述“黄帝”“帝俊”“赤帝”“帝尧”等复合称谓的帝,见于《山经》5处 [39] ,见于《海经》《荒经》51处,数量悬殊。《山经》所记不仅数量少,而且极简略。
最后,讲复合称谓的“帝”的世系者只见于《海经》《荒经》,而不见于《山经》。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区别,可以看出《山经》与《海经》《荒经》关于帝的记载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约略言之,可以说时代较早的《山经》多讲单称的帝,而时代较晚的《海经》《荒经》则多言复合称谓的帝。
关于《山经》的时代的早晚问题,比较复杂,本文暂不讨论,只简要写出愚之浅见。我赞成《山经》是《山海经》里写成时代及所述内容为最早的说法。理由如下。其一,《山经》所写的古地理范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即传说时代部落联盟的核心区域。谭其骧先生说:《山经》所述“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最正确,经文里距与实距相差一般不到二倍;离开这个地区越远,就越不正确。……肯定顾颉刚的《山经》作者为周秦河汉间人说” [40] 。这个地区是仰韶文化直到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分布最多的区域,只有在这个部落联盟的中心区,才有可能将各种传说集为一体,有较为翔实并能长久流传的共同记忆。其二,那是一个部落联盟的时代,邦国等社会组织形式尚未出现。《山经》不提邦国,足证其时代比讲邦国的《海经》《荒经》为早。其三,《山经》多写异禽怪兽、山林土石,少有鬼神,更无国家、五帝之说,其内容应当是早期先民所见所闻,而非商周时代之事。概括说来,《山经》见物(包括动物)不见人,物多而人少;而《海经》《荒经》等则多“人”及“神人”的魅影,是人多而物少。就先民认识规律而言,先关注特异的自然物,然后才将认识的眼光扩展到人与社会。总之,从《山经》所述内容看,它的时代应当是《山海经》全书中最早者。
在《山经》里,提到黄帝的仅《西山经》一处,而提到单称“帝”者则在所多有。这个情况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关于《山经》所述时代较早这个判断没有大误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而推论说,在较早的时代里,人们只称“帝”或“天帝”,只是到了后代(亦即周代)才开始出现黄帝及其他诸帝的称谓。分析此一问题,用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精见,非常合适。顾先生说“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41] ,关于黄帝的概念就是如此。在《山海经》里,《山经》部分基本上不提黄帝,而《海经》《荒经》里虽提及黄帝,但却没有天下共主的面貌,只是诸帝之一。平实而论,他的地位还赶不上“帝俊”。
关于“黄帝”“帝俊”等的关系,值得我们考究。请先看《山海经》里的“帝俊”情况表: [42]

可以肯定,在《山海经》里,帝俊的影响远甚于黄帝。关于帝俊其人,郭璞以为就是帝舜, [43] 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见,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 [44]
王国维同意皇甫谧此说,并举甲骨卜辞为证,认为“郭璞以帝俊为帝舜,不如皇甫以夋为帝喾名之当矣” [45] 。郭沫若肯定王国维说“倍有见地”,又指出《山海经》“盖以舜、俊、喾为三人也,……凡神话传说之性质,一人每化为数人,一事每化为数事,此乃常见之事实,殊不足怪”,“《山海经》之帝俊实即天帝,日月均为其子息。……实如希腊神话中之至上神‘瑳宇司’,并非人王也”。 [46] 诸家之说,层层深入,皆有依据,其中以郭沫若说帝俊即“天帝”,最为宏观而近是。皇甫、王、郭三家,以为帝俊即帝喾,有甲骨卜辞为证,可信度很高。亦可以推测,这是商代时殷人的观念,殷人试图把帝俊(喾)作为统领天下的天帝,合乎情理。但到了周代,则没有完全认同这一观念。虽然亦以姜原为“帝喾元妃”,顺从了殷人的观念,还用“禘喾”的祭法与殷人保持一致 [47] ,但又说周祖后稷乃姜原直接与天神所生,编造出她践巨人迹,“身动如孕” [48] 的神话, [49] 与天帝攀上直接关系。再者,周人每以“夏”自称,似乎是夏之后人。 [50] 这样做的目的,应当是在表示与殷商有别。周人对于殷商传统的态度游移不定,表明周人对于殷商传统既有保持一致的倾向,又有别出蹊径,直接攀附于天帝并且和夏的传统挂钩的意向,但总的趋势是强调周人自己固有的传统,彰显周人自己的传统。周人编排的古史系统,极大地提高了黄帝的地位,应当与夏人“禘黄帝” [51] 有关。把他与帝俊的位置颠倒过来,说帝俊(喾)是黄帝的后裔。春秋战国时期写成的《尚书·尧典》及《大戴礼记·帝系》等书,总结了周人的古史编排,截断众流,厘定出一个传承有绪的古史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概括为下表:

这是为司马迁承认的古史系统,是我国古代占有统治地位的认识。把这个表和《山海经》里“帝俊”的情况表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上古时代古史系统化时的轨迹,那就是极大地提高了黄帝的地位,降低了帝俊(喾)的地位。这个转变的深层因素在于周人自己的古史观念从“服殷”到“附夏”终而“崇周”的变化。通过这一转变,周人自己的古史系统就超越了殷人,而更为源远流长。
关于“黄帝”的文献记载,最初出现于西周初年成书的《逸周书·尝麦》篇。这就可以考虑“黄帝”之说出现的时代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黄帝”的观念甫一出现(即周初)就被载入《尝麦》篇,二是长期流传的说法被整合进入《尝麦》篇。愚以为后一种推测更为可信些。这是因为,《尝麦》篇不仅提到了黄帝,而且详述了他与赤帝联合大战蚩尤的传说,这一个系统的古老传说,非经历一个漫长世代不足以定型,很可能它是五帝时代就有的说法,历经夏商两代而至周初才被写入文献。 [52]
总之,上古时代“帝”观念的变化,约略说来,最初是只将天神尊奉为单称的“帝”,意即作为天神的帝,待到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亦即五帝时代),部落联盟首领去世后成为天神,被尊为“帝”,开始有了黄帝、炎帝、帝喾等复名的帝。殷商甲骨卜辞表明,那个时代延续了单称帝的传统,只是将帝视为天神,但那个时代的传说里很可能有了复名的帝,所以到了周代就顺理成章再将这些帝名载入文献。《山海经》的时代黄帝只是《大荒南经》所说的“群帝”之一,还远未被定于一尊。经过漫长时间的整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传承有绪的五帝系统,黄帝的名称才赫然显然而位于诸帝之上,从而彪炳千古。
[1] 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2] 此种观念流传甚久,汉朝时人尚有如此看法。《史记·封禅书》载:“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史记》卷二十八,第1401页)此举意味着所祭之帝在天上,“昆仑道”即登天之路,公玉带把它说成是黄帝时所为,犹存古意。
[3] 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4] “昆仑”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叠韵连语之一,这类例子还有旁薄、混沌、蹈腾、营惑、狼戾等,参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第807—808页;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国书店,1985年,第31—36页。是可推测其出现的时代。
[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七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39页。
[6] 泰、太、大三个字为同源字,音近意通(见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90页)。在上古文献里这三个字相通假的例子不胜枚举,《尚书》的《大誓》,《尚书大传》和《史记》并作《泰誓》,是为显证。
[7] 《山海经》里关于“大泽”的记载如下:《西山经》:“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北山经》:“维龙之山……敞铁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泽。”《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大荒西经》:“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大荒北经》:“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
[8] 今嫩江下游地区在古代曾是一个方千余里的大湖,《魏书》卷一《序纪》称拓跋鲜卑之祖曾经“南迁大泽,方千余里”,这个大泽当即今嫩江下游地区的古代大湖。说见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
[9] 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919—920页。
[10] 《山海经·西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第38页。按,原文在“祠之”之后有“烛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纯之”之语,毕沅说是“周秦人释语,旧本乱入经文”(毕沅注《山海经》卷二,光绪三年浙江书局校刻本,第11页),其说甚是,今从之。
[11] 关于经文“婴”字的解释多歧,或读若璎,指玉器;不若读为缠绕之意的“缨”为优,新蔡楚简“婴之以兆玉”,是为其证。说见罗新慧《说新蔡楚简“婴之以兆玉”及相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3期。
[12] 这段话末尾的“羭,山神也,祠之用烛”八字,原在“太牢”之后。愚以为,从文意上看应当处于此段话末尾,因为后面的享用“百牺”“百瑜”“百樽”“百璧”这样高规格祭品者,不可能是作为“山神”的“羭”,而应当是华山之巅的天神。关于“羭”,郭璞认为《北山经》的“闾”就是羭,“似驴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驴”(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97页)。段玉裁以为羭就是母山羊(说见《说文解字注》四篇上,第146页)。
[13]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二,四库全书本。
[1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第2618页上栏、第2568页中栏。
[15] 清儒毕沅已经指出此点,见毕沅注《山海经》卷二,光绪三年浙江书局校刻本。
[16]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63页。此条经文在“吉玉”之下,原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牺”十字,疑错简而误置于此。其下的经文,言“太牢”之事,必当连于讲“太牢”“婴用吉玉”之后。“䰠”字义为神。《中山经》青要之山,“是多仆累、蒲卢,䰠武罗司之”,郭璞注“武罗,神名;䰠即神字”,或谓这个字应当是“神鬼”之意,指鬼之神者。愚以为,“䰠”当是神字异构。
[17] 以上七条引文依次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46、181、188、195、198、213、219页。
[1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19] 田广林:《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20] 《礼记·丧服小记》郑玄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5页中栏。
[21] 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
[22] 黄宣佩主编《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64—66页。
[23] 在《山海经》里将尧称为“帝”者,见于《海外南经》《海内北经》《大荒南经》等。
[24] 《礼记·礼器》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假。”郑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440页中栏)依此意,则“天”在高处,所以要在山顶祭天神,就是“因高者以事”。汉晋时人或认为天未必那么高,《列子·天瑞》言“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张湛注说:“自地而上则皆天矣。”(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31页)这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所做的解说。张湛的这一观念,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先秦时期所理解的“天”是在高处,而不在身旁。《易·大畜·象传》谓“天在山中”,是据其上艮(表山)下乾(表天)的卦象所做的解释,是古人对于“骏极于天”(《大雅·崧高》句)的高山的印象。耸入云端,犹如在天。《礼器》所谓“因天事天”,与在山顶处祭天是一致的。
[25]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十六,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第952—953页。
[26] 以上三条经文分别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98、213、195页。经文的“席”字,袁珂指出,王念孙校改为“帝”,郝懿行亦谓“席当为帝字,形之讹也。上下经文并以帝冢为对,此讹作席”(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第214页)。诸家说甚是,今据改。
[27] 关于“帝”字本义指束柴尞祭于天的说法,见王辉《殷人火祭说》(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严一萍《美国纳尔森艺术馆藏甲骨卜辞考释》(《中国文字》第六卷)两文。两说均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第1082—1083页。
[28]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52页。按,关于禘祭之义,汉儒有争议。郑玄以为《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意谓“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5页中栏),将禘义定为郊祀天神之祭,后来王肃等则以为祭祖的庙祭。清儒金鹗曾经详加辨析,肯定郑玄之说,见其所撰《求古录礼说·禘祭考》(《清经解续编》第三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286—292页)。
[29]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第418、12855、14301片。以下称引甲骨卜辞,皆简称书名和片数。
[30]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803页。
[31] 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三册,台北世界书局,1975年,第69页。
[32]
关于甲骨文“岳”字上部所从形体的解释,有专家认为它不是羊。小屯南地甲骨出土之后,其第2906片“岳”字作“
 ”形,姚孝遂和赵诚先生指出:“此
”形,姚孝遂和赵诚先生指出:“此
 字上从‘羊’,与一般的形体有别。过去关于此字是从‘
字上从‘羊’,与一般的形体有别。过去关于此字是从‘
 ’还是从‘
’还是从‘
 、
、
 (即
(即
 )’均有争论,据此则字或从羊,或从‘
)’均有争论,据此则字或从羊,或从‘
 ’,似无区分。”(《小屯南地甲骨考释》,第11页)这个发现解决了甲骨文“岳”字是否从“羊”问题的争论,是对于“岳”字考释的一个突破。
’,似无区分。”(《小屯南地甲骨考释》,第11页)这个发现解决了甲骨文“岳”字是否从“羊”问题的争论,是对于“岳”字考释的一个突破。
[3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十,第625页下栏。
[34] 将“帝”作为天神,在我国上古时代的观念里影响甚久,战国秦汉时尚且存在。《礼记·曲礼》云:“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玄注谓:“同之天神。”(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第1260页下栏)是为一例。顾颉刚先生亦曾指出,“‘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在上古文献中,帝、天二字常为互文,“王也而曰‘帝’者,臣子对于所崩之王,尊之至极,配天不足则上同于天,故假帝号以号之”(《史林杂识初编·黄帝》,第177页)。顾先生此说甚精辟。我们可以进而指出早在上古时代的祭天祀礼中,“帝”与“天”就已经有了意义的系连,这两个字的意相涵而音相通,有着悠久的渊源关系。
[35]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1页。按,将帝号“兼摄”到人王头上,应当是很晚的事情,商代并不如此。商代称帝甲、帝丁、帝乙、帝辛等皆当为庙号,说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40页)和常玉芝《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文史哲》2008年第6期)。
[36] 说见郝懿行《尔雅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37]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229页。
[38] 检《文选》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以及《古今图书集成·历象·乾象·云霞部外编》皆作“姚姬”(《文选》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75页),《文选·别赋》又引作“瑶姬”(《文选》卷十六,第754页),盖传闻异辞,作瑶、作姚皆可。然即令作瑶,亦不能证明巫山神女就是《中次七经》之“帝女”。
[39] 《中山经》所载复合性的帝称有一处称“阳帝”者,但系作为山名而非人名,且经文明谓“阳帝之山皆冢也”,所以不将此例计算在内。
[40]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41]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42] 此表取自徐中舒、唐嘉弘《〈山海经〉和“黄帝”》(《〈山海经〉新探》,第98页)一文。
[43] “帝俊”于《山海经》里凡十二见,郭璞注多谓是帝舜,惟《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郭注“俊宜(且)为喾”。经文“宜”字,王念孙校改为“且”。见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第359页。
[44] 皇甫谧:《帝王世纪》第二,《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第11页。
[4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13页。
[46] 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47] 《礼记·祭法》:“殷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十六,第1587页中栏),皆对喾行禘祭,可见其一致的情况。
[48]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1页。
[49] 见《诗·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
[50] 《尚书·康诰》说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左传·成公二年》引《周书》说文王“所以造周”,可见区夏即周。“我区夏”意即“我周”(或有专家以为区夏意为华夏,恐非。因为此时尚无华夏的概念)。《尚书·立政》“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说是上帝使我有夏接管了商所受的天命,抚治天下万民。“有夏”亦是周人自称。徐旭生先生曾指出,我国上古先民“从古代起,就自称诸夏,又自称华夏,又或单称夏或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7页),周人以夏人后裔自称,有向殷人自炫历史悠久之意。
[51] 《礼记·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及《礼记·丧服小记》所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则夏人实认为自己是黄帝后裔。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87页中栏、第1495页中栏。
[52] 甲骨卜辞中没有发现关于“黄帝”的记载,很可能是因为商人以喾为始袓,而不禘祭黄帝的缘故。文字记载所见古史传说,可以说明此文字记载的时代必当有此传说,但不能因此默证在此文字记载以前的时代无此传说。黄帝的传说应当就是这种情况。周初的文献始有关于“黄帝”的记载,不能绝对证明在此之前没有黄帝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