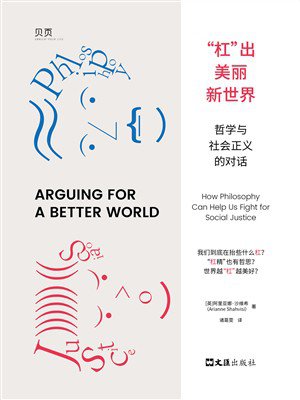言语之重
言论自由至关重要。然而,与其他自由一样,它也并非毫无边界。例如,我固然有权在夜晚独自穿越城镇的每个角落,但实际上作为女性,安全隐患往往使我望而却步。同样,虽然我有权在公共空间自由活动,但如果我选择在一群陌生人吃午餐时站到他们的野餐垫中央,就会破坏他们享受公共空间的乐趣。言论自由亦是如此,它常与我们认为重要的其他权利相冲突,而且不同人群行使这一权利的能力大相径庭。虽然原则上我们都有说话的自由,但有些人因发言而面临的后果过于严重,只得选择缄默;有些人则因缺乏发声的平台,而被迫沉默。自由从来都不是无限的,也鲜少能实现公平的分配。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游乐场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棍棒石块或能伤我筋骨,但是闲言碎语却无法动我分毫。这是一种用以抵御辱骂的护身符。你可以用这句话回敬骂你的人,以此作为自我保护的预防措施。成人鼓励孩子这样做,或许是想让我们坚强起来,能够面对游乐场上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然而,言语确实能够伤人,任何曾遭受残酷或侮辱性评论的人都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脑部扫描显示,辱骂所造成的社会排斥会激活前扣带皮层,当我们遭受身体疼痛时,大脑的这一区域也会被激活。 24 更为严重的是,言语有时甚至会导致或升级为肢体冲突;辱骂往往是身体伤害的导火索。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健全中心主义、跨性别恐惧症和同性恋恐惧症等恶行往往以言语为手段。一旦它们演变为暴力行为,就绝非沉默无声。言语,远不止声音、像素或墨迹那么简单。它们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许多哲学家都指出,言语与行为总是紧密相连。例如,当我说出“黑人的命也重要”时,我实际上在做多件事情:表达我对一场政治运动的声援,批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惹恼保守派。反之亦然:行为同样传达着言语。如果一名足球运动员在赛前单膝下跪,她就是在通过这一行为表达“黑人的命也重要”或类似的立场。
 正如女权主义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所言:“言语会行动。行为会说话。”
25
正如女权主义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所言:“言语会行动。行为会说话。”
25
哲学家把所有以言行事的言语实例称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哲学家奥斯汀于1962年首次正式提出并描述了言语行为,他认为“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26 。当我们发声时,并非仅仅在发出有意义的声音,而是在通过言语实施某些行为。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对世界产生某种影响。以“你不用再来上班了!”为例。如果老板说出这句话,那么你就丢了工作。或者,如果一方在性行为过程中说“我不想继续了”,那么他/她实际上已经撤回了自己的同意,如果此时继续性行为,就会立即成为一种违法行为,甚至在某些法律体系中构成犯罪。正是因为言语,对方继续实施的行为才会被转变成道德错误或违法行为。因此,言语往往只需通过发声便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举个更贴近日常的例子,如果在用餐时,我问姐姐“还有辣椒酱吗?”,我不仅是在了解那罐辣椒酱的状态,还是在要求姐姐把它递给我。因此,我的话语执行了提出请求的动作。相比之下,如果我在洗碗时跟着邦妮·泰勒的歌哼唱,这种发声则不会对世界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即使长夜渐尽,也不会有英雄出现。)

那种认为“言语只是言语!”或倡导“人们应能畅所欲言”的反对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言语不仅可能引发某些行为,而且它们自身就常常构成行为。想要达成“人们应能随心所欲地行事!”的境界更要困难得多。
在审视色情作品时,也可从相似的视角出发。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活动家凯瑟琳·麦金农和安德丽娅·德沃金联手起草了一项反色情法令,旨在为受色情作品伤害的人群提供民事诉讼的途径。法官赞同“对从属地位的描述往往会使从属地位永久化”,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女性在)职场中遭受侮辱和低薪待遇,在家庭中遭受侮辱和伤害,在街头遭遇殴打和强奸” 27 。但该法令最终因被认为侵犯色情作品生产者的言论自由权而被裁定违宪。然而,这一裁决未能抓住问题的关键。麦金农和德沃金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妙的论点。诚然,色情作品是以非人性化的方式描绘女性的言论,从而对其所呈现的女性造成伤害,然而,她们并不只是在说色情作品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描绘女性,并导致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些都是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她们是在说,色情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构成伤害的行为。因此,应将其视为有害行为而非有害言论进行监管。哲学家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指出,对于德沃金和麦金农这类反色情女权主义者来说,色情作品的“全部意义”就是“允许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赋予女性低等公民地位”这样蓄意的言语行为。 28 色情作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遣,更是许多人借以学习性爱和思考他人的人格和偏好的途径。色情作品能够发声,它通过发声采取行动,通过行动,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且保持沉默。
1993年7月至1994年7月期间,卢旺达千山自由广播电台(RTLM)的广播就是言语导致严重伤害的最著名的例证之一。电台面向胡图族听众(当时执政的是胡图族政府),煽动原本就已存在的对图西族的仇恨,教唆胡图族“消灭”所谓蟑螂和毒蛇。在短短一百天内,就有一百万人遭到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图西族人。尽管比利时殖民当局助长并利用了这种敌意,但人们普遍认为,卢旺达千山自由广播电台那些丧失人性的煽动性言辞在随后的种族灭绝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言语终究变为利器。
压迫性言论能够兜售有害的刻板印象,这些歪曲事实的表述限制了边缘化群体的生活,也决定了他们可能面对的未来。例如,女孩们常被(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告知,她们的大脑不适合学习科学和数学。(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在伊朗,绝大部分理工科毕业生都是女性。 29 )最终结果就是,许多女性相信了这种刻板印象,并因此感到气馁,于是这个预言和谎言最终变成现实。这就是所谓“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在一项旨在评估刻板印象对女性数学能力的影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女性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接受了名为“几何”的测试,而另一组则接受了内容完全相同但被命名为“美术测试”的考核。 30 结果表明,第二组的得分更高,这是因为该组受试者在测试过程中无须面对“女性不擅长几何”的性别偏见压力。至今没有任何权威的科学研究能证明,在解决数学问题或其他相关领域的问题时,“女性大脑”的能力会逊于“男性大脑”(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性别分类并无实质性意义)。大脑没有性别之分,它的特性是由我们的行为所塑造的。
刻板印象是一种言语行为。每提及一次,就会强化对我们行为的现有约束,从而使世界更加符合其错误的表征。刻板印象会阻碍女孩在物理领域的发展,限制男孩表达情感的能力。而“政治正确”的目的正是打破这些刻板印象,减少人们面临的一些内在障碍,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把它做好。这就引出了那些希望反对“政治正确”的人所用的一系列反“政治正确”论据中的第一个论点:对精英统治的威胁的担忧。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平权法案、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和“多元化招聘”等政策的出现,“政治正确”更加重视身份而非能力,从而降低了标准。作家莱昂内尔·施赖弗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她提出,现今的出版环境更倾向于出版“一个七岁辍学、开着代步车在城里转悠的加勒比跨性别同性恋者”的作品,即使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 31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人物随意发表此类言论的背景下,竟然还有人声称“政治正确”已经“变调”了。)
施赖弗的说法既毫无根据,又令人憎恶。2019年,白人撰写的书籍占据了美国出版市场的76%,尽管他们只占总人口的57.8%。在已出版过书籍的作者中,顺性别者占97%,异性恋者占81%,非残障人士占89%。 32 由此可见,一个“加勒比跨性别同性恋者”要想出版作品,机会实在渺茫。而且,即使他们真的能够脱颖而出,其稿酬也极有可能远低于白人作者;在出版行业中,书籍作者的薪酬存在着显著的种族差异。 33
她暗示“政治正确”会拉低艺术作品的质量,这种说法实难站住脚。首先,即便为更多元的声音提供表达平台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标准(施莱佛主观臆断如此,这很能说明问题),但这真的是问题吗?我们难道应该只看重表现,而忽视其他因素吗?即使二者相互排斥,一个非正统的观点也至少和一位伟大白人的犀利言辞具有同等价值。其次,施赖弗假定这是一个精英统治的体系,因此增加多样性的举措会威胁到那些原本只靠天赋就能赢得的机会。然而,文学上的成功与其他领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特权。(我查阅了维基百科上有关我欣赏的作家的所有词条,并且沮丧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接受过私立教育。)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一旦采取有效措施吸纳代表性不足群体,这些群体的表现往往会变得更加优秀,这表明他们之前所遭受的(经济、社会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边缘化或排斥,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虽然特权有助于为人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创造条件,但也可能使人们产生自满情绪,导致他们表现不佳。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瑞典在引入性别配额之后,往往能将不称职的男性淘汰出政坛,从而提升了政府整体的工作能力。 34 同样,2015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种族和族裔上最多元化的公司在财务回报方面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可能性要高出35%,而且,研发团队的性别越多元化,其创新能力就越强;文化越多元,产品开发就越富想象力。 35 2006年的一项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涉及黑人被告的模拟庭审中,相比种族多元化的陪审团,全白人陪审团在正确评估事实方面表现较差。 36 有色人种陪审员不仅更加注重细节,更愿意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他们的参与还能提高其他白人陪审员的表现。尽管对“能力”或“表现”加以衡量的想法值得商榷,但这类研究无疑驳斥了那种认为提高多样性必然需要付出代价的轻率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