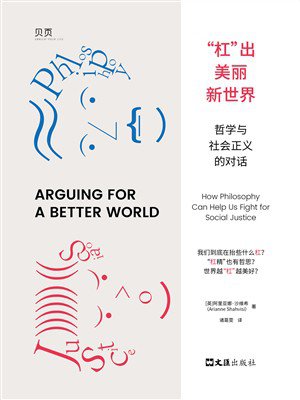不那么陡峭的斜坡与香肠咆哮
那些抨击“政治正确”的人,常常站出来为冒犯行为辩护。他们认为,对言论施加限制是危险之举。虽然他们敦促我们对待言论限制要谨慎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根据具体语境来判断是否应对言论加以限制。无法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批评政治领导人或对他们有所冒犯,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嘲笑掌权者,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他们的权威并非不可撼动。同样,因使用伤害性词汇描述残疾人而受到谴责,虽然看似限制了言论自由,但难以断言人们需要这种无拘无束的言论自由,而且任何尝试这样做的行为,最终都可能以其他方式妨碍残疾人的日常生活。
发表负责任的言论需要关注权力的运作。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以肤色蔑称白人(如“奶瓶”),与用类似形容蔑称黑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尽管两者都显得不友善,但前者只是一种冒犯,而后者则是对现有压迫的推波助澜。反“政治正确”者往往无视这种微妙的差别,他们渴望有一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畅所欲言,又无须承担任何批评或付出任何代价的硬性规定。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而是让压迫性言论能免于评判或惩罚的“自由”。正如雷尼·埃多–洛奇在《我为何不再与白人谈论种族问题》一书中所言,“政治正确”是“在无须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下,尽可能公开地表现偏见的最后防线” 37 。
正因如此,“政治正确”的滑坡谬误
 是无法成立的。我关于“请不要使用‘黑打头的词’:因为它很伤人,而且会加深反黑人种族主义”的言论,与“很快就没人敢说话”的观点之间并无明显联系。尽管如此,此类论点仍然被屡屡提及。针对“Me Too”运动的兴起,为右翼杂志《旁观者》撰稿的道格拉斯·穆雷曾抱怨说:“规则正在被重新制定,然而人们却不知道这个新的性别乌托邦的边界在哪里,更不清楚最终是否允许存在任何性别。”
38
试想一下,居然有人在听到女性为“性骚扰”大声疾呼后,得出了“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可能存在性别”这样的结论(而且,作为一个白人男性,他还能如此自信地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批评压迫性言论与右翼评论家所描绘的那种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之间并无明显的逻辑连接:这个“斜坡”其实一点也不陡峭。
是无法成立的。我关于“请不要使用‘黑打头的词’:因为它很伤人,而且会加深反黑人种族主义”的言论,与“很快就没人敢说话”的观点之间并无明显联系。尽管如此,此类论点仍然被屡屡提及。针对“Me Too”运动的兴起,为右翼杂志《旁观者》撰稿的道格拉斯·穆雷曾抱怨说:“规则正在被重新制定,然而人们却不知道这个新的性别乌托邦的边界在哪里,更不清楚最终是否允许存在任何性别。”
38
试想一下,居然有人在听到女性为“性骚扰”大声疾呼后,得出了“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可能存在性别”这样的结论(而且,作为一个白人男性,他还能如此自信地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批评压迫性言论与右翼评论家所描绘的那种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之间并无明显的逻辑连接:这个“斜坡”其实一点也不陡峭。
道格拉斯·穆雷的“很快就没有性别”的言论正是那些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在遇到新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时,迅速夸大其词并陷入慌乱的一个典型例证。保守派因其曾经熟悉的世界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而大发雷霆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戳穿了“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年轻人往往过于敏感”的谬论。
尽管那些追求“政治正确”的公义性目标的人试图保护人们免受伤害,但那些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在反对特定的行动或行为时所捍卫的内容却并不总是那么清晰。至少在某些时候,他们似乎是在表达一种我们都会时有经历但鲜少有人愿意大声说出来的不适感:“世界正在改变,我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我不喜欢这样!”耐人寻味的是,对于那些表面上支持以自由和个性为基础的政治的人来说,这些怒火大多与对现行规范和制度缺乏足够的尊重有关,例如:人们不尊重国旗!那个政客没有向女王鞠躬!他们为什么允许新闻播报员不戴罂粟花
 就出现在电视上?他们提供素食!年轻人吃牛油果!
就出现在电视上?他们提供素食!年轻人吃牛油果!
 我在超市里听到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在超市里听到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
此类例子数不胜数。2020年,英国百货零售商Argos推出了一则以黑人家庭为主角的广告,却因此遭到投诉,被指广告“完全不能代表现代英国”。一名推特用户甚至表示:“原来@Argos_Online对白人无感。好吧,那我们就去买别家的东西。让我们看看@Argos_Online离开了白人顾客还能撑多久!” 39 (Argos 之前也推出过一则以蓝色外星人家庭为主角的广告,却没有收到过“完全不具代表性”的投诉。)英国连锁面包店Greggs推出素食香肠卷后(普通猪肉香肠卷仍然有售),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皮尔斯·摩根大发雷霆。2016年,美国橄榄球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在比赛开始前奏美国国歌时单膝下跪,以抗议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其他球员也纷纷效仿。然而,他们的举动却引来了特朗普的严厉批评,他声称这些下跪的球员“不配待在这个国家”,并建议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解雇他们。 40 (不到一年,卡佩尼克就发现自己遭到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针对,他因政治观点被所有球队列入了黑名单。)一位校长分享了一张被剪成碎布的耐克T恤衫的照片(耐克是卡佩尼克的赞助商)并配文“只要耐克选择反美暴徒为品牌代言,我就不再支持、穿着、购买或认可他们的产品” 41 。2017年,一名休斯敦少年因在向美国国旗效忠宣誓时拒绝起立而被学校开除。 42 一些法国学校已经取消了所有不含猪肉的餐食选择,以证明他们没有向伊斯兰教的教义妥协。 43 这些学校在狂热地要求穆斯林学生表现出他们是心怀感激、融入法国社会且爱吃猪肉香肠的法国公民,从而屈从于“法式世俗主义”的同时,也把不吃猪肉或喜欢在午餐时间作其他选择的人排挤在外。(这实际上侵犯了另一种法国价值观:自由。)因为在11月时没有佩戴红罂粟花,英国黑人新闻播音员查伦·怀特被人用不雅语言攻击,人们还让她“滚回老家”。时任工党领袖的杰里米·科尔宾曾身穿一件防水连帽夹克参加战争纪念仪式,因穿着不够得体(他戴了红罂粟花)而被指责“不尊重”阵亡将士。新闻播音员乔恩·斯诺也遭到了批评,他将保守派痴迷于佩戴红罂粟领章的行为称作“罂粟花法西斯主义” 44 。
人们可能会像作家约翰·威尔逊在大约30年前那样,将这些案例视作“保守正确”(conservative correctness)的实例, 45 或是像分析师亚历克斯·诺拉斯特在2016年所做的那样,将它们归为“爱国正确”(patriotic correctness)。 46 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年轻人常被指责为过度敏感的“玻璃心”,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但他们的敏感往往集中表现在尽量减少对边缘群体的伤害这一方面。这体现了一种道德感。那些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往往同样敏感,但他们通常关注的是如何维护那些已经得到当权者支持的传统。认为年轻人无法承受“现实生活”逆境的观点也站不住脚。“现实生活”到底是什么?之所以有人要求使用善言善语,是因为我们可以借此让这个世界变得轻松一些。我们应该控制自我,让彼此免受侮辱。认为“政治正确的语言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必须能够应对不顾及他人的残酷言论”,就好比在说:“必须允许我成为种族主义者,否则人们将无法应对种族主义。”如果我们能消除生活中一些可消除的伤害,就能保存更多的能量来解决更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