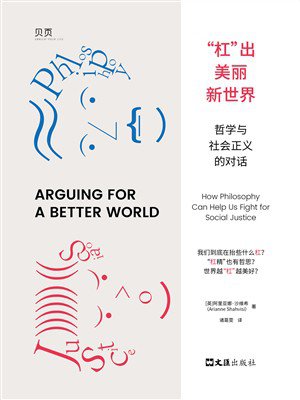现代礼仪
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年,我们开始接受礼仪教育。老师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规则。她告诉我们,与家人一同吃饭时,手肘不得上桌,要礼貌地说“请递给我盐,好吗?”,甚至在离席之前,还需征得同意。(在我家,大家吃饭时都习惯把手肘搁在桌子上,十分钟内风卷残云地吃完,然后各自忙各自的事去。)老师还叮嘱我们,在没听清或不明白时要说“请再说一遍好吗?”而不是“你说什么?”。女生要学会行屈膝礼,男生要学会鞠躬。然而,这些繁文缛节对我来说都显得有些专横。即使当时只有四岁,我也能感受到这些烦琐而无理的纪律束缚,内心不免生出几分抵触。
这种令人费解的“举止礼貌”的要求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直到中学时期仍如影随形。一位中学老师曾告诫我,往学校操场上吐橘子籽儿的举动不是“淑女”所为。进入大学后,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街头漫步,因为没有走在外侧保护我这个“弱女子”免受车流或水坑的侵扰,我的朋友竟遭到了陌生人的指责。
礼仪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可接受的社会行为的准则,尽管有时显得矫揉造作且难以理解,却在维系社会和谐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常被用来巩固社会等级制度,但同样也能激发对他人的关怀与尊重。政治正确的言行规范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礼仪,这种类比对于我们探索鼓励某些言论、谴责其他言论的初衷与潜能大有裨益。
礼仪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与他人相处,以期达到各种预期的效果。有些礼仪注重卫生与安全。例如,如厕时关门、进家门前先脱鞋、不用便后用来清洁身体的手取食和打招呼。这些都可谓实用的礼仪。一些礼仪则更侧重于对他人的体谅与关怀,例如为过往行人留门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主动让座。这些准则具有道德目的:它们提醒我们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还有一类礼仪则是以强化特定社会规范为目的的象征性行为。这类礼仪往往与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社会阶层化体系紧密相连,因此往往会强化令人不安的等级制度,加深不平等。在英美文化中,礼貌的言谈往往要求你在称呼群体时使用“女士们、先生们”,在与个人交谈时使用“先生”“女士”“夫人”“小姐”等称谓来强调被称呼者的性别。正式场合的着装也夸大了性别的差异:在西方,日常穿着的中性的牛仔裤和T恤衫被西装、领带或华丽的礼服所取代。屈膝礼和鞠躬礼更是彰显了性别与阶级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从事低薪服务工作的人员(如服务员、售货员)被要求以“先生”或“女士”来称呼他们服务的对象,同时表现出顺从。“优质客户服务”的理念往往要求低薪员工对客户彬彬有礼——往往是过分的彬彬有礼——却不图任何回报。透露自己的工资或询问别人的工资往往被视为无礼之举(有时甚至被合同明令禁止),因为这会让员工认识到薪酬差距,核实自己是否得到公平报酬。
举止得体的男人或男孩被誉为“绅士”,他们以骑士般的风度对待女性,如为她们扶门,主动承担体力繁重或令人却步的任务,天冷时递上自己的夹克或毛衣以表关怀,送她们回家,慷慨付账,甚至送上鲜花。 47 “淑女”们饮酒有度,保持着良好的男女交往尺度,穿着整洁迷人但不失端庄,不过于聒噪或大声喧哗,远离粗俗之语,不暴饮暴食,也不会草率或匆忙行事。换言之,彬彬有礼的男性以对待孩子或病人的温柔与细致来呵护身边的女性;温文尔雅的女性则将自己装扮得既体面、矜持又不张扬,宛如精美的装饰品一般。礼仪成为塑造性别角色的重要因素。正如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赖伊所言:
开门这一举动,看似是一种体贴的服务,但实际上这种帮助往往流于形式。无论这个动作是否有实际意义,男性都会这么做,我们由此便能窥见一二。即使是体弱的男性和身负重担的男性也会为健康的女性开门。他们会急切地,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地抢在前面去开门……但是没有人帮女性清洗(他的)脏衣服;没有人帮女性在凌晨4点完成报告;没有人帮女性调解亲戚或孩子之间的纠纷。 48
在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中,72%的受访者认为现今社会的礼貌程度正逐渐下滑。 49 其中,最令受访者不满的是那些吝于使用“请”和“谢谢”的人,许多人将此归咎于学校和家长。 50 显然,这反映了一种代沟。年轻人承认,他们经常做出一些老年人眼中的不礼貌行为。例如,29%的人不遵守排队秩序,53%的人在别人打喷嚏时不会送上“上帝保佑你”的祝福,更有84%的人认为使用“请”和“谢谢”以及为别人扶门这些传统礼节已经过时。 51 这似乎印证了老年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年轻人既无礼又不体贴。
然而,事实远比这复杂。年轻人在摒弃某些旧有礼节的同时,也创造并接纳了新的礼仪形式。说脏话就是一个颇有趣味的例子。一般来说,年长的人更讨厌别人说脏话:在5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45%的人对电视节目中的脏话感到反感;相较之下,18岁至34岁的人群则更习惯于说脏话,而且对脏话的抵触情绪较低。 52 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有近半数坦言他们经常使用冒犯性言辞,而在55岁至64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12%。 53
思考冒犯性语言的根源至关重要。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喜欢把这类词挂在嘴边,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带有歧视含义的词,我们永远都不会脱口而出。
 此外一个针对东亚人的蔑称
此外一个针对东亚人的蔑称
 依然被视为不可触碰的雷区。同样,“黑鬼”(nigger)一词如今也成为不可言说的敏感词。我们关注的不是语言文雅与否,而是避免使用那些旨在伤害受压迫群体的言辞。从道德层面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让人困惑的是,为何连一些普通的粗鄙之语也会遭到禁止?事实上,这些词汇不仅为我们的语言增添了色彩,还能起到语言强化剂的作用,赋予我们更丰富的情感表达空间。比如,“我快累死了”所传达的疲惫感远超“我好累”。这些词汇并没有特指的侮辱人群,像“狗屎”这样的辱骂可以针对任何人。但相比之下,另一些词则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充斥着对同性恋者和黑人的暴力与排斥。正如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所言:
依然被视为不可触碰的雷区。同样,“黑鬼”(nigger)一词如今也成为不可言说的敏感词。我们关注的不是语言文雅与否,而是避免使用那些旨在伤害受压迫群体的言辞。从道德层面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让人困惑的是,为何连一些普通的粗鄙之语也会遭到禁止?事实上,这些词汇不仅为我们的语言增添了色彩,还能起到语言强化剂的作用,赋予我们更丰富的情感表达空间。比如,“我快累死了”所传达的疲惫感远超“我好累”。这些词汇并没有特指的侮辱人群,像“狗屎”这样的辱骂可以针对任何人。但相比之下,另一些词则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充斥着对同性恋者和黑人的暴力与排斥。正如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所言:
不要对女性使用你不会对男性使用的侮辱性语言。你可以用“混蛋”“白痴”或“蠢货”,但不要用“婊子”“妓女”或“荡妇”。如果你叫某人“蠢货”,那么你只是在批评她的停车技术。但如果你骂她“婊子”,就是在贬低她的性别。 54
“政治正确”的要求并不是什么噱头,也不是为制造生活障碍而设置的烦琐规定;相反,它是对第二类礼仪(那些鼓励我们体贴他人的礼仪)的延伸,是一种对不公正现象极为敏感的社交礼仪。与旨在维护社会地位等级制度的第三类礼仪不同(幸好这类礼仪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种新的行为准则主要是为了促进我们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政治正确”是由那些希望通过改变我们对待彼此的一些规则来颠覆权力场的人制定的一套习俗。
这套新礼仪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在称呼个人和群体时,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使用他们不希望你使用的方式来称呼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应使用他们指定的姓名和代词
 。违背这一原则不仅显得古怪,而且充满恶意。(更糟糕的是,违背他人意愿强行为其命名、将其分类的行为,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在与群体交往时,应使用该群体成员创造的词语,避免使用他们认为具有伤害性的言辞。
。违背这一原则不仅显得古怪,而且充满恶意。(更糟糕的是,违背他人意愿强行为其命名、将其分类的行为,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在与群体交往时,应使用该群体成员创造的词语,避免使用他们认为具有伤害性的言辞。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简单明了。关于哪些词汇最为恰当仍存在争议,而且这种争议的焦点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变化。例如,关于究竟是使用“残疾人”(disabled person)还是“残障人士”(person with a disability)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残疾活动家们对这两种观点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我们应该欣然接受围绕这些术语产生的摩擦和动态变化,因为这正是我们反对陈规旧俗、防范独裁主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