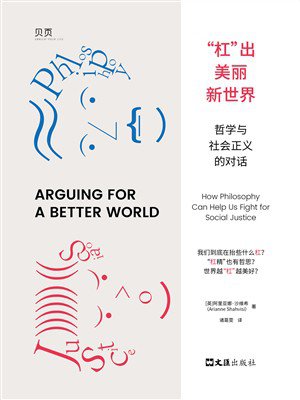新禁忌
去年夏天,一位白人朋友告诉我,她所在的中学曾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她举例说,学校经常使用P字词(源自“巴基斯坦”一词的种族主义蔑称)。她没有使用“P字词”这种委婉表达,而是直接说出了整个单词。这让我感到非常不悦。这个词曾给我的家人和我伴侣的家人带来伤害。在我们家,这绝对是一个禁忌词。在我所描述的新礼仪中,“不可说”(unutterable)的词汇这个概念是一个颇具争议却又十分重要的特征。
蔑称是那些用于羞辱、侮辱、恐吓、贬低他人或表达仇恨情绪的有害的词语或表达。 55 它们不仅表达蔑视,还倾向于将所提及的群体同质化、非人化。哲学界涌现了大量关于这类复杂语言实体的文献,但在此我们仅需探讨它们的一些基本特性。 56 在其使用语境中,蔑称是广为人知约定俗成的术语,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能充分理解这些词汇的传统含义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负面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这些蔑称的使用,而应将其视为系统的一部分来理解,正是这个系统赋予了它们特定的意义,并使其具备伤害性。
蔑称利用并激活了一系列有害的背景假设,进而强化了这些假设。就像它们经常利用的刻板印象一样,每当这些词汇被提及,都会加深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例如,称某人为“荡妇”便体现了父权思想,即女性的性行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如果脱离了这种意识形态背景,“荡妇”一词就失去了意义;而处于这种背景下,该词便承载了一系列有害的假设和限制,并因不断被提及而得到强化。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
如果不自引,种族主义言论就不具备种族主义性质;正是基于我们先前对其威力的了解,我们现在才意识到它的冒犯性,并警惕它在未来的出现。 57
哲学家对使用术语和提及术语进行了明确区分:有时我们是在使用某个词汇,但有时我们只是在谈论这个词。例如,当我说“种族主义是有害的”时,我就是在使用“种族主义”这个词;而当我说“如果你会拼‘种族主义’这个词,就能在拼字游戏中拿到10分”时,我仅仅是提及这个词。直觉告诉我们,提及蔑称的危害远不及使用蔑称。例如,“有些人管女人叫‘荡妇’”的表述,其伤害性远小于“有些女人就是荡妇”。
听到有人提及N字词,其伤害性并不如听到有人使用这个词那么强烈,当然,最好还是不要听到这个词。即使是在出版物中使用这个词也会引发问题。如果我们在此处将N字词完整地写出来,那么有声读物的朗读者就必须将其读出来,听众也不得不听到这个词。甚至在印刷品上出现这个词也可能造成伤害。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在阅读时,即使只是快速浏览和默读,我们的声带也会轻微颤动,就像在无声地念出单词一样。 58 这意味着写出一个特定的词汇会迫使读者进入一种与他们念出这个词时相似的生理状态,如果本可以使用一个广为人知的委婉语却仍然使用了这个特定词,这种情况就尤为令人不安。
采用“N字词”这种委婉表达来替代它所指的蔑称,不仅是为了避免使用有害的言语,也是为了展现一种鲜明的立场。它彰显了对某个特定词汇及其背后体系的否定,同时也在对话中巧妙地插入了一个停顿,让听者意识到说话人回避了某个特定词语,并迫使听者接受这种否定,促使人们反思并抵制那些赋予该词意义的潜在背景和偏见。
有时,受影响的边缘化群体成员也能以轻松且不带恶意的方式使用这些蔑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它们。例如,用来指代同性恋者的“酷儿”(queer)一词曾是一个蔑称,而非表达自我认同的术语,但是现在,人们几乎都是以积极的方式来使用它。美国作家塔那西斯·科茨指出,在这些情况下,使用该词的人的身份至关重要,因为其他人并无权利随意使用这些词汇。 59 尽管一些书籍、电视节目和电影为了真实反映其所描绘的世界而使用了蔑称,但许多评论家指出,在一些情况下,本可以通过其他更具思想性和信息量的方式来展现反黑人种族主义的恐怖,但N字词因其带来的冲击而被过度使用。罗克珊·盖伊指出:“N字词当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靠嘻哈音乐和说唱歌手就能维持生命力。白人也一直为这个词注入生命力和活力。” 60 她承认,在适当的情境下使用这个词可以有效地传达出种族主义的力量,但她也观察到,在《被解救的姜戈》这部片长近三个小时的电影中,这个词的出现次数达到了惊人的110次。换言之,在这部对白并不密集的影片中,平均每三分钟就会出现两个N字词。盖伊将《被解救的姜戈》描述为白人试图从奴隶制的恐怖中获得救赎的一种方式。也许有些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总是在讲述一件可以证明他们反种族主义资格的轶事时,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个词。把这样一个可怕的词挂在嘴边是一种自我鞭挞,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自己不是会使用这个词的人。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使用蔑称来铭记其恶劣性质。
哲学家勒妮·乔根森·博林格指出,提及蔑称仍有可能表现出冒犯性态度,“从单纯的麻木不仁到以说令人不快的话为乐,再到无视怂恿使用贬损性蔑称这一风险” 61 。不管一个人的态度或话语的背景如何,蔑称仍然可能带来伤害。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即使只是提及蔑称,也可能激活隐性偏见,导致蔑称的目标群体成员面临刻板印象的威胁。 62
蔑称危害性极大,很容易引发恐惧和不适,以至于即使某些没有被明确用作蔑称的词语,或只是听起来像蔑称的词语,也可能被用作狗哨(见第3章),或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一位朋友曾在一次演讲中使用了“chink in one’s armour”这个习语(意指弱点或致命缺陷,但chink现在常被用作蔑称
 ),她一边说,一边抬头看了看全班同学,发现唯一与她有眼神交流的是一名中国学生,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虽然她使用这个词并非要表现蔑视,但在那一刻,两者在学生心中却紧密相连——学生听到了蔑称——因此,她决定以后再也不使用这个短语了。
),她一边说,一边抬头看了看全班同学,发现唯一与她有眼神交流的是一名中国学生,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虽然她使用这个词并非要表现蔑视,但在那一刻,两者在学生心中却紧密相连——学生听到了蔑称——因此,她决定以后再也不使用这个短语了。
某些词汇虽然不包含侮辱性的意味,但它们依然能引发人们的不安。以denigrate(诋毁)为例,该词意为贬低或轻视某人或某物。其词源中,de来自拉丁语,表示“远离”或“完全”,而nigrate则与N字词同根,都可追溯到拉丁语中的“黑色”一词。从字面意义上来看,denigrate指的是抹黑事物或使之暗淡。在日常语境中,denigrate常用来描述对某人或某事的侮辱、辱骂或其他形式的负面评价。当我们用denigrate这个词来表达负面含义时,无形中强化了黑暗或黑色的东西与邪恶之间所谓显而易见的关联。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对黑暗的邪恶引申并非源自种族,而是来自对黑夜的合理恐惧。但现在,denigrate所承载的负面意义与N字词已相差无几。
2017年,英国小报《每日邮报》刊登了梅根与哈里的订婚照片,并配以标题“是的,他们幸福地相爱了。但为什么我对这张订婚照有一丝隐隐的担忧呢?” 63 。哲学家利亚姆·布赖特因此在推特上调侃道:
《每日邮报》的标题应该改成“我对梅根的隐隐担忧——她是不是太在意吝啬的细节了?我们在尼日尔度假时,一边喝着内格罗尼酒,一边讨论她性格上的这个污点”。
64

禁忌语并非新时代的产物,而是许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常与性、身体部位和功能(屎、尿)以及超自然现象(该死、上帝、地狱)等敏感话题有关。在讨论死亡和疾病时,通常也需要使用委婉语(例如,说某人“作古”了)。关于这些词语的使用和语境,有正式和非正式的严格规定。例如,英国明确规定了哪些词汇可以在晚上九点前的广播时间使用。
 在许多社交场合中,说脏话或讨论性、排泄物或死亡细节都是不恰当的。
在许多社交场合中,说脏话或讨论性、排泄物或死亡细节都是不恰当的。
人们认为,规范禁忌词语的目的是避免谈论涉及神圣、令人厌恶或私密的话题。禁止使用这些词语有助于维护更广泛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感觉说“屎”很奇怪,那就有助于确保他们继续将排便视为一种需要以正确、卫生的方式进行的肮脏活动,并将性视为一种受规则约束的私人活动。
要求人们避免使用N字词并非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禁令的一部分,旨在将反黑人种族主义纳入社会禁忌的范畴。P字词与针对南亚人的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F字词与同性恋恐惧症之间的关系、C字词与反东亚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不允许说这个词,就是在提醒你存在一系列与言论和行为相关的道德约束。因此,当某人发现某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时,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试图理解相关的道德问题。
最后一点有助于回应那些指责“政治正确”仅为“美德信号”的观点。那些呼吁谨慎用语的人有时会被指责过于在意塑造正义的形象,而非推动“实质性”变革。但首先,公开践行美德并非如人们所言那般可怕。(这一点值得另辟一章!)它可以展示变革性、团结性行为的可能性,并可能提振人们的士气,让抗议运动变得更加有益。 65 其次,这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语言对于构建我们所处的道德环境至关重要,而解放性的语言与行动是相互交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