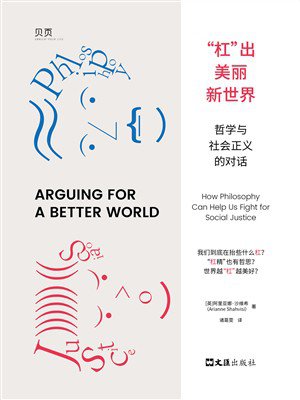压迫初探
压迫的实例可以通过一系列典型特征加以识别,包括因个人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而遭受某种不公正的负面待遇;此类待遇有历史先例,是社会组织方式所产生的模式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也就是说,它具有结构性。
对女性的压迫由来已久,现实毫无改善,令人沮丧。在中世纪的欧洲,不论是通过设计并使用避孕和堕胎方法来掌控自身生育能力的女性,还是被视为不守规矩、令人不悦或缺乏女性气质的女性,都有可能被冠以“女巫”之名而遭处死。直到20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已婚女性才在法律上摆脱“夫妻一体”的束缚,而此类法律曾将她们视为丈夫的附属品,即她们的所有法律决策均由丈夫代行。而“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并无法律保护女性免受这种普遍的性别歧视伤害。1736年英国的一部法律汇编曾明文规定:“丈夫强奸妻子并不构成犯罪,因为在婚姻成立时,妻子就作出了不可撤回的同意。”这意味着,女性一旦结婚,便等同于给予了丈夫无限制的性同意。这项法律直至1991年才被废除。因此,在我所经历过的年代,英国男性可以强迫妻子与其发生性关系,而这并不算是强奸。 10
当代的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带有历史的烙印。虽然女性不再被视为丈夫的附属品,但在英国,仍有90%的已婚女性冠夫姓;在美国,仅有3%的已婚男性从妻姓。 11 尽管在许多地方,女性的身体似乎已经从丈夫和父亲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对于那些拥有子宫的女性来说,生育自由仍然岌岌可危。决定何时怀孕、是否怀孕或继续怀孕的权利始终受到威胁。虽然我们已不再提及“女巫”这样的字眼,但在包括美国某些州在内的许多司法管辖区,终止妊娠的女性和帮助她们的医务工作者仍可能面临牢狱之灾。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了孕妇受宪法保护的堕胎权。他在判词中引用了17世纪法学家马修·黑尔的观点。黑尔不仅撰写过颇具影响力的巫术主题专著并以此为由判处女性死刑,还一手将婚内强奸不算强奸的条文写入了法律。
种族主义同样符合这一历史标准。据估计,曾有1300万非洲人被绑架,并被强行带离他们的家园和亲人,被锁在船舱下的狭小空间内,在自己的排泄物和呕吐物中挣扎求生。那些病重或死亡的人被抛入大海。而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则被丢进一个陌生的世界,被迫从事繁重的无偿劳动。他们的孩子被卖掉或送给其他人,继续遭受同样的命运。认为黑人是野蛮的次等民族的“科学观点”助长了抓捕、奴役和压迫黑人的行为。这种观点为白人的道德价值设定了一个上限,从而使得压迫者能够以最小的罪恶感对他们进行剥削。
这段历史常常被描述成属于遥远过去的一种已不复存在的道德制度(尽管在撰写本书时,奴隶制存在的时间竟然仍比其被废除后的岁月漫长,而且在美国,监狱中的奴役劳动仍然受到宪法的庇护)。但是正如昔日奴隶的汗水铸就了欧洲与北美国家的繁华一样,奴隶制也塑造了当今的道德风貌,并深深影响着反黑人种族主义的特征和持久性。当代的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余孽;而殖民主义,又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产物。种族主义曾是经济制度自我辩白的手段,在那种令人发指的制度下,它需要在不同人群间制造并强调差异,并以虚假的科学论调支撑这些差异。将殖民主义视为过往云烟,是对种族与种族主义的起源与目的的漠视与误解。在美国,“自由”终究演绎成恶毒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警察、司法机构与监狱体系承袭了对黑人的征服与压制。正如非裔美国学者赛迪亚·哈特曼所言:“我也生活在奴隶制时代,我指的是,我正生活在奴隶制所铸就的未来之中。” 12
1833年的《废除奴隶制法案》终结了英国的奴隶制,主要原因并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是因为奴隶制已利润无多,而且奴隶叛乱越来越难以镇压。 13 英国急切地对奴隶主进行了“财产”补偿,以弥补他们失去的合法所有权。此举所费不赀,财政部不得不背负相当于190亿美元的债务,直至2015年才偿清。这意味着大部分英国劳动者都曾为“补偿”奴隶主贡献了税赋。然而,曾为无偿劳役耗尽一生的昔日的奴隶,却未得到分文补偿,他们的后裔也同样一无所获。那些失去了亲人的非裔社群未曾得到任何慰藉,反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持续遭受露骨的殖民统治。时至今日,他们依旧面临着经济的边缘化与资源被掠夺的问题。在英国乃至更广阔的地域里,黑人不得不在这个充斥着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世界中艰难求生,而这个世界又限制了他们的健康状况、预期寿命以及教育与就业的前景。
尽管现在,宣称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先天差异的做法已变得越来越为社会所不容(部分原因在于,种族差异具备科学依据的观点已被反复而有力地驳斥),但是,有关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生物学差异的谬误仍然普遍存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美国白人医科学生和医生中,有一半对种族间的生物学差异抱有谬见,包括认为黑人的神经末梢较白人更为迟钝、白人的脑容量更大、黑人的皮肤更为厚实等。 14 这些谬误导致的后果极为严重:由于偏见,黑人患者常因痛感被系统性地质疑而得不到充分治疗。例如,事实表明,患有阑尾炎的黑人儿童所能获得的止痛药,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效果上,都远不及白人儿童。 15
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无端伤害,绝非凭空产生;这种伤害由来已久,也证明了想要根除这些伤害是何等艰难。这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我们不仅需要深入学习历史,使其成为当下切实可感的重要部分,更要避免让现存的种种不公,继续以神秘莫测、不可避免且貌似永恒不变的面目示人。
历史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进一步突出了压迫所带来的伤害。每当一个女孩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她就加入了一支由女孩和妇女组成的具有几千年历史的队伍,她们都曾忍受同样的愤怒、羞耻与侵犯。这种漫长的阴影使侵犯行为显得更加严重,也让受害者感到更加绝望。
在某些情况下,历史背景是赋予事件伤害属性的核心因素。如果一个白人在化装舞会上戴上非洲黑人的假发头套,或是把脸涂成黑色或棕色,而此人对历史或其重要性一无所知,那么他的这一举动所带来的伤害可能就并不那么不言自明。黑人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黑人歌舞表演采用的一种妆发造型,白人表演者通过这种方式迎合并强化了关于黑人的夸张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他们的表演将黑人描绘为丑陋、愚蠢、虚伪、轻浮、怯懦、过度性征化和懒惰的形象,以此娱乐白人观众。倘若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很难理解为何黑人妆如此令人受伤与愤慨,也很难认识到这种行为在延续种族主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黑人妆出现在精英教育机构的聚会上时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无知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这些行为更像是一种旨在巩固主导地位的公认的笑料。)然而,如果黑人将脸涂白(可能是为了扮演小丑或模仿白人)时,却并无此种含义,而仅仅是妆发造型的一部分而已。历史打破了两种本可相提并论的行为之间的对称性。 16
无论是黑人妆、性侵犯,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触及了人们对痛苦、屈辱和暴政的更深、更久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尚未得到充分正视,更遑论得到补偿。这正是压迫有别于其他形式的伤害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如社会学家萨拉·艾哈迈德在《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一书中所言:“我不愿遗忘那些尚未终结的历史。” 17
最后,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压迫具有结构性,也就是说,它源自比任何个体行为都更深层、更具影响力的原因。无论是在资源还是在尊严层面,“结构”都是调节社会价值分配的力量。正如引力是由具有质量的物体所产生并作用于所有具有质量的物体一样,结构也是由我们的集体行为所创造,同时制约和决定着这些行为。我们并非有意促成结构,而只是对我们所受的影响作出反应,就像行星被恒星的引力拉入轨道,此后必然会以可预测的方式运动一样。当谈到压迫具有结构性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要理解压迫的运作方式并解决其所带来的伤害,就需要研究整个制度,而非仅仅专注于个体或机构的行为。
例如,在英国的医院中,薪酬最高的职位(如医生和管理层)主要由白人担任,而薪酬最低的工作(如清洁工和搬运工)大多落在黑人的头上。乍一看,这一现象似是由负责招聘的员工个人存在种族歧视所致,但很明显,还有其他因素在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显然,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不均等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不均等,追根溯源,与营养、住房和医疗等其他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例如,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这种尊严分配的不平等?医生和管理层的收入是否理应高于清洁工和搬运工?薪酬等级制度是否应该存在?)
压迫人们的结构是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协商,甚至忍受。想象一下,当你试图在城市中寻找一条通往目的地的最短路径时,却遇河流阻断,无桥可过。你决定转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又发现自己手头没有零钱,而其他人都有公交卡。无奈之下,你改回步行,但这条路并非为行人而设,你不得不沿着高速公路的一侧艰难前行,不仅生命安全堪忧,还要吸入汽车尾气。这便是压迫的真实写照。诸多障碍有待克服,若非身受其害,人们绝不会将这些特征视作障碍,甚至根本不会察觉,或是难以理解他人挣扎之苦。
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抽象。结构性压迫的影响在女性为防范街头性骚扰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选择的路线或许不是最直接、风景最优美或最适合步行的路线;我们戴上墨镜和耳机,以隔绝不必要的关注;我们会佯装在通话;我们甚至会根据衣服的款式和颜色可能引来的评头论足或是暴力威胁来选择着装(有些女性坦言,红色让她们觉得自己太过“鲜艳”和显眼);我们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既不显脆弱也不露悲伤或怒意,以免招来“振作点”或“笑一笑”这样的无理要求;更有甚者,我们还可能会因为拒绝扮演快乐的女性而遭到攻击;我们将钥匙夹在指间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也不忘向朋友和姐妹们报平安。 18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对于被种族化的女性而言,风险更甚,需要适应的环境更为复杂多变,而暴力行为的发生也往往更加突如其来。我们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这些应对策略,并在公共空间中日复一日地实践,以至熟能生巧,甚至能够下意识地做出反应,而大多数男性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本无须承受这样的压力和焦虑。
压迫具有结构性,因此如影随形,无孔不入。它所引发的障碍与羞辱,可能在无数场合不断上演。然而,“逆向种族主义”和“逆向性别歧视”却并非如此。白人偶尔被称为“白人婊子”,这或许只是个别事件,虽然令人不快或心生畏惧,但应对这种偶发的侮辱,与持续不断地承受侮辱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对于有色人种而言,“滚回去”或“滚回你的国家去”的呼喝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而这往往还只是种族主义辱骂中较为温和的部分。更糟糕的是,这些冒犯常常伴随着更为直接和严重的暴力威胁。相较之下,反向种族主义在现实中则显得根基不稳,难以直接引发更为严重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