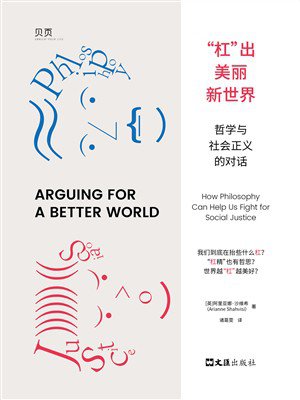哭泣、关怀与监护权
当人们提及男性享有特权时,常会遭遇这样的反驳:男性的生活往往更为艰难、残酷,生命也更为短暂。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寿命普遍短于女性,且更容易被杀害或选择自我了断。为了赚取足够的金钱来养活家人,他们常从事危险、肮脏且屈辱的工作,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默默忍受身心上的双重折磨,却又不能显露半点软弱;此外,他们更有可能被征召上战场。
无可否认,男性特质对男性和女性均造成了伤害。但这种伤害颇似化疗:尽管有毒且伴随一系列严重的副作用,却仍有可能带来益处。正是那些赋予男性权力、自主性与社会地位的行为,让他们深受其害。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男性肩负重担,但这往往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大的经济权力和自主性,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并有能力摆脱不幸的家庭环境。男性因性别特质获得的益处往往要大于“副作用”,但女性面对的只有“副作用”。成功的女性特质,意味着女性具备吸引力、和蔼可亲、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等特质。这要求她们必须随时准备满足他人,尤其是来自男性的需求——无论是性需求、情感需求还是家务需求。而这需要女性自我克制、作出牺牲并放弃自主性。未能达到这些理想状态的女性,有时会面临被忽视、排斥,甚至遭受敌意与暴力的风险。
牢记这种差异,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些用来论证男性因其社会角色而受到压迫的具体案例。这种压迫具有结构性、群体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例如:男性通常不能在公共场合流泪,他们往往被认为不适合从事护理工作或提供无偿关怀,甚至在寻求子女的合法监护权时也常被忽视。
诚然,男性会因在他人面前哭泣而受到更为严厉的评判。这是广泛存在的情感压抑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不仅损害了男性的幸福感,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然而,女性却可以在公共场合流泪,这就类似于婴儿在公共场合排便,不会有人为此发出责难:我们之所以不在乎婴儿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也知道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关于女性天生情绪化的刻板印象普遍存在,人们以此质疑女性作为优秀决策者或领导者的能力,并据此剥夺她们应有的权力。女性在公共场合流泪而不会被指摘的根源在于,人们认为她们在情绪上缺乏控制力,因此即使她们公开显露这一缺点也没有关系。相比之下,男性则被认为更加坚强,情绪也更加稳定,因此他们需达到更高的标准。
此外,“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要求主要是由男性负责监督的,那些能够克制自己脆弱情感的男性也因此赢得并保住了社会地位。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赖伊曾于1983年写道:
男人可以哭吗?在女人面前可以。如果不能,那是在其他男人面前。需要如此这般克制自己的是男人,而非女人;男人不仅需要这种克制,还对此给予奖赏……践行这种自我约束,对他们而言是有好处的。 19
投身护理行业的男性也常常会遭到嘲笑,因为这种选择意味着他们自降身份,去做了所谓“女人的工作”。《老友记》中就有这样一幕:瑞秋和罗斯正在为他们的孩子面试保姆。 20 好几位女性都申请了这一职位,但由小弗雷迪·普林兹饰演的唯一一位男性候选人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罗斯对于雇用一个男人来照顾他们的孩子感到十分不自在,觉得他过于温柔细腻,多愁善感,令人不适。最终,罗斯毫无理由地解雇了他。 21
全职爸爸并不多见,而且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找不到一份“正当的”工作,或是“受制”于“当家”的伴侣。那些以职业身份照顾非亲生孩子的男性,也常常会遭到人们的猜疑。同样,接受护士培训的男性也常常会受到嘲笑,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同性恋,或是被误认为医生。一名男护士在撰写一篇关于护理行业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文章时,就曾回忆道,有人这样问过他:“你是因为不够聪明,所以才没当上医生吗?”
22
这句话耐人寻味。当护士的女性就从来不会被人问及,她们是否具备足够的聪明才智去当医生。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两个别有用心的假设:一是医生比护士更聪明,而这种观点建立在人们对“治疗”与“护理”的不恰当划分以及二者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
 ;二是男性更加适合从事那些“需要聪明才智”的职业,而养育孩子这类的工作则更适合由女性来承担。
;二是男性更加适合从事那些“需要聪明才智”的职业,而养育孩子这类的工作则更适合由女性来承担。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照顾老幼病弱的护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忽视,因为这类工作在私人领域通常是免费的,而在公共领域则报酬极低。它们通常被人们视为“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也毫无吸引力可言,因此一般都由女性承担。虽然这类工作并未被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活动指标当中,但仅就无偿护理工作这一项而言,全球年估值就已高达10.8万亿美元,是英国经济规模的三倍多。 23
虽然从事这些职业的男性可能会遭到嘲笑,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认为护理工作有失身份。因此,这种嘲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所感知到的自卑或失败的一种反应。相比之下,那些最终从事典型的“男性职业”,如工程、航空或外科手术领域工作的女性,则会因为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并找到了回报丰厚的工作而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些反应也揭示出了我们对男性和女性,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工作所持有的等级观念。
最后,人们普遍认为男性不太可能获得孩子的合法监护权。然而,在英国,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根据2015年的一份报告,没有证据表明法院在裁决孩子应与父母中的哪一方生活时存在性别偏见。 24 而在美国,仅有4%的监护权案件是由法院裁决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监护权决策是由父母双方在没有法律干预的情况下共同作出的。 25 尽管如此,人们仍普遍认为母亲会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并且理应如此。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希望成为孩子主要照顾者或平等照顾者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一种阻碍(正如上文所述,那些担任主要照顾者的男性往往被视为异类或失败者)。然而,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于一个实际现象:女性承担了过多的育儿责任。在美国,当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时,女性每周投入的时间为14小时,而男性仅为7小时。 26 正因为女性通常是主要照顾者,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认知。这一现象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许多人认为孩子与母亲在一起是最佳选择;另一个则是,无论女性是否愿意,她们都常常需要承担大量且大多无形的额外劳动。相比之下,父亲在育儿投入方面则拥有更多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将父亲的参与描述为“临时照看”或“奶爸日托”,仿佛这只是一种爱好或恩惠),而且即使男性只提供了有限的照顾,也往往会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赞扬。因此,男性只要参与了育儿工作,就会被认为是出色的父亲。 27
男性在角色和行为方面的选择确实受到限制,但这些限制以及由此可能给某些男性带来的困扰,并非压迫的表现,而是特权的反映。这些限制源于一个事实:少数相当有限且地位较低的角色和行为——如展现脆弱、承担照顾职责——被划归女性的专属领域,并因此受到轻视和低估。男性被告诫不要涉足这些领域,却同时被鼓励将世界上其他的事情都视作他们的囊中之物。当然,对于大多数男性而言,世界显然无法任由他们支配,但让他们受挫的却并非他们的男性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