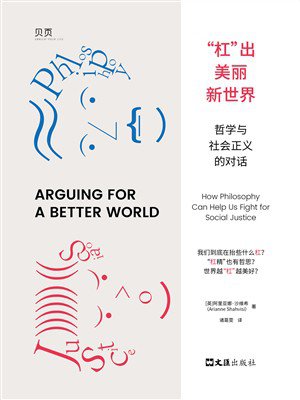避开“球体奶牛”谬误:交叉性的重要性
人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压迫具有单向性,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利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个旨在防止我们过度简化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一位农场主请一批物理学家帮助她找出奶牛产奶量不高的原因。物理学家们迅速投入工作,并很快得出了结论。不过他们强调,这一解决方案仅在奶牛以完美的球体形态在真空环境中吃草的情况下才成立。这则笑话告诉我们,物理学家们为了简化复杂问题,经常采用这种理想化的模型。球体因其高度的对称性在数学上易于处理,而在真空条件下,则无须考虑摩擦和湍流等复杂因素。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奶牛并非球体,也无法在真空环境中生存。这种适用范围有限且无用的解决方案忽略了世界的复杂性。
在讨论压迫问题时,我们也往往会陷入类似的“球体奶牛”谬误。我们倾向于简单粗暴地将人划分为整齐划一的身份群体,如“男性”或“黑人”,仿佛这些群体内部的人都足够相似,可以被视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然而,那些落在我们构建的清晰分类边界之外的人群却可能会因此而被完全忽视。我们的简化假设往往会对人群进行四舍五入的处理,从而彻底抹去某些人的存在。
正如女权主义理论家奥德丽·洛德在1982年所言:“生活不是单一的,所以生活中也没有单一的问题。” 28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特权与压迫也在个人经历中以不同方式共存。例如,我的父亲既是有色人种又是穆斯林,但他同时也是一名异性恋男性。我的母亲虽是白人,却是一名工人阶级女性。在他们的经历中,特权与压迫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谈论“男性特权”或“白人特权”可以揭示他们相对于彼此所享受的一些特权或经历的一些压迫,但这并不能涵盖他们的全部经历。更重要的是,如果脱离他们的其他身份来讨论这些元素,我们就可能会误入歧途。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社会身份如何相互作用并产生压迫与特权的混合体,我们引入了“交叉性”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是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金伯利·克伦肖在1989年提出来的, 29 但其历史可追溯至更早的激进主义运动。1977年,由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团体“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就曾表示,她们的组织目标是“基于主要压迫体系相互关联的事实,开展综合分析与实践。这些压迫的相互交织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条件” 30 。
交叉性警示我们,不要开展那些立足于某一特定受压迫群体共有经历的运动,因为这种做法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优先考虑该群体中最具特权者的利益。正如哲学家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所言:“仅处理‘纯’父权压迫案例的女权主义,即处理那些未因种姓、种族或阶级等因素而‘复杂化’的案例,最终只会为富裕的白人或高种姓女性服务。” 31 这种局限性也存在于种族和其他边缘化轴心问题的讨论中。假设有一项旨在解决伊斯兰恐惧症的倡议抛开了阶级、种族、性别和国籍等因素,仅仅关注穆斯林身份。然而,这种做法无法充分满足穆斯林女性和贫穷的无证非洲裔穆斯林移民的需求。事实上,穆斯林身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社会身份相互交织。因此,这种倡议无法真正帮助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
交叉性有时会造成一种误解,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由相互交织的压迫所构成的独特“指纹”,因此我们应该以个体的身份来处理社会正义问题,而不是作出假设或进行类比。然而,这种误解实际上为当权者所欢迎,因为它将挑战不公的责任转嫁到了个体身上,使普通人无法看到压迫之间的共性,由此错过系统性变革。将交叉性纳入考虑范围,可以鼓励集体行动,但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在开展运动时认识到压迫的相互关联性,并从最边缘化群体的需求出发。交叉性具有三个值得我们深入关注的特征:异质性(heterogeneity)、不可加性(non-additivity)和利益冲突。
异质性
关于交叉性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51年。19世纪,三场重要的社会运动在美国兴起:废奴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黑人选举权运动。 32 然而,无论是妇女选举权运动还是黑人选举权运动,都未能充分考虑到压迫的其他层面。“女性”仅指“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而“黑人”也仅指“黑人男性”。其他人在划分这些类别时,完全没有将处于这两种身份交叉地带的黑人女性和土著女性考虑在内。
一些黑人女性废奴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和女权活动家大声疾呼,反对这种隐形化。索杰纳·特鲁斯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出身奴隶家庭,后来成功逃脱,过上了自由的生活,成为一名巡回活动家。1851年,特鲁斯在俄亥俄州一场女权大会的演讲中提醒其他活动家,他们对女性身份的理解并不包括那些拥有与她相同经历的女性。她坚定地宣告“我代表女性的权利” 33 ,让自己和其他黑人女性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特鲁斯进一步指出,被用作剥夺女性权利借口的女性概念并不包括黑人女性。 34 用来证明剥夺女性选举权合理的论据,如她们过于柔弱、无法承受选举的严峻考验等,在黑人女性身上并不适用。因为黑人女性通常需要像男性一样从事繁重的劳动,并未因为所谓女性的娇弱或敏感而享受任何特殊照顾。她向在场的所有人保证,由于被迫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她与男性一样强壮。特鲁斯的演讲无疑是一种挑衅,要求那些谈论“女性”的人要么承认自己所指的其实是“白人女性”,要么就采用一种能够涵盖所有女性需求与经历的更加包容的女性概念。
女性的生活和需求具有多样性,而她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伤害(如贫困、国家暴力)往往与种族或阶级密切相关,并因性别问题而进一步加剧(如在剥削性的工作环境中遭受性骚扰)。奥德丽·洛德在1980年的一篇论文中对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女权主义进行了比较,她写道:
有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女性所共有的,有些则不然。你们担心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加入父权社会并反对你们,而我们却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人从车里拖出来当街枪杀,而你们却对他们的死因视而不见。
当代女权主义主要关注的仍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需求,过分聚焦于精英职位上的女性代表,如公司高层、政界、广播公司、富豪榜等,而工人阶级女性的需求却几乎被忽视,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色人种女性。对于她们来说,薪酬、工作条件、住房和儿童保育等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我们穿的几乎所有衣服都是由南亚和东亚血汗工厂中的女性缝制的,她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还时刻面临着性骚扰的风险。这难道不应该成为女权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吗?
不可加性
在一次活动中,我的父亲在听完我关于种族主义的演讲后,对我愿意公开表达愤怒的情绪感到意外。他为此感到自豪,也乐于见到我以恰当的情绪提出这些问题,但他同时也在思考,作为一名棕色人种移民,几十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他人面前显露怒意。他的愤怒很容易被解读为对他人安全的潜在威胁(这种解读甚至可能实实在在地危及他自身的安全),因此他禁止自己对任何事表达愤怒。别人插队时,他忍气吞声;听到种族主义言论时,他压下怒火;别人对他无礼时,他表现得过分礼貌。而我,由于肤色较浅,常被误认作白人,因此在表达愤怒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愤怒的女性同样不受社会欢迎,但我的愤怒更可能招致嘲笑或蔑视,而非恐惧。
在过去二十年中,穆斯林(或是那些被误认为是穆斯林的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种族主义冲击。西方媒体和政客利用“9·11恐怖袭击事件”煽动恐惧与仇恨,以此牟利。身着伊斯兰服饰的人在街头遭受唾骂,清真寺遭到袭击,那些被视作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人所生的婴儿,其出生体重也有所下降,因为伊斯兰恐惧症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已经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损害。 35 (尽管大多数穆斯林并非阿拉伯人,许多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但西方人仍将二者混为一谈。)
然而,穆斯林男性和穆斯林女性经历种族主义的方式却有所不同,被区分为“他”和“她”两种版本,各有其独特的险恶之处。 36 穆斯林男性常与暴力、教条主义和愤怒联系在一起,而穆斯林女性则被描绘成被动、顺从且被丈夫和父亲洗脑的形象。这些刻板印象催生了性别化的种族主义形式。穆斯林男性更有可能在街头和机场因种族歧视遭受盘查,甚至可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而女性则更有可能因着装受到那些声称为她们最大利益着想的人的指摘,或是被系统性地低估专业能力。
在探讨性别歧视与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交融时,我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不可加性现象。当米歇尔·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时,她所面临的一连串谩骂并非仅仅是她两个最显著身份所带来的压迫的简单叠加,即不仅仅是希拉里·克林顿所面临的性别歧视与巴拉克·奥巴马所面临的种族主义的叠加(尽管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够受的了)。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黑人女性的、独特而疯狂的仇恨,学者莫亚·贝利称其为“厌黑女症”(misogynoir),即针对黑人女性的厌女症。 37 虽然白人女性也会因其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和举止而遭受不公正的批评,但米歇尔·奥巴马所遭受的性别歧视与反黑人种族主义的混合攻击更要恶毒千百倍。人们对她厌恶至极,将她比作动物,恶意篡改她的照片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仿佛她仅仅因为身处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位置就显得荒谬至极,理应遭受持续猛烈的谩骂。此外,由于她在芝加哥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长大,对她的谩骂中还夹杂着与厌黑女症紧密相连的阶级主义因素。电台主持人塔米·布鲁斯曾放言:“这就是他娶的女人……你知道我们得到了什么吗?我们白宫里进了垃圾。” 38
考虑不可加性就意味着我们认识到,黑人女性面对的困扰并不是白人女性面临的性别歧视与黑人男性面临的种族主义的简单相加。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歧视视作“正常”或标准的性别歧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根据其他女性的情况稍作调整,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等于认为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是“正常”或标准的女性。
利益冲突
1985年,艾丽斯·沃克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紫色》被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改编成好莱坞电影。这部电影与小说一样,聚焦了黑人社区内部的家庭暴力问题。影片主人公西莉是一位饱受父亲与丈夫摧残的黑人女性,最终,她在与其他女性的深厚情谊中寻得了慰藉与力量。尽管电影有其不足之处,但因其无畏地展现了西莉的抗争与胜利之路而广受好评。 39 然而,它也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有人在部分影院外举行抗议。示威者主要是黑人男性,他们对电影将黑人男性刻画为暴力和野蛮的形象表示强烈不满。许多黑人女性则反驳道,如果不通过改编黑人女性的文学作品来揭露真相,那么她们所遭受的来自男性的暴力和野蛮行径又该如何向世人揭露?影片上映后,《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在电话公司任职的黑人女性埃尔蒂斯·托马斯。她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母亲和姨妈们被丈夫施暴的经历,并坦言影片对这一问题的正视让她“如释重负”。她最后说道:“黑人女性不应成为维护黑人男性自尊的牺牲品。这部电影应该被更多人看到。”而饰演西莉暴力丈夫的黑人演员丹尼·格洛弗也坦言:“我们常常以维护黑人历史和黑人男性尊严为借口,来回避和掩盖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 40
刻画黑人男性异常暴力的形象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新闻媒体、电影和电视所广泛鼓吹的种族主义观念,即黑人男性是怪物、低人一等、无法自控,因而需要受到监督者、警察和狱警等的监管与约束。这种刻板印象往往为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提供了所谓“正当”的理由。然而,《紫色》从未将黑人男性刻画为天生的暴力狂,而是直面了一个事实,即黑人男性之所以表现出暴力倾向,并非因为他们的种族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性别身份。如果我们为了避免加深对黑人男性的种族主义泛化而禁止讨论或展现这种暴力,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以黑人女性和儿童为代价来保护黑人男性,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抹去了他们遭受的暴力经历,也摧毁了他们寻求帮助的努力。(在此,我主要关注黑人女性和儿童,因为当黑人男性伤害非黑人,尤其是白人时,人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描绘成施暴者,将受害者视作值得同情和保护的对象,而黑人女性和儿童得不到同等待遇。)
然而,如果不是黑人男性的形象从一开始就被严重歪曲,就根本不会出现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避免以进一步非人化黑人男性的方式来描绘他们;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黑人女性遭受黑人男性暴力侵害的事实。为了防止针对黑人男性的种族主义偏见进一步恶化,黑人女性正成为性别暴力的牺牲品。正如金伯利·克伦肖所言:
当然,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虚构作品中对黑人暴力的描绘,往往都被嵌入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中,这个框架一直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作为病态和暴力的代名词。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暴力本身的描绘,而在于缺乏其他更全面地展现黑人经历的叙事和形象。 41
在现实中,这里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利益冲突。我们既不应该将黑人男性描绘为异常暴力的人,也不应该阻止黑人女性公开谈论她们所遭受的暴力。这种冲突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产物,因为缺乏正面或中立的表述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伤害事件,最终导致了这种难以弥合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