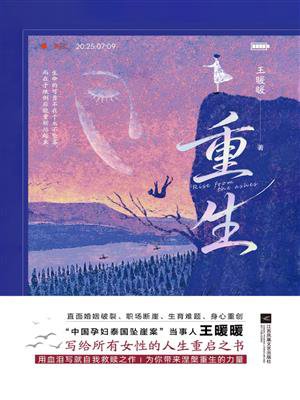4
我如他所愿,扮演着一个市井小女人的角色。我用眼神和手指传达着俞晓冬希望看到的情绪——嫉妒。只有让他确信我正嫉妒着他们母子畸形的亲密,他才会放松警惕。
这种畸形关系,早在一次旅行时就初现端倪。记得第一次带陆慧芳出游,我们特意为她单独开了房间,谁知她执意要和儿子同住。此后每次旅行,这都成为我们争吵的导火索。直到有一天,俞晓冬干脆订了三人亲子房。看着他们母子理所当然地同睡一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嫁了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
我用唯一能动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妈宝男俞晓冬,他嘴角扬起满意的弧度,继续给陆慧芳喂燕窝,而陆慧芳则继续喂他吃牛肉。吧唧声、吸溜声此起彼伏,令人生厌。
我只能忍着,因为时候未到,我还不能刺激他,我要继续等待。
等到时间已过午夜,外面的大风也已经消隐了,这个时候,正是俞晓冬心理防线最薄弱的时刻。
“现在也没有外人,”我突然开口,声音划破病房的寂静,“我们聊聊这个事吧,你为什么把我推下去,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
俞晓冬略显迟疑,不接话,沉默着。
武元平时就是个老实人,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表演,就是假装镇定,他装作不知情地看着我们。
可无论我怎么问,俞晓冬就是不说话,保持着高度警惕的状态。见状,我决定不再讲了,越讲他警惕性越高。
然而,这个时候,万万没想到,神助攻出现了。
陆慧芳听到我不断向俞晓冬问话,但是她儿子又保持沉默,她也想知道怎么了。于是,她开始问:“儿子,她刚才一直在那儿说你推她,说不是意外啊,问你打算以后怎么办,说家里人早晚要知道的,她到底在说什么?”
俞晓冬继续选择沉默。陆慧芳发扬了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追着问:“说啊,你说说啊!”
我没想到还有这个转机,立刻跟在后面蹚浑水:“对呀,你要告诉妈妈呀,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我们没有理由欺骗妈妈。”
果然,俞晓冬开始动摇了。他可以跟我已读不回,但是妈妈问的问题,不能不答,如果不回答的话,就是不尊重他的妈妈。他看着陆慧芳,奇迹般地开口了,上来开门见山就是一句:“是的。”
我一听就急了,就算录到音,录到的只是“是的”两个字,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根本无法成为证据。
于是,我继续引导:“是什么啊?妈妈年纪那么大了,你一句‘是的’,她知道什么啊?是你把我推下去的,是你处心积虑要杀我,你一定是有你的想法的。我觉得趁妈妈在,我们把这个心结聊开,我也答应你不跟警察说出真相,我也答应你以后回去要钱,我就给你钱。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把话讲得不清不楚,我觉得你是不尊重这个事情,不尊重我,也不尊重妈妈,你也不想以后跟我把日子过好。”
我故意刺激他的神经。
武元在旁边一言不发,大气都不敢喘,就好像隐形了一样。
我发动我全部的脑细胞和毕生所学去插话,我希望他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果我录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他亲口承认他推我,并且说出他推我的原因,那么录音就可以交给警方作为呈堂证供。
在陆慧芳的追问和我的插话下,俞晓冬可能一时之间心智乱了分寸,也可能放松了警惕,他终于开口回答陆慧芳的问题。他俩相对而坐,陆慧芳直直地盯着他,那架势好像让他无处可躲。这个妈宝男最见不得母亲担心,既然妈妈想知道真相,他就不得不说。
他完全没意识到,在他回答母亲的同时,我们都在听着——而武元正在录音。要是俞晓冬知道武元在录音,就算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绝不会吐露半个字。
然而,我们还是低估了俞晓冬的警惕心。他跟陆慧芳说话时,故意用普通话夹杂着大量江阴方言——那是我和武元完全听不懂的家乡话。
这江阴方言就跟天书似的。我和他在一起的二十三个月里,一句都没听懂过。现在只能干看着他们母子俩叽里咕噜说个没完。说到后来,陆慧芳开始用余光扫我。我猜他们八成是在说把我推下悬崖的前后经过,但陆慧芳的神情很平静,没有任何责怪俞晓冬的意思。
俞晓冬话音一落,我继续插话:“现在妈妈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了。你需要认认真真地发一个誓,做出保证。只有这样,我才能相信你。我的诺言是我不报警,我不揭发你,然后跟你回中国好好过日子;你的诺言就是以后不会再伤害我,并且全心全意对我和孩子好。我们要各自为自己的诺言负责。”
我躺在床上说,武元坐在我的身边;俞晓冬和陆慧芳坐在床尾那边,一个不动声色,一个满脸忧愁。
我继续说:“我先带个头,虽然俞晓冬把我推下悬崖了,做了种种伤害我的事情,我非常生气,但是鉴于他跟我诚心地悔过,我决定不去检举他、揭发他,我会按照他的意思去跟警方说,我是自己头晕掉下悬崖的。请大家放心,我在这里的治疗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回到中国,我们会好好地过日子,我们会相亲相爱,不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我发完誓了。”
我盯着俞晓冬,说:“你的誓言,该你讲了。”
俞晓冬眯着眼睛,缓缓转过头,盯着武元,看了足有半分钟。武元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能看到他左手手背上的青筋在轻轻地有节奏地跳动,仿佛在发电报,我甚至能模糊地听见空气中陡然响起了电波声,嘀嘀,嘀嘀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