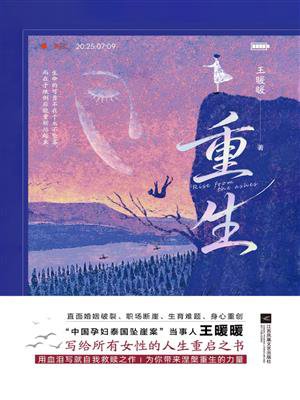6
后来,病房再次陷入了沉寂。俞晓冬不愿再多说什么,我也不敢再问什么。沉寂是让人可怕的状态,因为沉寂有双面,一面是静默的,而另一面可能蛰伏着爆发。除了沉寂,病房里还有恐惧,我恐惧录音被俞晓冬识破,而武元则直接成为恐惧的化身。
武元听完俞晓冬的大量陈述以后,觉得他丧心病狂,无可救药,并且他坚信俞晓冬后腰上卡的东西是枪。武元坐在椅子上,陷入高度的紧张,他也不玩手机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们三个人身上,特别是俞晓冬。俞晓冬只要动一下,武元都会本能地挪动一下凳子,或者是下意识地站起来,朝远离俞晓冬的方向挪两步。
恐惧还具有传染性,武元的肢体语言已将恐惧表现得极为明显,达到了几乎无法掩饰的地步。倘若他的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以俞晓冬敏锐的观察力,识破真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旦被俞晓冬看破,武元极有可能在压力下被迫承认录音的事情。而一旦录音被删除或被收回,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我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获取这份关键证据了。
时间开始过得缓慢,漫长的一秒过后是下一个漫长的一秒,我觉得空气都凝固了。我不敢看俞晓冬,只是偶尔用左眼的余光朝他的方向扫一下,他稳稳坐在床尾的椅子上,看样子没有离开的打算。因为之前的几天,他从来没有离开过ICU VIP,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曾离开。按照之前的规律,今夜他还会在这里过夜,所以我觉得我被推进了一个死局,而我已无力破局。
病房里的四个人陷入了长久的僵持,而俞晓冬快速从这种氛围里觉察到了某种危险。他揣起手机,把所有注意力都汇集到了我的身上,偶尔他也会突然转过头看向武元和病房外来来回回的人流。
被俞晓冬突然盯着,武元更加紧张了,他赶紧移开眼神,身体朝床头挪了挪。俞晓冬突然起身,把手伸向后腰,武元也站了起来。我闭上眼睛,把命运交给了黑暗,我想武元可能露馅了吧。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来了,陆慧芳拿着手机走到门外接电话,而俞晓冬转身走到病房门口,听陆慧芳打电话。我松了一口气,用眼神暗示武元坐下来。武元颤抖地点点头,缓缓坐在椅子上。
陆慧芳接完电话走回病房,仍然远在天边,有时候跟俞晓冬聊聊天,打打岔,有时候看看手机,回回消息。
俞晓冬继续观察武元,时不时跟武元叙旧唠家常,甚至问武元手机里有没有他们以前的合影。提到手机,武元抖得更厉害了,我心想恐怕不用到天亮,武元就会暴露。
漫长到令人窒息的对峙,我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生怕录音的事露馅。也不知到底熬了多久,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陆慧芳熬不住了,她说:“太晚了,我想休息了。”说完,她又心疼儿子已经熬了好几个通宵,害怕他把身体熬坏了,于是她建议他们一起在附近找个酒店开个房间。
俞晓冬当然没同意,他跟陆慧芳说:“我不去外面住酒店,我就在这里陪着暖暖。”陆慧芳也没说什么,又坐下了。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陆慧芳又开口了,这回她强烈要求去开房睡觉。她说,人不睡觉是不行的,身体是会熬坏的。最后,陆慧芳拍了板,她让俞晓冬去外面开一个房间睡觉,她留下守着我。
出于对陆慧芳身体的考虑,俞晓冬第二次表示拒绝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陆慧芳先留守ICU,他和武元出去开两间房,先把武元安顿下来。然后,他和武元回到医院,他留守ICU,武元带着陆慧芳去宾馆休息。
俞晓冬的计划相当谨慎,相当于无缝衔接,既出去开了房让陆慧芳得到休息,又使得我和武元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在长达近四个小时的僵持过程中,他应该已经觉察到有一点点不对劲了,可他没有证据,但是他不可能再给我和武元单独相处的机会,所以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两全之策。
我能说什么呢?稍不小心,不但会葬送我和孩子的性命,也会将武元推下深渊。然而,他的完美对策,却遭到了陆慧芳和武元强烈的反对。陆慧芳太心疼儿子,儿子在ICU连续“看护我”好几天了,她怕儿子身体垮掉。武元也是一万个不愿意,他不能跟俞晓冬单独出去,因为他太害怕俞晓冬了,他对俞晓冬的恐惧已经到达了顶峰状态。万一在开房路上露馅,俞晓冬把他做了呢?于是他说他晚上一般睡得很晚,他可以在这里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关键是陪陪暖暖,毕竟他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了。
尽管遭遇双重反对,俞晓冬却没有放弃,他一直劝说武元跟他去开房,但武元的态度异常坚决,甚至搬出了一个不可拒绝的理由。他来泰国是来看我的,看到我变成这个样子,作为朋友,他哪还有心情去睡觉呢?
俞晓冬一听,使劲皱了皱眉头,一副纠结的样子。迫于无奈,他在陆慧芳的催促下,只好同意让武元留在病房,他带着陆慧芳去酒店安顿。
陆慧芳和俞晓冬走后,我没有让武元去做什么,可他跟了出去。也许有了上次的经验,他跟在陆慧芳和俞晓冬身后走到医院大门外,确定他们离开后,他又在ICU门口待了将近两分钟,确认他们真的走了,才回到我的病房。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又把双肩背包卸下来,双手抱在胸前,仿佛抱着一个小孩一样。我知道他一直在克制他的恐惧。
我迫不及待地跟武元确认录音的事情。我问他:“我都没有看到你弄手机,你录到了没有?”
武元掏出手机,解锁屏幕:“录到了,你放心。”
武元播放录音时,他的手还在抖,以至于我听到的录音也是发抖的。武元说他自己挺㞞的,居然害怕得要死,说话时舌头都打结了。
我说:“你一点都不㞞,你比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要伟大。”
我告诉武元先把录音上传到云端,备份保存证据,即使中途被识破,手机被抢夺,但至少证据被保存了下来。继而我又嘱咐他:“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把江阴话翻译成普通话,把普通话翻译成英文,再把英文翻译成泰文,然后把录音证据交给警察。”
俞晓冬把陆慧芳安顿好,很快就回来了,房间里的气氛瞬间进入了高度紧张和戒备的状态。他和武元又开始熬鹰了,你不睡我也不睡,你不吃我也不吃,你不动我也不动,你看着我,我也要看着你。
武元靠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抱紧双臂;俞晓冬坐在椅子上,靠在靠墙的那边,盯着武元研究起来;我躺在病床上,心里不停地打着鼓点子,千万别出事,还有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录音千万不要被夺走。我怕俞晓冬从武元身上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事情一旦败露,俞晓冬随时可能动手。
俞晓冬研究了一会儿,试图打破僵局,他叫武元:“我们一块儿去上个厕所吧?”
武元摇摇头:“你自己去吧,我要上厕所我自己去,我认识路。”
俞晓冬回来后,武元找把椅子靠在上面,闭上了眼睛。我睡在中间的病床上,右边靠窗的椅子上坐着俞晓冬。夜深了,救护车的警报灯光时不时反射进来,打在武元脸上,他的脸忽明忽暗。我知道他没有睡着,因为一床之隔坐着一个杀人凶手。武元的眼睛时不时睁开又闭上,有时他坐起来看一会儿手机。俞晓冬突然起身,武元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下意识地挪动着凳子。
他怕俞晓冬,他是真怕俞晓冬。
俞晓冬则比较放松,因为我们刚刚互换了誓言,意味着我不会再去揭发他,他终于可以打个盹了。
我也眯瞪了一会儿,我仿佛看见武元变成了一只信鸽,他飞出医院的窗口,一直朝北飞,最后飞进了警察局。
武元在乌汶府医院只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如果可以用爆炸来形容恐惧,那么对武元来说,这个晚上的恐惧相当于恒星坍塌,在强大的引力下,他的灵魂被迫向内坍塌,慢慢被压缩成一个小球,随时可能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