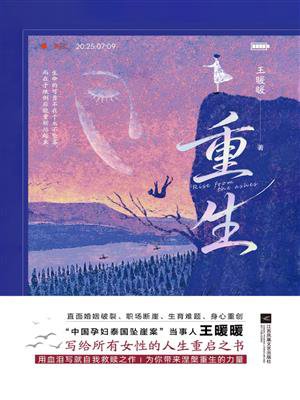1
我把关键的录音证据飞鸽传书出去了,但是并没有人来找我。
在战场上,第一发子弹射出去,对面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大概率是因为子弹没有打到敌人身上。我等啊等,住院后的第五天上午,终于把警察等来了。
两个警察来到我的病房,一个坐在床头,另一个站在床尾。坐在床头的警察体态发福,留着八字胡,他的语气十分官方,非常人道,提的问题也异常简洁,大部分时候我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也可以点头或摇头。
俞晓冬起初站在床尾,随后慢慢踱到床头,目光紧锁在我唯一能活动的左眼上。在他的监视下,我连眼球都不敢轻易转动。
虽然身体不能动,但直觉告诉我,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录音证据。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从我心底升起,就连平日里不喜欢男人留的八字胡,此刻都显得英勇神武。似乎他随时都能站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样,从腰间拔出手枪瞬间制伏俞晓冬。
不同的心境塑造不同的情绪,在与八字胡警察的一问一答中,我尽可能表现得春风细雨,甚至比八字胡警察还要官方。
按照泰国警方的办案流程,他们既然已经拿到录音证据,那么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想办法引开俞晓冬,好单独给我做笔录。我努力配合着八字胡警察,同时也用那只不敢乱转的眼睛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我想从他的每一个动作里读出暗示——比如暗示我支开俞晓冬或暗示我昏迷过去。可直到我把眼睛都看酸了,看得流泪了,也没有收到任何暗示。
我想,泰国警方可能还有别的招数吧。毕竟我不是警察,也不通晓他们所有的办案流程。
这时俞晓冬突然凑过来,俯身帮我擦掉眼泪,这哪里是好心,这分明是一种警告!
奇怪的是,这次即便被他威胁,而且还是当着警察的面威胁,我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注意到那个瘦高警察正抱着胳膊站在床尾,饶有兴趣地盯着俞晓冬,像研究犯人似的。
我想,泰国警察的办案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八字胡警察负责给我做笔录,吸引俞晓冬的注意力,而高个子警察在一旁观察,用他数码相机般的眼睛记录俞晓冬的一举一动。想到这里,我的情绪随之高涨起来,就像脚下的冲浪板随着巨浪迅速攀升至浪尖。
“这么说,你是自己掉下悬崖的?”八字胡警察问。
我的眼珠转了转,看了一眼八字胡警察,目光又在高个子警察身上流连了好久。但高个子警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居然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摇曳的椰子树走了神。我的眼珠不得不转向俞晓冬,他满脸堆笑,我看见了这副假面背后的无垠黑洞。
他的眼神仿佛一把狙击枪死死锁定了我,看架势要是我说错一句话,他分分钟就能扣动扳机爆了我的头。
我不得不按照俞晓冬的话跟警察说,我是头晕不小心掉下悬崖的。俞晓冬握着我的右手,右手食指在印泥盒子里滚了一圈,红指印又按在笔录本上。这一刻,我依旧认为我成功地完成了我的计划,是的,警察完成了初步的试探。
两个警察走后,俞晓冬长舒了一口气。不知为何,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空空荡荡的,就像小时候开完运动会人群散去的那种空荡,仿佛有个巨大的耳环在耳边晃动。窗外又起了风,走廊传来脚步声——有护士的,有病人的,就是没有警察的。看来,没人留下来监视我们。
我开始怀疑伟大的朋友武元先生了。我并不是怀疑他的能力,只是担心他没能把录音证据送到关键的人手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不是在泰国递交的录音,而是安全地飞到国内才向乌汶警方提交证据。泰国不是中国,司法程序的迥异暂且不论,关键的是录音里我们说的都是汉语,甚至还有方言,他们需要翻译,翻译过程中难免产生误读,到最后只能用时间来纠正语言的差异和错误。
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我在和时间赛跑。
看来第一计划已经失败了,我告诉自己,必须寻求第二计划。我的脑子开始飞转,第二计划怎样实施较好呢?首先,我必须找到一个会说泰语的人,然后让他帮我把消息传递出去,但是这个人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