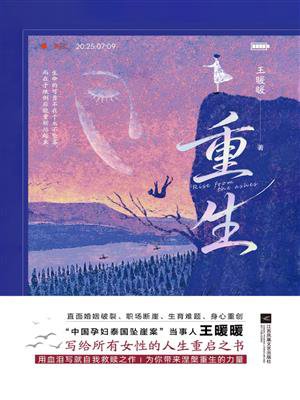2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最美的幻境中不能自拔,我幻想有一个人踏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把我带出医院。
最终,我的目光锁定在白大褂身上。他是我的主治医生,长得像泰剧里面的男主角,他每天下午两点左右都会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ICU看我一眼。他会问我:“哪里疼?哪里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例行检查,像我这种几年不遇的危险病人,是他时刻关注的对象。
他每次进来时,我都在俞晓冬的看护和监视中,我们讲的都是非常官方的话。我告诉他,我疼,疼得受不了,能不能给我再来一点那个镇痛,或者类似的什么。我一天要打四五支粗的止痛药,都是他特批的,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并不是说我申请止痛药,他便批给我,他需要观察我的情况,推断我的疼痛,以此确定是否特批。
在他面前,撒娇耍赖都是没有用的,他有自己的标准。
我之所以想要接触白大褂,是因为俞晓冬身上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武元离开泰国,俞晓冬放松了一层警惕;其次,陆慧芳留了下来,一个他信任的人在身边,他又放松了一层警惕;再次,昨天我们互相交换了誓言,他再次放松了警惕;最后,今天上午,八字胡警察找我录笔录,我也没有揭发他。几重安心的加持之下,俞晓冬不再把所有精力放在我身上,他开始翻弄我的手机。我猜他应该是在查找我的财产。有时,他还会给他的狱友和马仔发一些语音,大概意思是让他们火速赶到乌汶。
下午一点多,陆慧芳着急忙慌地闯进ICU。她说她住的酒店隔音不好,想重新换一个酒店。一般的酒店都是下午两点钟退房,为了省点钱,她想在两点前把酒店退掉。俞晓冬害怕陆慧芳因为钱着急上火,毕竟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跟我们不同。于是他跟我说:“我要去帮我妈退酒店,得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俞晓冬前脚刚走,白大褂后脚就进来了。他见ICU只剩我一人,例行公事地问我:“感觉怎么样?伤口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什么异样,都可以跟我反馈。”
我内心正进行天人交战。从白大褂进来那刻起,我脑子里就炸开了锅——说还是不说?万一那对母子突然折返拿东西,听见我在告密,我和白大褂都得完蛋。这次说?下次说?还是永远憋着?不同的声音在脑袋里吵得不可开交。
白大褂例行检查结束,起身要走。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讲,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于是,我一把拉住他的白色长褂。
他转过身,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他疑惑地看着我。
我抓紧时间说:“其实我不是自己掉下悬崖的,这个事情背后是有……有人做的……”
白大褂坐下来,悄声用英语问我:“Tell me,who is it?(告诉我,是谁?)”
“我不敢说是谁,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情不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样子,不是我自己掉下去的,是有人做的。”我不敢直接说答案,但我可以透露关键信息。
白大褂追问:“到底是谁?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
我摇摇头说:“我不敢说。”
白大褂问:“既然说了,为什么把话说一半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白大褂是什么性格的人。他是率真的人,还是机智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率真的人,当他知道凶手是俞晓冬,他可能直接去质问或者去对质,到时我连被救的机会都没有。
一瞬间,我思绪纷飞,却沉默不语。
白大褂继续问我,问了大概十来次,到底是谁?我还是没有说。白大褂点点头,没有再问。
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你好好休息。”然后他就走了。
白大褂走后,我有些后悔,我有些拿不准他的性子。作为我的主治医生,我是该相信他的,因为他把我全身碎掉的骨头重新拼到了一起。而且,入院第二天,俞晓冬要把我强行带出医院时,他带着医生死死把着病床。
他说:“你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不允许你去送死。”
面对生命,他是有人道精神的;可面对一个杀人犯,他还能保持外科医生的冷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