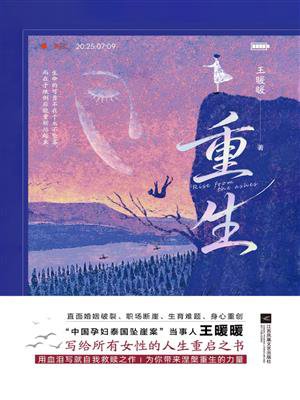1
我吃力地睁开眼,耳朵贴在地上,隐约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难道是一条蛇正扭动长长的身体向我逼近?
内心的恐惧让我的每根神经都绷得很紧,连风声在我听来都像是在呜咽。
渐渐地,我能感觉到地面传来一阵共振的频率,我不确定那是从哪里传来的。有一刹那,我甚至怀疑那种共振是不是幻觉,可是,如果是幻觉,它会在一个频率上,但它的频率是渐进的。是的,幻觉是不会有渐进的,可它越来越近,由远及近,我停止所有的思考,屏住呼吸,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着那共振的频率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
不知过了多久,我眼前居然出现了人影!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正朝我走来,我这才知道,原来刚才地面的共振是他们的脚步发出来的。他们穿着帆布鞋,帆布鞋走路很轻,我听不到那种“嗒嗒嗒”的声音,但我能感觉到脚步和地面接触发出的共振。
看见他们,我仿佛看见了救星,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点。
最前面的“迷彩服”扑了过来,一下子扑倒在我的面前,用泰语问我:“怎么了,怎么了?”
血在我嘴里弥漫,蔓延进我的气管,我说不出话,叫不出声。
“迷彩服”看出我是中国人,他想了想,嘴角努了努,然后握住我的手,用英语跟我反复地说:“You are safe(你安全了)!You are safe(你安全了)……”
他一直说着“You are safe”,试图安慰我,我的恐惧感渐渐消失。另外几个“迷彩服”也围过来,查看我的情况。
我知道,我得救了。比得救更让我开心的是,我知道这不是幻觉。刚才我在用耳朵听,听那些微小的声响;此刻我在用眼睛看,看到他们弄出巨大的动静,他们从包里掏出各种救援装备,他们在组装担架,他们在打电话联系救护车。
从绝望地躺在崖底,再到被好几个人围着,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我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我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的心里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我希望他们赶紧把我捞上去,把我送进医院。然而,疼痛的知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蚀骨的疼痛从身体的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连睁眼睛都是痛的。他们想把我抬上担架,有人抬我的胳膊,有人抬我的腿,但无论是胳膊还是腿,他们根本抬不起来,因为我浑身上下的骨头都断了,就像一摊烂泥。
他们好不容易把我弄上担架,我左边站着三个人,右边站着三个人,六个人一起抬着我走在山路上。山路不是很好走,蜿蜒曲折,我的身体跟着担架颠上颠下,浑身仿佛散了架一样,那种疼,真是一分一秒都难以承受。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人的神经麻痹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在崖底躺了四五十分钟,救援队找到我又花了四五十分钟,差不多两个小时,刚好过了那个临界点,我的痛觉神经彻底苏醒。
断掉的骨头就像一把把尖刀,把我的身体扎出了无数个窟窿,血液流出来,最后形成了无数个伤口。本来已经凝固的伤口,随着颠簸开始崩裂,像一座座活火山在我身上复活,岩浆般的血开始涌出,撕心裂肺地疼。
终于挨过了山路十八弯,我被抬上了救护车。六个救援者长吐了一口气,他们跟随车护士交代了几句我的大概情况,便转身消失在山林中。他们来过,也好像没来过。他们仿佛鸟鸣,藏在光里,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光。
救护车鸣着笛在山路上行驶。泰国边境的这条路,很像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土路,路面铺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子,坑坑洼洼的。汽车轮胎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不断颠簸,我的身体也随着上下颠簸。轮胎每转动一圈,我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口便仿佛同时被撕扯,疼痛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剧烈。那种痛楚钻心刺骨,简直难以忍受,就像是全身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里都在集体发作结石般的痛。因为疼痛,我一直在掉眼泪,泪水混合着血水,导致我的世界变成了红色。
红色的护士,红色的“白”大褂,红色的救护车后门紧紧关闭,红色的针头,还有一双时隐时现的红眼珠。我不敢细看那双眼,生怕是俞晓冬躲在后面盯着我。
救护车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感觉漫长得像过了四年。好不容易熬到最近的救护站,结果救护站的大夫却摆摆手说:“治不了,伤情太重了,必须转到大医院。”
他们把我抬进去,没有做任何救助和治疗,连片止痛药都没给,又把我原样抬出来塞回救护车。我心里在喊,救命啊!我不想转院,因为不知道从救护站到最近的医院,还要再开多久。我受不了在路上颠簸时伤口撕裂般的疼痛。那种疼痛就像在凌迟一般,堪比古代十大酷刑,对我而言实在太残忍了!
救护车上的护士一路照顾我,她长得干瘦干瘦的,手指细如竹节,她简单地将我有伤口的地方贴一块纱布,却没有包扎,我明白这是常规流程,主要是怕伤口暴露引发感染。
我右眼的上眼皮没了,是被树枝和地面刮掉的,眼睛下面的肉也被刮掉了,要是再刮掉一些,眼球也就没了。女护士用一块很大的纱布才能把我的右眼盖住,我的面前随即黑了一大半。我全身上下,能用夹板固定的地方都用夹板简单固定住了。我只有左眼能动,更确切地说,是眼皮能闭合,眼珠能转动,但几乎无法表达任何情绪和想法。
救护车顶的架子上挂着四爪钩,其中一个钩子上吊着只老式的盐水瓶,应该是给需要输液的人准备的。盐水瓶随着救护车的颠簸而晃动,挂盐水瓶的钩子显然有些老旧了,该是钩子的地方磨秃了,几乎是平整的,我感觉那盐水瓶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好巧不巧,那盐水瓶正对着我的肚子,它晃得我心惊肉跳,我生怕它掉下来砸到我的肚子,砸到我的宝宝……
坠崖时,我的身体数次接触崖壁,撞到树枝,又从崖壁上滚过。坠落过程中,经过磕碰,我的嘴巴经过数次无意识的咬合,嘴唇、舌头和两腮都已经烂掉了,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刚掉下崖底时,出于本能,我喊了几句“help me”。可后来,我的嗓子里卡着血,血又无法处理,我感到口腔、嗓子、气管和食道里都灌满了血。痛感神经恢复后,我再也无法发出声音,完全无法讲话。我只能听,不能动,我只能用眼神疯狂暗示护士把盐水瓶挪开。
女护士以为我尚未度过恐惧期,她不停地用泰语重复讲着:“你不要害怕,你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真实的情绪是恐惧,但此时的恐惧不是她理解的那样,我怕盐水瓶掉下来砸到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活下来,我们可不想死在一只瓶子手上。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过日子,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难题”二字,因为我相信,一切问题都将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下得到完美解决。哪怕俞晓冬把我推下悬崖之前,我最后的想法仍是可以谈,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完美解决,上到几亿泰铢的进出口贸易大单,下到买菜时跟卖菜阿姨因为块八角进行的拉锯战。可我现在说不出话,浑身上下能动的只有左眼珠。
我用唯一可以动的左眼珠,不停地瞪着护士,以此寻求跟护士的眼神交集。只要护士看我,我们的眼神对上了,我立马将眼神瞟向上面的盐水瓶,希望借此把她的注意力也带上去。我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个动作,看护士看盐水瓶,再看护士再看盐水瓶,几近疯狂,可女护士始终没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救护车在颠簸,瓶子在晃动,我只好直勾勾地盯着瓶子,使出最后的力气不停地用目光表达:嗯,嗯嗯,嗯嗯嗯。最终,护士顺着我的目光,抬头看了一下,就在瓶子沿着平整的钩子滑下时,她用竹节般的手摘下了它。
我总算松了口气,在颠簸晃动的视线里,我看见她给了我一个充满歉意的微笑。
大约一小时后,我被送进乌汶府最大的医院。躺在人流穿梭的门诊大厅里,我的气息微弱至极,一直在叠加的疼痛击溃了我,疼到绝望,疼到无法忍受。我努力向抢救人员表达着想要安乐死的诉求,可无论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僵持了几分钟,抢救人员才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他们答应,我会毫不犹豫地签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那种百爪挠心、蚀骨钻心般的疼痛,我是多一秒都不能忍受了,给我注射一针安乐死药剂,好让我停止这种疼痛和折磨。
但他们不同意,所有抢救人员都不同意,其中一个护士表现得相当决绝,从她的身体语言来看,她是能理解我的疼痛的。她怜悯地看着我的肚子,刹那间有一些走神,想来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