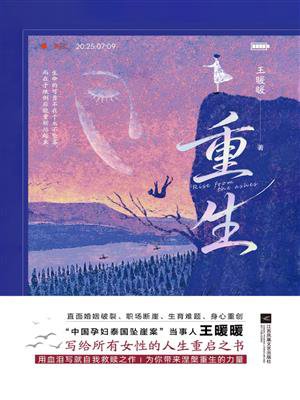2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俞晓冬。
他一路尾随我来到了这里,警察看他鬼鬼祟祟的,上前盘问。起初他还装作看热闹的路人,当警察发现他不会泰语,要查看他的护照时,不得已,他只好承认是我丈夫。他是被工作人员从门外喊进来的,对方示意他进来安抚我的情绪。他被喊进来以后,站在离我床位四五米远的地方看着我,迟迟不敢走近我,停顿了大概半分钟。我们互相盯着对方,彼此脸上都写满了错愕与震惊。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突然,他提高嗓门,夸张地喊道:“老婆你去哪里了?我找你也找不到,我急死了。”
我瞬间怒火中烧,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嘶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经过一路颠簸,喉咙里淤积的血终于咽下,我又能出声了。
俞晓冬听到我的反驳,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交织着震惊、恐惧与错愕。他瞪大眼睛,活像见了鬼——显然,他没料到我能开口说话。其实他刚刚那句“老婆你去哪里了”的关切,不过是演给旁人看的戏码,他根本没指望得到我的回应。
按常理,一个人从34米高的悬崖坠落,不是粉身碎骨就是重度昏迷,或者是摔到头变成植物人。他只知道我还有生命体征,却不清楚具体状况。他这番试探本是为探虚实,却没想到我不仅口齿清晰、思维敏捷,最关键的是,我还能在第一时间回复他,甚至指认他。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判,因此他备感震惊,那张虚伪的面具瞬间裂开了一道缝隙。
不过,他反应极快,迅速调整好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的床边,蹲下身凑近我的耳边,低声跟我说:“你闭嘴!不要乱叫,这里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刚才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也没有监控,如果你继续大喊大叫,等会儿我看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弄死你!”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像毒蛇般渗着刺骨的寒意。他此刻的语气在我听来,和在悬崖边推我下去前的那句“你去死吧!”如出一辙——这是他给我下的第二张死亡通知书。但奇怪的是,当死亡再次被赤裸裸地摆在面前时,我浑身的血液反而沸腾起来。就像在悬崖半空努力伸手想要抓住什么救命那样,那种灼烧般的求生欲又回来了。
你叫我死,我还偏就不想死了!我死死咬住牙关,不是屈从于他的威胁,而是在蓄积反击的力量。
随后,我被紧急送往手术室。医生取来一把巨大的医用剪刀——我身上的灰绿色T恤和牛仔背带裤早已被鲜血浸透,紧紧黏在皮肤上。剪刀的寒光闪过,布料被一片片剪开,像剥落一层血痂般从我身上剥离。
麻醉医生给我注射了麻醉药,我的意识渐渐涣散。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醒来,也不知道醒来后我的孩子是否还活着,在昏睡过去前,我拼命在心底祈祷:活下来,我们一定都要活下来。
我被麻醉时,俞晓冬也在给媒体和泰国警方打“麻醉药”,面对警方的询问,他编织着精心设计的谎言——
“我们原本是去看日出的,中途我去服务站上厕所,回来就发现她不见了……”
“我打她电话也不接,我以为她已经独自下山,便开车下山寻找……”
“后来我去机场的路上看见一辆救护车和我擦肩而过,听到有游客坠崖,我担心她遇险,立刻折返,想去现场查看。”
“我估计她可能是孕期头晕导致的意外……”
有记者追问,我对他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怎么回事。
俞晓冬解释:“那只是她在埋怨我为什么没陪在她身边。”说完还不忘补充,“可能是现场翻译偏差造成的误解。”
手术后的苏醒像从深海浮出水面。意识先于知觉复苏,睁开眼的瞬间,刺眼的白光中,俞晓冬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他的眼神阴鸷冰冷,与我记忆中那个曾为我做饭的丈夫判若两人。
我下意识地想要动一动,却发现自己一动都不能动,全身都被夹板绑死了。一切如旧,还是只有左眼能动。即便它能动,我也不能让它乱动,因为我担心俞晓冬从我的眼神中读出我的真实情绪。
我如同被封印在石膏中的木乃伊,僵卧在ICU(重症监护室)的VIP病房里。麻药劲还没过,浑身上下一点知觉都没有。我缓缓转动眼球,观察着周围。我发现自己戴着氧气面罩,浑身插满了管子,就跟恐怖电影中的异形似的。余光中,我看见两个女护士坐在床的这一边,她们见我醒了,便围了上来。她们说的是泰语,我只能听出个大概。她们说,手术做了11个小时,而且非常成功,体内的断骨接了一半,气管和脏器内的瘀血也被清除,最重要的一点是,孩子保住了。
我用泰语说了一声“谢谢”。
两个护士把俞晓冬拉到门口,低声说着什么。俞晓冬不停地点头,不停地哈腰。两个护士一前一后走出ICU后,房门缓缓关上。
俞晓冬转过身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击中了我:这是一个单独的病房,病房里没有监控,而俞晓冬可以24小时陪伴我。说是陪伴,其实就是监视,他练过泰拳,又经常健身,健硕的身体可以让他做到不吃不喝不睡。关键是这个ICU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的重症监护室周围全是玻璃,方便医护人员从外面透视观察。可这里的病房上半截是玻璃窗户,下面差不多有一人高,全部都是木头围挡,有很大的视线盲区。
ICU VIP里只剩下我和俞晓冬。他死死地盯着我,突然俯身逼近,我吓得想躲,可根本动弹不了。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特别凶狠,让我想起推我掉下悬崖时的那张脸。
“你记住!”他咬着牙说,“你是自己头晕掉下去的。无论谁问,你都要说,你是自己掉下去的。我跟警方和媒体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敢和我说的不一样,我就弄死你。”
“好……”我艰难地挤出回应,声音细若蚊蚋。这不是屈服,而是重伤之下的权宜之计。
我刚刚做完大手术,精气神受损,身体虚弱不堪,非常乏累,但我不敢真正入睡。我像只惊弓之鸟,只要俞晓冬稍有动静,我立刻绷紧神经。因为我担心他走火入魔,对我下死手。他此刻要杀我易如反掌:一个枕头,或者拔掉氧气管,都能让我悄无声息地“意外死亡”。
而我毫无反抗之力。
我躺在病房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在这极致的被动中,一股前所未有的求生欲却在疯狂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