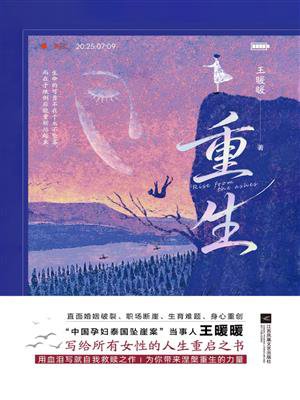3
幽闭狭窄的病房,就像薛定谔眼中的盒子,而我是盒子里的猫。如果薛定谔站在盒子外面观察盒子里的我,在没有打开盒子的情况下,我既是生的也是死的,我处在这种叠加态里,或生或死都在俞晓冬的一念之间。他在病房的透明玻璃前踱步,不停观察走廊的护士和医生,他在经历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他要杀死我,必须在视线盲区内,他赌别人看不见。
赌赢了,他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遗产,过几年挥金如土的好日子;赌输了,他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牢里度过,或者被判死刑。多年的商场经验让我对人性有着清醒的认知,我告诉自己,我能做的就是在他去往赌场的路上,在他孤注一掷的途中,把他拉回来。
首先,我要争取他的信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所谓的信任是求饶。我向他求饶,跟他保证,再三保证:“我不会报警,而且我会原谅你,你想让我跟警察说什么,我就跟警察说什么,你想让我说我是自己掉下去的,我就说我是自己掉下去的。”
其次,在这个要命的时刻,我必须尝试换位思考,是的,该死的换位,我要站在凶手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一个凶手现在想要的应该是行凶后的心理慰藉,他需要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于是,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时冲动,才对我这么做的,毕竟我们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孩子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啊。如果我把你弄进去了,我也没办法跟孩子交代,我说什么,我说孩子啊,你爸是被我亲手送到牢里面的,因为他要杀你的妈妈。”
当然,我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你都要杀我了,都要我的命了,我怎么可能继续跟你做一家人,而且还让你来跟我一起升级做爸爸妈妈呢?你不配!但是,现在我被封闭在薛定谔的盒子里,身不由己,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命,我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对我进行二次谋杀,哪怕保持这种既生又死的状态也好。
俞晓冬见我服了软,只是微微一笑,就转过身走到透明玻璃前,继续观察走廊。他时不时抬腕看表,像特工一样记录着走廊里人流的走向和护士的状态,他应该是在寻找时间的缝隙吧。
时间的缝隙,就是下手的时机。
我一动都不能动,只能默默躺在床上。我在祈祷:老天爷呀,让我动起来吧。
我的眼球扫向右半边身体,微光中飘浮着灰尘,清晰得粒粒可见。我怔住了,因为我看见我的右手食指在床单上有节奏地敲打着,手指敲打床单,激起了灰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要多恢复几根手指,可任凭我怎么努力,还是只有食指能动。
一只眼睛,一根手指,这是此刻的我能拿上台面的所有筹码。
有那么一瞬,我恍惚看见俞晓冬窜过来,拿起枕头捂住我的脸。我浑身一动也不能动,只有一根手指在拼命抖动。灰尘,更多的灰尘在我的上空急速荡起,而后慢慢归于平静。
哦,是我走神了。真正向我走来的是护士,护士后面跟着一个手持POS机的男人,原来是院方要我缴纳住院费和手术费。俞晓冬在我的包里找到了我的银行卡,他们让我在POS机上输入银行卡密码。原以为右手食指的恢复是为了抵抗俞晓冬的攻击,可老天爷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它不是用来抵抗攻击的,而是用来输入银行卡密码的。
当我用唯一能动的食指输入密码的那一刻,内心涌起一阵巨大的悲凉——即便刚刚经历了生死浩劫,醒来后依然要面对这个充满金钱交易的现实世界。万一我银行卡上余额不足呢?万一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呢?万一我坠崖导致头部受伤,意识模糊不清呢?只要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我都可能无法获得及时的救助,甚至会被医院拒之门外。泰国的医疗体系不同于我国的“先救治,后结算”模式,一想到如果那一刻我无法结账,可能会被赶出医院,喉咙突然发紧,一股无尽的悲凉在我心中蔓延开来。即便我经历了那么大的背叛与伤害,这个世界对我依旧是那么残酷无情。
收费的人一走,病房顿时空荡起来。麻药劲过去了,剧痛卷土重来,我疼得直叫唤,喊着要打止痛针。这时,我的主治医生进来了,只见他穿着白大褂,长相俊朗,有点像泰国电视剧里的男明星。他轻轻碰了下我的左腿,我立刻发出杀猪般的号叫;他又捏捏我的右腿,我再次嚎得撕心裂肺。他用一口标准英语告诉我:是他和团队给我做了11小时的手术,我的右腿已经打好石膏;我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太严重,暂时用夹板固定,还得再做一次修复手术。
他站在我和俞晓冬之间,宽厚的肩膀让我稍微安心了些。当俞晓冬提出要转院回曼谷治疗时,他直接回绝:“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她的病情我比你更清楚。”
说完,他直视着俞晓冬,目光毫不退让。俞晓冬冷笑一声,转身避开对峙。我的“白大褂”医生亲自给我注射了止痛药,疼痛立刻减轻了一半——我知道,一半是药效,另一半纯粹是因为他在场带来的安全感。
可白大褂刚走,俞晓冬就快步冲到床前。他坚持要让我转院,不想让我继续在乌汶府的医院治疗,他说这里离事发地太近,而且警方也在盯着坠崖事件,这里不安全。他提议先转到曼谷的医院,之后再回中国治疗。
他俯身逼到我面前,脸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低声问我:“转院,你同不同意?”
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眼睛,知道此刻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我心里充满抗拒,还是轻声回答:“好,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