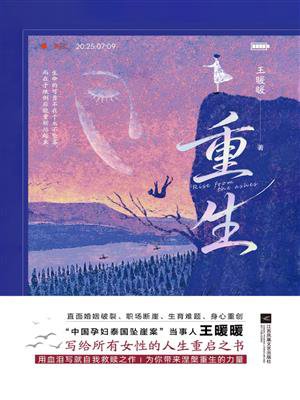4
当天下午,俞晓冬向医院提出转院申请,医院直接驳回了他的请求。医院不放,他就强行带我走。他直接打电话给曼谷的一个私立医院,要求对方从曼谷开一辆救护车到边境乌汶,为此他预付了一万多元人民币。救护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到达乌汶,司机给俞晓冬打电话,说:“救护车已经到医院门口了,你可以把人送过来,我们把她带回曼谷。”
俞晓冬拔掉我身上所有用来监护体征的仪器,包括氧气面罩、导尿管和引流管。由于我睡的病床是可以直通手术室的,病床底下带着滚轮,他就推着移动的病床强行往医院外面闯。
有护士看到这阵势,赶紧过来阻拦。
俞晓冬镇定地说:“我们需要回曼谷更好的医院去治疗,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而且我们自费叫了救护车了,不需要你们管。”
他边说边推着病床向前走,前面有医务人员拉住病床。
俞晓冬有些发狠了,他说:“你们要签那个什么,就是后果自负之类的东西,没关系,我是家属,我来签。”
他的态度强硬,眼睛充血,猩红猩红的,但是,医务人员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们就是不放我走。
医务人员再三强调:这个患者现在已经是濒死的状态了,而且刚做完11个小时的大型手术,身上全是创口。创口一旦感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之所以把患者送进ICU,而且还是ICU中的VIP,就是因为患者是重症中的重症,连动都不能动,现在把她弄出院,相当于看着她去送死。
冲突爆发得异常激烈,双方争夺的焦点是病床,确切地说,是病床上的我。而我只能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躺着,既不能反抗也无法发声。我的身体动弹不得,更可怕的是,我连抗争的意志都不敢表露。要是让俞晓冬发现我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边,他立刻就会起疑心,就会察觉到我承诺的“不报警不揭发”都是假话。所以我只能继续装乖,继续顺从。可天知道,看着他们拖曳我的病床时,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绞痛。
其实,只要医务人员把免责文件拿过来,俞晓冬签了字,他就可以把我带走,我就再也没有以后了。我可能被俞晓冬捂死在救护车上,也可能死于创口感染。我躺在床上,任由俞晓冬拖曳着病床横冲直撞。他的力气大得吓人,医护人员在前面拦着,他就拖着病床在走廊里左右突围。我的身体随着病床剧烈晃动,好几处伤口同时崩裂,鲜血渐渐染透了白色绷带。在剧痛和眩晕中,我仿佛看见俞晓冬正把我和整张病床一起拖向鬼门关——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片刺眼的白光。
我想,这次大概会死吧。
把我从那个白色世界里拉出来的是另外一抹白色。我的主治医生白大褂站在病床的前方,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第一次见他时,觉得他很俊朗,也很绅士,可面前的白大褂变了,变得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圆溜溜的眼睛闪烁着像黑宝石一样的光芒,锐利又充满威严。
他的手搭在病床围栏上,掷地有声地对俞晓冬说:“患者不能出院,无论你讲什么都不能出院,即便你已经把曼谷的救护车花钱调过来了,即便你愿意在出院申请书上面,自己签后果自负,我们还是不能放她走。因为她是一条生命,从医学的角度判断,她现在出院,伤口暴发大量的感染可能会引发免疫系统的问题,她会死的,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去。”
听到这些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白大褂疯狂、执拗甚至是固执地握着病床的栏杆,死活也不肯退后,在他眼里,我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不允许他的病人去送死。而我也不希望白大褂遇到任何不测,这比我自己死去还要难以接受。我知道俞晓冬身上可能藏着枪,我不敢想象他会不会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情。
热带季风吹进走廊,所有人的衣角都被掀了起来。风笼盖了一切,也刮在我的脸上,刚刚流下的眼泪居然被风吹了回来,重新灌进了眼睛。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医院走廊里黑压压一片,挤满了人,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能赶过来的都赶过来了,他们站在白大褂身后,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墙。
那一刻,一股巨大的暖流瞬间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再次滑落眼眶。
俞晓冬的手伸进裤兜,我知道他在犹豫。如果枪在裤兜里,他掏出枪,那么事件性质就会由强行带老婆出院转变为持枪劫持人质,到时候警察会出现,狙击手也会出现。
季风刮过,大雨倾盆,砸在住院楼外的铁皮车棚上,发出“啪啪啪”的响声。我从每个人脸上都看到了急切、焦躁,甚至是颤抖。突然,手机铃声响起,铃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散开。俞晓冬接起电话,他的脸上也出现了涟漪,不,应该是巨石投入湖面砸出的黑洞。
电话是曼谷的救护车司机打来的:他们从曼谷开了十几个小时,已经人困马乏了,司机提前半个小时给俞晓冬打过电话了,他们的预想是车到人也该送到,然后把人推上车,他们赶紧返回曼谷。可是,俞晓冬折腾了这么久还没把人弄出去,司机很不耐烦,一直催催催。
救护车从曼谷出发之前,俞晓冬已经把车费打过去了,相当于曼谷的医院已经收到车马费了。救护车到了乌汶,却迟迟接不到人,司机和随车护士给俞晓冬打了好几次电话,问走不走,不走他们就回程了,因为救护车还要给别的病人用。司机最后一次跟俞晓冬沟通后,没有经过俞晓冬的同意,直接开车回曼谷了。
我想,救护车上的司机和医护人员也算变相救了我一命吧。
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开走了,俞晓冬也松开了我的病床,他说:“算了,那就先安定下来吧。”
白大褂和护士把我推回ICU时,我看见棚顶的灯向后掠过,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移动医院里,窗外风雨交加,走廊内人影幢幢,他们全是天使,他们拼死保护着病床上的我。是的,我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去送死。所以,我不能辜负了他们。
我想,是时候主动出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