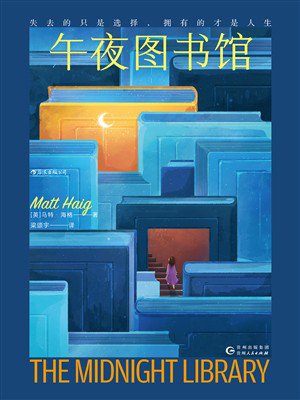门外的男人
决定去死的二十七个小时前,诺拉坐在破旧的沙发上,琢磨旁人的幸福生活。她正等着大事发生。不知怎的,接下来果然有事情发生。
有人按响了她家的门铃。
在那一刻,诺拉犹豫该不该去应门。虽然才晚上九点,她已经换上了睡衣。她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T恤衫,衣服上面印着“环保斗士”的字样,下身穿着一条格子图案的睡裤。她也意识到自己这副模样实在不好见人。
她穿上拖鞋,好让自己看上去像样一点,然后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小伙子,他们曾有过几面之缘。
他的身材高挑瘦削,洋溢着几分孩子气。他一脸和善,眼睛却犀利有神,仿佛能看穿事物表面。
诺拉很高兴见到他,但她稍稍有些惊讶。看到他一身运动装束站在自己对面,在这寒冷的雨天里热气腾腾、浑身冒汗,她甚至比五秒钟之前更加自惭形秽了。
诺拉向来觉得孤独。虽说她对存在主义哲学知之甚多,知道在这个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宇宙中,孤独是人类个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还是很高兴能见到他。
她露出微笑:“你叫艾许,对吧?”
“是的。”
“很高兴见到你,有什么事?”
几个星期前,艾许沿着班克罗夫特大道跑步。在经过A33号的时候,他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诺拉。当时诺拉正在弹奏电子琴,艾许朝她挥挥手。大约在一年前,他还邀请她一起喝咖啡。或许现在他又想约她去喝咖啡呢。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艾许说,可是他那紧皱的眉头没有半点“高兴”的意思。
他在乐器店里和诺拉聊天的时候总是有说有笑,可现在他的嗓音里却蕴含着沉重。他挠挠额头,支支吾吾地吐不出一个完整的词。
“你在跑步吗?”诺拉问道。这个问题真是白痴,他当然是在跑步。可是在那一刻,这句寒暄却让艾许稍稍放松。
“是啊,我正在为周日的贝德福德半程马拉松做准备。”
“哦,对哦,好棒啊。我当时也想参加半程马拉松来着,可后来又想起自己讨厌跑步。”
她原本以为这句话很风趣,可话一出口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并不讨厌跑步。可不管怎么说,艾许那凝重的表情让她惶惶不安。接下来两人都没说话,沉默中不仅蕴含着尴尬,还有别的东西。
艾许总算开口了:“我记得你说你养了一只猫?”
“没错。”
“我记得它的名字是伏尔泰,是一只橘猫,对吧?”
“没错,不过我叫它‘福子’。它觉得‘伏尔泰’这个名字太矫揉造作了,看来它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和文学不是很感冒。它可是一只很接地气的猫咪。”
艾许低头看着她的拖鞋。
“我觉得……它恐怕是死了。”
“什么?”
“它躺在路边一动不动。我看到了它项圈上的名字,我想是一辆车撞到了它。我为你感到难过,诺拉。”
此时此刻,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把诺拉吓坏了。她硬撑着一张笑脸,仿佛这样就可以一直留在刚才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福子还活着,而这个曾向她购买吉他乐谱的男人之所以要按响她的门铃,是出于别的原因。
她记起艾许是个外科医生,不是兽医,也不是家庭医生。当他说某个生物死了,那十有八九就是真的。
“我很难过。”他说。
这种悲痛似曾相识。幸好她服用了抗抑郁药,不然她当场就要哭喊起来了。“哦,上帝啊。”她说。
她走出门,走上班克罗夫特大道,她的脚落在湿漉漉的碎石街砖上。她几乎透不过气。在雨水冲刷下,人行道边的柏油路面闪闪发亮。她看到一团橘色的绒毛摊在闪亮的路面上,看上去那么可怜。它的头顶着人行道的边沿,它的腿向后撇,仿佛正跳到半空中,追逐一只虚幻的小鸟。
“啊,福子!不,不要!上帝啊!”
她知道她应该为自己的毛小孩感到怜悯和绝望,事实也的确如此。但除此之外,她的内心还涌动着其他情绪。她看着伏尔泰——那只猫咪一动不动,宁静安详,再也感觉不到疼痛。这时一股难以摆脱的情绪却暗暗滋生。
那是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