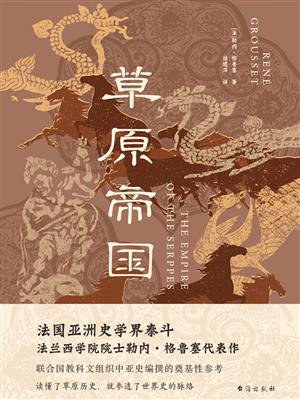导言
草原及其历史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亚洲高原,经历过地球史上最壮观的地理运动。它是由两大褶皱山系-天山和阿尔泰山脉的海西褶皱和喜马拉雅褶皱山系碰撞挤压形成。天山以西域版块为界,阿尔泰山以安哥拉大陆的古西伯利亚高原为界。喜马拉雅褶皱则在中生代和新生代期间取代了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
 。天山和阿尔泰山向西北凸起的弓形与喜马拉雅山朝南突出的凹形合拢,把突厥斯坦
。天山和阿尔泰山向西北凸起的弓形与喜马拉雅山朝南突出的凹形合拢,把突厥斯坦
 和蒙古包围隔绝开来,使其悬挂在四周平原之上。由于海拔较高,远离海洋,这里便形成了极端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在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
和蒙古包围隔绝开来,使其悬挂在四周平原之上。由于海拔较高,远离海洋,这里便形成了极端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在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
 ,气温变化幅度很大,从零上38℃至零下42℃。高海拔使得西藏高原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形成典型的高山气候,山脚森林遍布,山顶植物稀疏。除了西藏高原、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整个亚洲内陆几乎都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草原上万物冬季休眠,夏季枯黄。在灌溉区,草原土地肥沃,生机勃勃。在中部空旷地带,草原渐渐被死气沉沉的荒漠取代。这条草原带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延伸到梅尔夫(马雷)
,气温变化幅度很大,从零上38℃至零下42℃。高海拔使得西藏高原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形成典型的高山气候,山脚森林遍布,山顶植物稀疏。除了西藏高原、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整个亚洲内陆几乎都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草原上万物冬季休眠,夏季枯黄。在灌溉区,草原土地肥沃,生机勃勃。在中部空旷地带,草原渐渐被死气沉沉的荒漠取代。这条草原带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延伸到梅尔夫(马雷)
 和巴尔赫地区,欧亚北部草原在此处被有地中海气候特征的伊朗和亚热带草原气候的阿富汗取代。
和巴尔赫地区,欧亚北部草原在此处被有地中海气候特征的伊朗和亚热带草原气候的阿富汗取代。
在北方,欧亚大陆纵向的草原地带与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北部的大森林地带、蒙古北缘和中国东北部汇合。在中部的三个地区,草原逐渐让位于广袤的沙漠:河中地区
 的克孜勒库姆沙漠(Kyzyl-Kum)和阿姆河以南的卡拉库姆沙漠;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从西南贯穿东北的戈壁沙漠,该沙漠从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的罗布泊起,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边境的兴安岭。在有文字记载之前,这些沙漠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蚕食着周边的草原地带。戈壁沙漠的北面是北蒙古、贝加尔湖畔的森林、鄂尔浑河和怯绿连河(克鲁伦河)
的克孜勒库姆沙漠(Kyzyl-Kum)和阿姆河以南的卡拉库姆沙漠;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从西南贯穿东北的戈壁沙漠,该沙漠从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的罗布泊起,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边境的兴安岭。在有文字记载之前,这些沙漠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蚕食着周边的草原地带。戈壁沙漠的北面是北蒙古、贝加尔湖畔的森林、鄂尔浑河和怯绿连河(克鲁伦河)
 流域的草原地区,南面是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草原和热河。不论是对古代的匈奴帝国还是中世纪的突厥帝国而言,中间的戈壁荒漠都是长久以来阻碍这些突厥-蒙古帝国幸存下来的因素之一。
流域的草原地区,南面是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草原和热河。不论是对古代的匈奴帝国还是中世纪的突厥帝国而言,中间的戈壁荒漠都是长久以来阻碍这些突厥-蒙古帝国幸存下来的因素之一。
对位于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来说,沙漠边缘的这条草原之路决定性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历史。尽管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和控制,这一地区仍摆脱了草原游牧生活,形成了具有城市和商业特征的商路绿洲。众多的绿洲链条式排列开来,连接起世界几大文明板块,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与远东的中国文明。在干涸的塔里木河南北的两条凸形河岸上,两条贸易线路诞生了:北线经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喀什、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南线经过敦煌、和田、叶尔羌、帕米尔山谷和巴克特里亚
 。这两条弱似蚁虫跋涉、蜿蜒漫长的细线,交替着穿越沙漠高山,顽强地将地球连成一个整体,使地球不再是隔绝开来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它维持着中国和印欧之间最低限度的联系,这便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这条路,进行着贸易往来和宗教传播;沿着这条路,迎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的希腊艺术和阿富汗地区的佛教徒。通过这条路,托勒密
。这两条弱似蚁虫跋涉、蜿蜒漫长的细线,交替着穿越沙漠高山,顽强地将地球连成一个整体,使地球不再是隔绝开来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它维持着中国和印欧之间最低限度的联系,这便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这条路,进行着贸易往来和宗教传播;沿着这条路,迎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的希腊艺术和阿富汗地区的佛教徒。通过这条路,托勒密
 曾记载,希腊-罗马商人曾竭力控制着易于获得“塞里斯国”
曾记载,希腊-罗马商人曾竭力控制着易于获得“塞里斯国”
 大捆丝绸的途径,而中国东汉大将们也试图与伊朗世界和东罗马帝国进行交往。从汉朝到忽必烈时期,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无阻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基本政策。
大捆丝绸的途径,而中国东汉大将们也试图与伊朗世界和东罗马帝国进行交往。从汉朝到忽必烈时期,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无阻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基本政策。
然而,在这条通向文明的狭窄小道的北面,草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由无数羊肠小道组成的无边的路,即蛮族之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畔与巴尔喀什湖岸,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来势汹汹的蛮族大军,因为看上去合拢在一起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北部支脉在塔尔巴哈台的额敏河处朝着塔城(Chuguchak)的方向上,仍然有宽阔的缺口,在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朝西北方向也存在较大的缝隙,从这里,蒙古游牧民可以看到远方一望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塔尔巴哈台、阿拉套和木扎尔特的通道上,不断出现从东方向西方草原迁徙的游牧民。在史前时期,这一迁徙运动的方向可能相反,我们知道的伊朗种(印欧种人)的游牧民,即希腊史学家称呼的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伊朗碑文上称呼的萨卡人,曾经朝东北方向远徙,到达巴泽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而另一些印欧种人则移居到塔里木盆地定居,分布在从喀什到库车、焉耆、吐鲁番,甚至远至甘肃的广大地区。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自东向西的迁徙始于公元初年。之后,印欧各族的语言,像“东伊朗语”、库车语和吐火罗语,在中国突厥斯坦的绿洲上不再流行,反而是被称作“匈人”的匈奴人,在南俄罗斯和匈牙利建立了前突厥帝国。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而俄罗斯草原则是亚洲草原的延伸。之后是阿瓦尔人(Avars)先后统治着俄罗斯和匈牙利,阿瓦尔人是6世纪无法忍受突厥人压迫而从中亚逃出来的蒙古族部落。7世纪的可萨突厥人,11世纪的佩切涅格突厥人,12世纪的库曼突厥人,都沿着同一道路奔驰而来。最终在13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统一草原,成为从北京到基辅的统治者。

草原自身的历史是突厥-蒙古游牧部落为争夺肥沃牧场互相吞并的历史,是因畜牧需要而在不同牧场间四处迁徙的历史。有时,因路途遥远,游牧部落往往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迁徙。游牧民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逐渐适应了这种迁徙生活。定居民记录了他们在黄河和布达佩斯之间不停游荡的历史,但只限于那些当时对定居民产生影响的事件,因此数量不多。他们记录了在长城脚下、多瑙河要塞、大同城前,或锡里斯特拉城下,所遭受的游牧民族潮水般的猛烈攻击。但是,关于突厥-蒙古各族间的内部争斗,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在鄂尔浑河源头,在被称为帝国地区的喀拉巴拉哈逊(Karabalgasun)和哈拉和林(Karakorum),我们发现了以统治其他游牧部落为目标的所有游牧部落:公元纪年以前就有的突厥语族的匈奴人、3世纪蒙古语族的鲜卑人、5世纪蒙古语族的柔然人、6世纪突厥语族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鹘突厥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
 、10世纪的蒙古语族的契丹人、12世纪突厥语族的克烈人或乃蛮部,以及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尽管我们可以识别出那些侵略统治过其他民族、在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我们并不了解突厥、蒙古和通古斯(Tungus)这三大母族最初的分布状况。毫无疑问,目前通古斯人占据着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的大部分,以及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蒙古人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本土,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不过,突厥人并非突厥斯坦的原居民,而是后来迁入的,公元1世纪才在阿尔泰地区崭露头角,直到9世纪在喀什噶尔、11世纪在河中地区发挥影响力。撒马尔罕
、10世纪的蒙古语族的契丹人、12世纪突厥语族的克烈人或乃蛮部,以及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尽管我们可以识别出那些侵略统治过其他民族、在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我们并不了解突厥、蒙古和通古斯(Tungus)这三大母族最初的分布状况。毫无疑问,目前通古斯人占据着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的大部分,以及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蒙古人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本土,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不过,突厥人并非突厥斯坦的原居民,而是后来迁入的,公元1世纪才在阿尔泰地区崭露头角,直到9世纪在喀什噶尔、11世纪在河中地区发挥影响力。撒马尔罕
 和喀什两城的居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历史告诉我们,在蒙古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后裔显然使许多突厥部落蒙古化,包括阿尔泰山的乃蛮部、戈壁滩的克烈部,及察哈尔的汪古特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落至“青蒙古”麾下前,今天蒙古的一部分仍属于突厥人,甚至今天还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库特人(Yakut)占据着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勒拿河、因迪吉尔卡河(Indigirka)和科雷马河盆地。这支突厥人出现在蒙古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白令海峡附近,因此必须相当谨慎地确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喀什两城的居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历史告诉我们,在蒙古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后裔显然使许多突厥部落蒙古化,包括阿尔泰山的乃蛮部、戈壁滩的克烈部,及察哈尔的汪古特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落至“青蒙古”麾下前,今天蒙古的一部分仍属于突厥人,甚至今天还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库特人(Yakut)占据着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勒拿河、因迪吉尔卡河(Indigirka)和科雷马河盆地。这支突厥人出现在蒙古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白令海峡附近,因此必须相当谨慎地确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所处的地理位置。
 以上事实说明,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体最初可能居住在遥远的东北部,因为当时,不仅现在的喀什噶尔,还有萨彦岭(米努辛斯克)和大阿尔泰(巴泽雷克)的北坡,都被印欧人占据,这些印欧人来自“古印欧人”的摇篮-南俄罗斯。这一假设与语言学者的观点一致,例如伯希和(Pelliot)和纪尧姆·德·埃维西(Guillaume de Hévésy)。在有进一步证据出现前,他们拒绝承认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与以乌拉尔为中心的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an)之间存在某种原始联系。
以上事实说明,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体最初可能居住在遥远的东北部,因为当时,不仅现在的喀什噶尔,还有萨彦岭(米努辛斯克)和大阿尔泰(巴泽雷克)的北坡,都被印欧人占据,这些印欧人来自“古印欧人”的摇篮-南俄罗斯。这一假设与语言学者的观点一致,例如伯希和(Pelliot)和纪尧姆·德·埃维西(Guillaume de Hévésy)。在有进一步证据出现前,他们拒绝承认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与以乌拉尔为中心的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an)之间存在某种原始联系。
 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可能有史以来即存在着原始联系,曾处于共同统治下,经常会产生一些文明术语所说的相互效仿。但考虑到它们当前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大语族曾经分布在亚洲东北的辽阔地域,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可能有史以来即存在着原始联系,曾处于共同统治下,经常会产生一些文明术语所说的相互效仿。但考虑到它们当前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大语族曾经分布在亚洲东北的辽阔地域,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如果突厥-蒙古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迁徙远征,或者寻找牧场过程中发生的不为人知的小冲突的话,那他们的历史意义便无足轻重。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也是这些游牧民存在的重大意义在于,他们一次又一次对南方文明帝国施加压力,直至最终将其征服。游牧部落的袭击符合自然规律,受其土生土长的草原上的居住条件的支配。
当然,定居在贝加尔湖森林地区和黑龙江的突厥-蒙古人仍处于未开化的状态,以渔猎为生,比如12世纪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时代的“森林蒙古人”。他们被广袤浩瀚的森林隔绝于世,根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令人羡慕的富庶地区。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与其截然不同。草原牧民以畜牧为生,注定会成为游牧者:畜群追逐牧草,人跟随畜群而行。
此外,草原是马的故乡
 ,草原人天生就是骑兵。不论是西方的伊朗人,还是东方的突厥-蒙古人,是他们发明了骑服。比如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的斯基泰人的着装;或者根据中国历史的记录,中国人于公元前300年仿效匈奴人,在骑兵交战时,用裤子取代长袍。如闪电般出击的牧马人或是弓骑手,在撤退时侧身射箭,能够远距离射中敌人。人们所称的帕提亚回马箭
,草原人天生就是骑兵。不论是西方的伊朗人,还是东方的突厥-蒙古人,是他们发明了骑服。比如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的斯基泰人的着装;或者根据中国历史的记录,中国人于公元前300年仿效匈奴人,在骑兵交战时,用裤子取代长袍。如闪电般出击的牧马人或是弓骑手,在撤退时侧身射箭,能够远距离射中敌人。人们所称的帕提亚回马箭
 ,实际上是斯基泰人和匈人的回马箭。他们在交战和追捕猎物或母马时,都使用箭和套索。
,实际上是斯基泰人和匈人的回马箭。他们在交战和追捕猎物或母马时,都使用箭和套索。
当他们奔驰到草原的尽头,涉足耕地的边缘,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展现在他们面前,令他们垂涎不已。在土生土长的地方,冬天严寒,草原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
 的延续;夏季炎热,草原是戈壁滩的延伸。为了寻找牧场,游牧者只能往兴安岭、阿尔泰山或塔尔巴哈台山迁徙。只有春天才能把草原变成青草茂盛、鲜花遍野的平原,春天对牧民和牲畜而言是最美好的时光。其他季节,特别是冬季,牧民就会把目光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如西南方的“热海”伊塞克湖、东南方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他们对土地耕种不感兴趣,一旦占有了土地,他们就让农田荒芜,把土地变成草场,为马羊提供牧草。
的延续;夏季炎热,草原是戈壁滩的延伸。为了寻找牧场,游牧者只能往兴安岭、阿尔泰山或塔尔巴哈台山迁徙。只有春天才能把草原变成青草茂盛、鲜花遍野的平原,春天对牧民和牲畜而言是最美好的时光。其他季节,特别是冬季,牧民就会把目光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如西南方的“热海”伊塞克湖、东南方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他们对土地耕种不感兴趣,一旦占有了土地,他们就让农田荒芜,把土地变成草场,为马羊提供牧草。
这就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持有的态度。征服北京地区后,他的真正欲望是把河北平原上肥沃的谷子地变成神圣的牧场。他们对春耕一无所知。直到14世纪,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仍然是纯粹的游牧民,愚蠢地洗劫着自己的城市。农民在交纳赋税时稍有反抗,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不过,他们对城市文明的手工艺品和装饰品垂涎三尺,大肆掠夺和洗劫。温和的气候令人向往,但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北京气候太过温和,会令人松懈,因此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过夏天。同样,打败了札兰丁之后,他有意避开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似地狱热锅。不管怎样,他对于舒适生活存有戒心不无道理,因为其曾孙子们入住北京和大不里士的宫殿后,随即开始堕落。但是,只要游牧民还保持着游牧精神,定居者就仍是他们的农民,城镇和耕地仍是他们的农场,农庄和农民仍是他们想方设法压榨的对象。他们骑马沿着古老帝国的边境巡游,从乐意顺从的人那里收受贡赋,一旦受害者拒绝支付,他们就会突袭抢劫这些不设防的城市。他们就像是狼群,徘徊在鹿群周围,扑向它们的咽喉,或者只是捡拾迷途和受伤的野兽。古代突厥人的图腾不正是狼吗?
 疯狂掠夺和以天子的名义勒索定期贡赋交替出现,成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点。
疯狂掠夺和以天子的名义勒索定期贡赋交替出现,成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点。
游牧民族中有时也会出现杰出人物,他们深谙定居帝国的腐朽内幕。这些狡诈的野蛮人,熟悉中国宫廷内的阴谋,就像4世纪的日耳曼人熟悉拜占庭的阴谋一样。他们会联合中国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一个王国反对另一个王国,或者与失败篡位者结成同盟,反对在位的皇帝。他和部落宣称与帝国结盟,打着保卫帝国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边境。经过一两代之后,其子孙具备了中国人的外表,便采取进一步行动,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宝座。13世纪忽必烈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氏的翻版。再经过两三代(如果没有被某次起义赶出长城外),这些中国化的蛮族就从文明生活中学会享乐和放纵,丧失蛮族坚韧的性格。这时他们便反过来成为被蔑视的对象,其领土也成为那些还在草原深处忍饥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觊觎的目标。于是,这一过程再次出现。5世纪,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膀上崛起,将其消灭,取而代之;从10世纪起,彻底中国化的蒙古种族-契丹人成了北京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女真人在契丹人的北面崛起,这些几乎处于原始状态的通古斯人,几个月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北京城,但最终他们也受到中国的影响进入停滞状态,一个世纪后被成吉思汗消灭。
西方和东方的经历一样。在亚洲草原延伸处的俄罗斯草原上,也经历了类似的朝代更替:先是阿提拉的匈人,随后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属芬兰-乌戈尔语族,具有匈奴贵族的强硬)、可萨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伊斯兰的土地上,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征服者也经历了伊斯兰化和伊朗化,就像征服天朝大国的突厥、蒙古和通古斯征服者被中国化的摹本。在西方,可汗成为苏丹或国王;在中国,他成为天子。当然,他也很快让位于更加野蛮的来自草原深处的可汗们。在伊朗,也出现了征服、继承和毁灭的类似过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后,塞尔柱和花剌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纷至沓来,更不必说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箭一般直插穆斯林地区的外缘,取代小亚细亚上垂死的塞尔柱人残部,征服拜占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亚洲大陆可以看作是各民族的母体,约达尼斯
 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要更胜一筹,就像是亚洲的日耳曼尼亚
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要更胜一筹,就像是亚洲的日耳曼尼亚
 ,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向古文明帝国贡献苏丹和天子。草原游牧部落的周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其可汗们纷纷登上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帝位,坐上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成为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但也存在一种逆向规律,游牧侵略者逐渐被古代文明地区同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首先从人口统计学上看,那些野蛮的游牧贵族分散在远古人口稠密地区,淹没在密集的人群中消失了。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中国和波斯被武力征服后,其文明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让他们陶醉其中,浑浑噩噩,最终灭绝。征服后只需要50年,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旦有来自蛮族的新攻击,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会率先起来保卫文明世界。
,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向古文明帝国贡献苏丹和天子。草原游牧部落的周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其可汗们纷纷登上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帝位,坐上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成为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但也存在一种逆向规律,游牧侵略者逐渐被古代文明地区同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首先从人口统计学上看,那些野蛮的游牧贵族分散在远古人口稠密地区,淹没在密集的人群中消失了。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中国和波斯被武力征服后,其文明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让他们陶醉其中,浑浑噩噩,最终灭绝。征服后只需要50年,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旦有来自蛮族的新攻击,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会率先起来保卫文明世界。
公元5世纪,占据洛阳的拓跋族君主自命为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卫者,反对所有企图重建霸业的蒙古人、鲜卑人或者柔然人。公元12世纪,正是塞尔柱人桑贾尔
 在阿姆河和锡尔河建立了突厥版的“莱茵河防线”,抵御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的所有乌古斯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
在阿姆河和锡尔河建立了突厥版的“莱茵河防线”,抵御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的所有乌古斯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
 的经历在亚洲历史上再次上演。就像罗马文明在抵御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其同化的法兰克人中找到后备力量,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拓跋人中找到了坚定的守卫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没有比英雄桑贾尔更为忠实的拥护者了。那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做出了更好的榜样,成为古代诸王之王或天子。库思老或哈里发没有取得胜利,未获得巴赛勒斯王位和入驻圣索菲亚,但出人意料的是其后继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却在伊斯兰世界的欢呼中实现了夙愿。同样,在13世纪和14世纪,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
的经历在亚洲历史上再次上演。就像罗马文明在抵御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其同化的法兰克人中找到后备力量,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拓跋人中找到了坚定的守卫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没有比英雄桑贾尔更为忠实的拥护者了。那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做出了更好的榜样,成为古代诸王之王或天子。库思老或哈里发没有取得胜利,未获得巴赛勒斯王位和入驻圣索菲亚,但出人意料的是其后继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却在伊斯兰世界的欢呼中实现了夙愿。同样,在13世纪和14世纪,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
 实现了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将北京变成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文明古国,最终还是用手中的剑为它服务。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具有古代文明的人,注定要适应文明之人的传统,实现文明之人的长期抱负。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中国的统治者执行中国在亚洲的帝国宏愿,在伊朗-波斯世界,他们完成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进军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事业。
实现了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将北京变成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文明古国,最终还是用手中的剑为它服务。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具有古代文明的人,注定要适应文明之人的传统,实现文明之人的长期抱负。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中国的统治者执行中国在亚洲的帝国宏愿,在伊朗-波斯世界,他们完成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进军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事业。
像罗马人一样建立帝国、取得统治地位的民族并不多见,突厥-蒙古人就是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