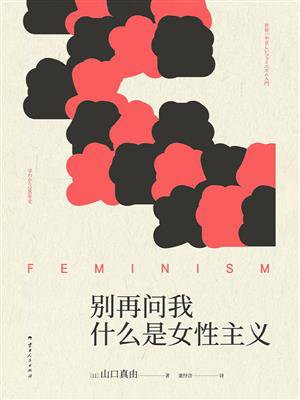1 从“难道人类仅等于男性吗”开始
沃斯通克拉夫特点燃烽火
女性主义第一波浪潮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在当时,推翻君主专制、夺回人民权益的法国大革命,也成了女性从家庭中施行专制的“君主”,也即从丈夫那里谋求解放的契机。
1792年,英国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一书,为女性谋求权利的运动点燃了第一把烽火。
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于伦敦。因为家道中落,她不得不走出家门自力更生。她曾出版《人权辩护》,因思想激进而为世人所知。紧接着,她又出版了《女权辩护》。此前,就连那些摒弃迷信与宗教信仰、重视理性与科学的启蒙思想家,比如法国启蒙运动卓越的代表人物让-雅克·卢梭(1712—1778)都曾表示女人生来不如男人理性,所以必须依赖男人。卢梭在《爱弥儿》中一边提倡要让男性市民爱弥儿得到相应的教育,一边对爱弥儿未来的妻子索菲进行说教,要求她学会讨男人欢心。沃斯通克拉夫特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局限:身为启蒙思想家,却不愿让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惠及女性。男人一边谋求自身自由,一边继续着对女性的奴役。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女性的劣势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社会性原因所致。 少女接受到的教育忽视智慧和自我实现,一味强调要重视自己的外貌和男性的意见,所以才会拼命修饰外在,寻找一个能“供养”自己的男性。由此,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一种极为前卫的观点: 为了被供养而结婚,这种婚姻是另一种形态的卖淫。 此观点一出,便对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冲击。她还呼吁“要确立社会平等,就要消除阶级的存在,解放女性”。 将性别与人种同样视作阶级的一种, 这一观点也彰显出其思想的先驱性。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生于伦敦。女性主义先驱者,社会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创作小说、旅行游记等。
这一时期关于女性权利的主张和革命初期大抵相同,都带着资产阶级式的自由主义气质。这种自由主义更重视为解放灵魂而斗争的战士们争取自由,并不在乎要如何为被奴役者的生活带去安稳与幸福。在这种环境下,有些人认为《女权辩护》就是一本提倡重视教育的女性教科书。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大都很差,尤其是女性主义运动的敌对派。他们不单对本书发出恶评,还进一步抨击作者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称其为“好似穿着衬裙的鬣狗”。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认为女性发表政治性观点本身就是“下流”的。而未婚先孕、两度自杀未遂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异端的存在。

《女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
沃斯通克拉夫特著。该书批判了男性阻碍女性追求知识的行为,呼吁女性想要获得解放,必不可少的就是教育。
生活在没落家族之中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要在经济上支撑父亲和众多兄弟姐妹的开销,又为虚妄的爱情流泪,还坚持发表政治观点。她最终因产褥热,在38岁的年纪便离开了人世。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观念因过于前卫未能被时代所接受,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也为世人所遗忘。直到19世纪末《女权辩护》一书再版,她的作品才作为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最早文献资料重见天日。
不过,当时被法国大革命所震撼的整个欧洲,的确出现了对自己所处地位表示怀疑的女性,其中也存在众多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法国大革命与奥兰普·德古热
法国大革命在引发既存秩序崩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女性可以参与政治的环境。1789年10月,数千名女性劳动者为了争取“面包”向凡尔赛宫进发。在18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法国女性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发行报刊。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俱乐部将她们拒之门外,她们就成立属于女性自己的政治俱乐部。
然而,在女性积极参与大革命并推动王政体制瓦解后,法国的新“统治者”国民议会却对多达六页的呼吁男女平等权利的请愿书视而不见,1789年发表的《人权宣言》也仅以男性为对象。而最早正面抨击这份《人权宣言》的,就是作家奥兰普·德古热。传闻德古热是大贵族蓬皮尼昂公爵的私生女,凭借着超凡的意志提升自身阶级地位,最终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中站稳了脚跟。
1791年,德古热出版名为《女权与女性公民权宣言》的手册,宣称 男女应得到彻底的平等,女性也应拥有参政权。 其理论有浓厚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色彩,比起对男性的批判,更多是在抨击女性自身的生活过得“太窝囊”。

奥兰普·德古热 Olympe de Gouges (1748—1793)
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剧作家,演员。因为宪法之中没有关于女性权利的阐述,故于1791年发表了《女权与女性公民权宣言》,呼吁男女平权。
她的政治主张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女性离婚的权利,女性参与国民议会、行政院及法院的权利等,共通之处是体现了一种对自由生活的勇敢追求。她不单关注女性,也关注黑人奴隶,并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批判奴隶制。她视依靠奴役制度敛财的富裕阶层为敌,还曾收到过威胁她的“杀人预告信”。
德古热这种略具危险性的胆识在革命期间得以充分发挥。她追求女性解放,赞成并煽动革命。但她真正追求的并非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革命,而是更富建设性的改革。因此,她也被质疑是一个为路易十六申辩的保皇派,更何况当革命政府内部斗争开始变得激烈时,她倡导的是和解。当雅各宾派在斗争中占据上风,她还公开撰写文章拥护处于劣势的吉伦特派。之所以说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是因为在当时,这样做是要搭上性命的。

德古热被处刑
法国大革命余波未平之际,德古热因批判革命政府及其煽动性的态度而被判有罪,并被送上断头台。
果不其然,德古热被捕入狱,遭受审判,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从监狱到法庭再到断头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瞬,她在公众面前也绝不显露一丝慌乱,维持着生而为人的尊严,最终从容赴死。
交际花、革命家梅里库尔险些丧命
在投身法国大革命的女性中,也有像塞洛瓦涅·德·梅里库尔这样充满激情的女性。她出身贫寒农家,自幼遭受虐待,承受着残酷的劳动压力。不过,自从成为某位身份高贵的女性的侍女后,她的天生丽质便逐渐大放光彩。此后被贵族看中,进入英国社交圈。梅里库尔学会了高雅的贵族举止,享受着上流社会的淫靡,成了伦敦首屈一指的交际花。她与众多有权人士结为知己,积攒了相当丰厚的财富。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之际,她义无反顾地将男人献予自己的财富投入到对女性的启蒙运动之中。
梅里库尔的美貌、迷人的声音、无比投入的姿态,都使她的演说备受瞩目。她有着极大的煽动力,使民众为之疯狂。
然而,由于梅里库尔是以一种带有性意味的象征人物被捧上台的,似乎少有人认真接受她的思想。她虽因此惨遭舆论所伤,却依然保持着卓然超群的行动能力。她甚至组建了女子骑手队,自己则身穿类似军装的紧身骑马服,随身携带手枪和剑。当时的人们甚至称手握刀枪的梅里库尔是“亚马孙人”——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全部由女战士构成的民族。
在饱受关注的同时,梅里库尔也成了猎奇甚至厌恶的对象。她歇斯底里的演讲风格和非同寻常的行为,遭到雅各宾派以及其他一些群体的攻击。1793年,正在公众面前举行演讲的梅里库尔偶遇其他激进派系的女性集团,其成员将站在讲坛上的梅里库尔拖拽下来,扒下她的裙子,用鞭子将她的臀部打得皮开肉绽。这场私刑险些要了梅里库尔的性命,她也因此精神失常,自那之后再未回归大众视野。

塞洛瓦涅·德·梅里库尔 Théroigne de Méricourt(1762—1817)
生于比利时。11岁离家出走,辗转欧洲各地。20岁进入伦敦社交圈,以交际花的身份闻名。她醉心法国大革命,将个人财产都投入到了支持革命、启蒙女性的活动之中。
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不单有男性参与,不少女性也为之流血牺牲。无论是贵族女性还是农家女,无论是老妪还是年轻姑娘,无论身为共和派还是保皇派,都积极地参与其中。还有一些女性承担了照顾受伤士兵的工作。最终,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都被投进监狱,有些则惨遭杀害。然而,1791年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却不承认这些与男性并肩共进,为自由而奋斗的女性是“市民”。1793年,女性的政治俱乐部遭禁,1795年,女性的政治聚会也被禁止。
不可否认的是,就算在女性之中,支持女性争取选举权的人也并不多。一些大城市的进步女性被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女性却仍旧坚定地信仰天主教,反对革命。何况大革命的精神支柱——卢梭的思想主要是在宣扬希腊和罗马市民战士的“男性气质”,这是一种赋予男性公共领域的责任、将女性推进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分工”。而大革命的指导者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也同样信仰着卢梭的思想。
即便如此,这把源自中产阶级女性启蒙思想的女性主义火焰也没有消失,反而逐渐蔓延到了工人阶级之中。
七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的新展开
此后,法国的平民女性又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提出了新主张。
这场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的女性主义思想复活运动,极大地受到夏尔·傅立叶(1772—1837)和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这两名捍卫平等主义的激进派男性影响。“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便是在傅立叶1837年发表的著作中出现的。
傅立叶和圣西门二人都设想了近代家庭模式的替代方案,这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他们提出要用集体生活代替家庭生活,其中傅立叶更是表示“ 妇女的自由程度就是衡量社会自由的标准”。 在当时,这样的思想相当前卫,无法被同时代的大众接受,甚至受到了无情的嘲讽。
不过他们的思想及行为影响到了一些女性,画家保罗·高更的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这样富有战斗性的女性主义者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极富个性与热情的女性中,有人在二月革命中挺身而出,站上围墙,或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还有人参与制作枪炮弹药。她们将宣扬女性权利的女性主义与为劳动者们谋求权利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一来,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和改善工作条件也一并成为她们呼吁的主旨。1848年成立的女性权利委员会还曾掀起拥立当时以自由女性身份著称的乔治·桑为国民议会议员的运动。当然,在那个时代,别说被选举权了,女性甚至连选举权都没有。
这些女性主义者高举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希望它的影响力不只停留在资产阶级女性内部,还要扩大到工人阶级女性之中。 女性主义运动由此也得到进一步展开。
让女性内部分化加剧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在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之间劈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1803—1844)
生于法国。作家,社会改革运动家。父亲是秘鲁贵族,母亲出身法国的资产阶级家庭。她曾结婚又离婚,也曾投入工作,与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拥有十分旺盛的创作激情,致力于追求女性权利内容的扩大与丰富。
当时女性主义的中坚力量,主要是被排除在经济职能之外、受困于家庭的中产阶级女性。相较于追求教育改善、有意义的事业和参政权的她们,那些在工厂中工作的劳动妇女鲜少发出相同的声音。比起这些抽象的权利,劳动妇女更关心薪水和劳动条件的切实改善,因而在观点上更倾向于劳动组合主义,也更容易向鼓励妇女摆脱婚姻压迫、组建集体生活的圣西门主义靠拢。
察觉到女性之间这道鸿沟的,是苏珊娜·沃伊金(1801—1877)。作为一名刺绣手工艺人,她通过编撰报刊《女性论坛》,倡议像自己这样的无产阶级女性和资产阶级女性应该同心协力,携手成为“新女性”。
关于劳动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也借鉴了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正是资本主义导致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之中被迫成为二等公民。

乔治·桑 George Sand(1804—1876)
生于巴黎。作家。她在公共场合穿着男性服装(在当时这是非法的),吸烟,同时和多位男性保持恋爱关系,这些行为使她成为自由女性的象征。当时乔治·桑已是欧洲颇有人气的作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她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一边主持女性权利扩张的运动。
话虽如此,提倡靠革命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女性的马克思,此后却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上,几乎再未谈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不过,马克思在晚年又回归了这一主题,恩格斯则以其遗留的海量笔记的一部分为基础,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本书将在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希望”中再度谈及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