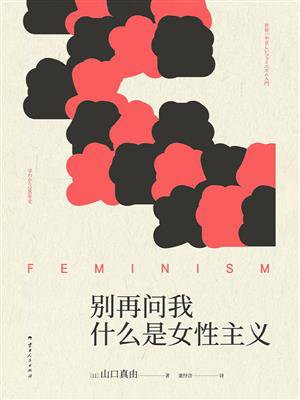2 英国女性主义的先声
近代家庭的诞生与女性主义
比起法国,英国女性争取参政权和财产权的运动发生得要更早。 讽刺的是,女性主义萌芽的契机,正是近代家庭的诞生。
在旧有的共同体中,如果丈夫对妻子施加暴力或行为专横,共同体便会主动介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日本落语故事里的情况:房东插手房客家庭矛盾,对房客进行说教或施加惩戒。这种故事十分多见。同样地,在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中,倘若丈夫的行为令人难以忍受,村落共同体和教会就会出面干涉。
然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近代革命提出“私有财产”的概念,改变了这种共同体的价值观。这里所说的私有财产不单包括土地和金钱等“物”,还涉及“人”。可以说,近代革命创造了一个叫作“近代家庭”的隔绝区域。这种家庭是一个封闭空间,它躲开了共同体的“监视”。 而在家庭这样一个私人领域之中,女性没有任何权利。 妻子被视作丈夫的私人财产,说得再极端一些,要杀要剐全凭丈夫裁决。
在结婚的同时,妻子的财产管理权就会被丈夫剥夺,从而丧失独自立下任何契约的能力。未来即便遭受暴力、监禁、虐待,女性也几乎无权离婚。一旦逃离家庭,甚至会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
1830年的“卡罗琳·诺顿事件”,就将近代家庭中极端不合理之处彻底暴露了出来。
卡罗琳·诺顿的丈夫乔治没有收入,靠妻子的财产度日,还会对妻子施暴。卡罗琳遭丈夫家暴流产,逃回娘家。可当她想要再回到自己家时,却被拒之门外。她的丈夫不允许她见自己的三个儿子,包括年仅两岁的幼子。六年后这个幼子去世,卡罗琳怀疑他的死亡并非事故,而是疏于照顾所致。孩子被夺走的同时,卡罗琳在经济上也惨遭丈夫控制。她通过创作得来的收入和继承的财产被丈夫尽数收入囊中,对方甚至时常拒绝支付她的生活费。卡罗琳不仅失去了监护权,甚至无法经济自足。未免过于不合理了。

卡罗琳·诺顿 Caroline Norton(1808—1877)
生于伦敦。社会改革运动家,作家。经历过和善妒且占有欲极强的丈夫分居、离婚、争夺抚养权等一系列苦难后,卡罗琳致力于为已婚及离婚的女性争取应得的权利,推动了数条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写。
一个被迫失去爱子的母亲,在这个既无法拥有孩子监护权,作为妻子也无权与丈夫离婚的时代,得不到任何法律救济。于是,这位文采斐然的女性便将自己的遭遇始末写成一本册子,试图唤起舆论关注。在当时的社交界,大部分人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不过,卡罗琳此举并不是要呼吁男女平等,更多的只是在寻求同情和庇护。她认为男女平等是荒唐的,保护女性是男性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或许正是因为她的这一思想前提和当时的主流思想并无太大出入,所以才会得到当时的舆论支持吧。
住家女家庭教师的活跃
进入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大旗开始由住家女家庭教师扛起。 其实,出版了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女权辩护》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曾是一名女家庭教师。正是这些充满智慧的家庭教师们,充当了贵族阶级法规形成过程的观察者。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这是一场激进派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积极要求在工人阶级中进一步扩大参政权的运动。虽然女性也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之中,可运动提出的诉求条目里却并没有出现争取女性参政权的内容。也就是说,就连那些寻求社会改革的女性们,也认可男性指导性的优越地位。
反倒是19世纪50年代,在宪章运动遭受打击之后,女性运动的进程才正式开启。 这是一场中产阶级的女性运动,参与者普遍要求从实质上改善女性的各项权利。
此次运动的成果是1857年《婚姻诉讼法》的出台以及离婚法院的设立。1870年和1882年,议会两次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承认妻子可独自拥有财产。由于英国在较早阶段就从民法层面上大致消除了男女不平等,争取女性参政权比起实际利益,更像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象征。
争取女性参政权的约翰·穆勒议员及他的伴侣泰勒
英国的女性参政权运动是从1867年开始迈入正式化进程的。1866年,约翰·穆勒(1806—1873)将女性参政权的诉求提上公约。 他在女性主义团体的支持下当选议员,并在下议院举行了最初的一波争取女性参政权的请愿活动。 穆勒和他的伴侣哈里特·泰勒在二人共著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对女性相关问题做了系统性阐述。泰勒此前在其著作《女性参政权》中已经强调了女性对参政权的需求,她在该书中指出:包含公职在内的一切职业,都应对女性开放。
《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有一个极富先驱性的观念,它认为 男女之间的差异并非“女性的(本质)天性”,而是“社会有意制造出来的”,并宣称从社会角度来说,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差异正是社会不公的源头。 由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属于保守阶层的一种基本观念,此书的主张遭到保守阶层的反对,但获得了大部分女性参政权运动参与者的支持。此外,这一观念也是第二章将要提到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原型,后世更是将《妇女的屈从地位》奉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

哈里特·泰勒 Harriet Taylor(1807—1858)
生于伦敦。哲学家。初婚后与穆勒相遇,二人的友情逐渐转变为爱情。此后二人结婚,思想上互相影响。穆勒的作品《妇女的屈从地位》就是和泰勒共同完成的。
不过,该书同时主张:女性要承担生产和育儿任务,所以男性出去赚钱、女性专注于家务工作的基本方法是适用于大多数家庭的。除去少数有能力的、“例外的”女性,大部分女性都不该从事需要走出家门的劳动,以免妨碍家务及育儿工作。这一主张在后来遭到了批判。实际上书中“有能力的女性才享有经济独立的权利”的观念大大领先于它所处的时代,而这一观念也涉及我们下一章将要提到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问题。

约翰·穆勒(左)泰勒的女儿海伦·泰勒(右)
泰勒死后,海伦继续支持着穆勒的工作。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泰勒是一名十分聪慧的女性。被迫走进婚姻后,她遇见了认可其智慧光芒、对她充满敬意,也能平等对待她的穆勒。两个人的灵魂产生了深刻共鸣,谁都不愿放弃这段感情。于是,在得到泰勒丈夫的公开认可后,泰勒开始追求和穆勒之间的柏拉图式情感。然而这种做法被外界视作丑闻,泰勒也因此被逐出社交圈,吃了不少苦头。即便如此,两人还是等到泰勒丈夫去世后才结了婚。然而,当1869年由他们二人共同写作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公开发表之时,泰勒已经去世了。穆勒始终强调泰勒的积极贡献,并宣扬自己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和这位头脑极为聪慧的女性共同创作的。
女性参政权运动的“黑色星期五”
接下来,英国追求女性参政权的活动开始由温和派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UWSS)和激进派的英国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分开主导。
WSPU的领导者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通称潘克赫斯特夫人)以及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西尔维娅和阿迪拉。 她们坚信“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具体目的,就是获得女性参政权。在那个时代,女性获得参政权并非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她们相信,只要女性拥有参政权,世界就会改变。然而,这种观念放在当时野心太大,大众很难理解。激进派女性参政论者认为,首先要把大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议题上来,这种迫切的愿望也导致她们采取了一些带着表演意味的激进行动。
具体来说,她们发动示威游行,对政府不认可女性参政的态度表示抗议,妨碍政治家的演说活动,甚至还打破了首相官邸的玻璃窗。潘克赫斯特夫人最器重的大女儿克里斯塔贝尔表现尤为活跃,经常会想出一些极富独创性的战斗策略。
1910年,正当女性参政权行将获得承认之际,时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插手喊停了相关法案。同年11月18日,伦敦约300名女性聚集在议会周边进行抗议游行活动。其中119人被逮捕,2人身亡,人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五”。自此之后,运动发展方向越来越趋向激烈。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
激进派女性参政权活动家。1903年创立英国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致力于为所有女性争取参政权。因举行激进的抗议活动受到瞩目。
WSPU的行动此前备受警察和一些男性的暴力及猥亵的困扰,因此领导者常会向女性传授一些自卫的手段。比如为保护肋骨,可以穿塞了厚纸板的马甲。潘克赫斯特夫人还想到了一个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学习警察们必须接受的训练——柔术。当时很多媒体都记录下了中产阶级女性积极练习格斗技能的场面。
WSPU的成员们会深夜潜入国会议员的住所以及教会、邮局、铁路等区域,进行点火或爆破等活动。恐怖行动持续升级的代价则是成员们屡遭政府逮捕,被投入监狱。但在她们看来,遭受逮捕正是引起民众关注的最好手段。而且她们早有觉悟,一旦被捕便要作为殉道者赴死,于是毫不畏惧地进行了绝食抗议。
另一边,警方认为,她们当中哪怕有一个人如愿为名誉而战死,就势必会招致大众的愤怒情绪,于是开始用鼻饲管强行为绝食抗议的女性塞入食物,因此严重伤害了她们的身体。此举由一位遭拘留的运动家玛丽·李公之于众,引发民众的强烈谴责,运动随之愈演愈烈。

英国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活动。
“动口不如动手”(“DEEDS NOT WORDS”),正是WSPU的标语。
即便如此,这些抗议行为也丝毫没有撼动政府的态度。于是,意识到这一点而越发焦急的WSPU成员们选择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潘克赫斯特夫人被捕,运动的激化与走低
此前,潘克赫斯特夫人每次出现在公共场所时都会有30人左右的精锐保镖队伍将她围住。她们的裙下都藏着棍棒,用各种方式保护潘克赫斯特夫人,避免她遭受逮捕。
潘克赫斯特夫人等人被逮捕后,一位名为玛丽·理查德森的运动家进入国家美术馆,用刀子割开了出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之手的名画《镜前的维纳斯》。她宣称:“我要毁掉描绘神话史上最美女性的画作,这是我对你们妄图毁掉现代史上人格最美的潘克赫斯特夫人的抗议。”
紧接着,1913年,一位名叫埃米莉·戴维森的WSPU成员冲进国王驾临的赛马场,随即葬身国王的马蹄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响使争取女性参政权的运动进入休战状态。 潘克赫斯特夫人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样也是热诚的爱国者。她倡议,祖国面临危机之时民众应团结一致,眼下并非在内部宣扬不同主张的时候。
事实上,在和工人运动合作这方面,潘克赫斯特夫人始终持怀疑态度。她和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更倾向于优先争取上层和中产阶级女性的参政权,她的另一位女儿西尔维娅则坚持将女性权利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最终,潘克赫斯特夫人一家所领导的、来势汹汹的女性参政权运动,还是被工党吸收成为其方针策略的一环。
英国最早采纳女性参政权的是工党,到1917年,女性参政权已经成为超党派的方针,实现它只是时间问题。翌年,英国以一种稍做限制和改变规则的形式采纳了这一倡议,1928年时则彻底将参政权赋予了女性。
然而,想要实现女性参政权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此时却陷入了一种认同危机:自己的主张被采纳了,期盼许久的女性参政权实现了,世界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本以为女性拿到参政权后,国家会陆续出台许多与女性相关的政策,事实却恰好相反。很多女性根本不愿意行使这一权利,积极参与到政治之中。当女性主义者们因达成目标而兴奋之时,普通女性对政治的冷漠却好似一盆冷水当头浇下。这些女性主义者的热情顿时被扑灭,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波浪潮也自此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