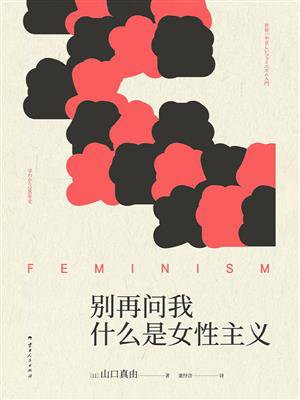1 “理想生活方式”的诞生
美国,物质生活丰富的国家
20世纪,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斥着物质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整个社会也走进了物质丰富的时期。欧美国家更是抢先一步,展开了生产力革命。
福特公司以革新气质著称,就像是今天的特斯拉。特斯拉推出的电动汽车对汽车工业来说是颠覆性的,同样,当时的福特公司也引发了一场被称作“福特主义”的汽车产业革命。
在当时,汽车还是只有富裕阶级才买得起的高级商品。然而,在亨利·福特(1863—1947)首次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颠覆了原有的汽车生产方法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汽车在传送带上移动着,劳动者们将各种零件组装上去。这种方式将汽车的制造过程细分化、单一化,如此一来,就算不是熟练工也能从事汽车制造这一行业。于是,大批量生产的方式由此而生,这也正是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大特征。至此,社会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福特T型汽车的生产数量从1908年的不满7000台飙升到1923年的突破220万台,翌年也超过了200万台。随着产量的增加,定价也一路下滑。1908年一台福特T型汽车的价格是860美元,1913年跌至600美元,到1922年时已经跌到了300美元。
到这一步,福特公司算是完成了让供给方大量生产的步骤。接下来便要开始刺激需求,让民众产生购买欲望了。他们积极进行海量宣传,掀起了一场市场营销革命。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拥有一件物品不再是简单地为了获取某种便利,而是变成了地位的象征。
与此同时,福特公司的工资水平也在上升。1914年,福特宣布员工每日的薪水为5美元。这个金额高于当时市场价的两倍,引发了社会轰动。因为推行流水线组装的模式,熟练工的价值相应下降,招致了大批员工的不满和离职。之所以选择大幅提高工资,则是福特为了稳定公司内的劳动力而推行的政策。
每天能拿5美元,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1000美元。在当时,这个程度的年收入足够维持一个蓝领家庭一整年的开销,并且还能额外购入一台福特T型轿车。
就这样,大批量生产、低廉的售价、高工资,这三点组合在一起,满足了高度经济增长所需的必要条件。高薪劳动者通过购买价格逐渐低廉的消费品而产生了大量的消费。供给方的大量生产由需求方的大量消费支撑,再进一步导致过剩的产量和多余的消费。供给方和需求方彼此令人目眩地互相影响,最终塑造了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
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却是压迫肉体和精神的“整齐划一的劳动”。流水线作业非常单调,会让劳动者产生一种自己只是机器中的一个零件的错觉。即便如此,为了维持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为了支付分期付款买下的消费品,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拼命劳动。
逐渐“麦当劳化”的社会
2016年,一部名为《大创业家》的电影上映,讲述了麦当劳公司创始人雷·克洛克的故事。
1954年,克洛克正做着推销员的工作,整日上门推销他自主研发的奶昔搅拌机,销量却并不大好。正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一家汉堡店的大量订单,于是便带着自己的产品拜访了那家店。在那里,他看到一份汉堡的制作被细分成烹饪饼皮、烤制肉饼、摆放酸黄瓜片和浇酱汁,整个流程的步骤各有对应的责任人来进行作业。克洛克一眼就从这种高效的运营方法中看到商机,于是马上说服经营该店的麦当劳兄弟理查德和莫里斯,拿下了经营权。
虽然这部电影主要表现的是贪婪的克洛克和麦当劳兄弟的对立,但麦当劳兄弟创造的细分化、分工化、单一化的生产方式,和克洛克的经营手法本身是相互契合的。克洛克就这样复制了麦当劳兄弟的模式,不断开设分店,最终将一间小小的汉堡店扩散到了整个美国。
麦当劳象征着大食量的美国饮食文化,同时也成为在保证一定品质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生产的象征。20世纪,整个美国社会都在逐渐地“麦当劳化”。
家庭主妇诞生
生产、消费的扩大化,逐渐上涨的工资,都赋予了美国男性更强的经济实力。现在他们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养活妻子。但是, 男性劳动者经济实力上涨的同时,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却始终处在极低的水平,一直没有变化,甚至连自力更生都很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婚后辞去工作回归家庭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趋势。“经济上抚养妻儿是男性的义务”这一社会规范就这样诞生了,妻子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局面也成了必然。
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其实是一个人人都化身工作狂的时代。比起从事流水线机械化工作的“蓝领”,坐办公室的“白领”劳动时间延长得更多。原因之一就是在物质达到极大丰富的社会之中,人们的消费欲也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刺激。
可是,原因不单如此。这一时期,劳动本身也被神圣化了。周末也要继续劳动,坚持那种拿不到相应报酬的加班,这在当时统统被美化成了员工对工作的献身精神。
在美国,美化劳动的源头其实是新教徒的禁欲思想。不过,在受基督教影响并不大的日本,人们大多也认可这种克己奉公的做法。虽然两国的思想基础各有不同,但这些思想都被经营者加以利用,对员工进行诱导。就这样,“休息可耻,只有工作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作为一种新的想法逐渐扩散开来。
“宽敞的家+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套餐
美化劳动的思想换了一种说辞,也开始对主妇们产生影响。
在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掀起的时候,男性被描述成专制君主。然而, 当那些认为“从属于丈夫是一种奴性的体现”并勇敢反抗的女性们拥有了一位“深爱自己的丈夫”,而不是“暴君”时,却瞬间改变了态度。 “我们遵循自由意志,愿为深爱自己的丈夫奉献一切”,这种言论将结婚变成一种浪漫之举。如此一来,成为家庭主妇就不再是未能达到经济独立的女性的妥协,而成了她们主动选择并认同的结果。
最终, 就像这一时代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一样,主妇们也开始对做家务产生了一种自豪感。
把宽敞的家收拾得一尘不染;亲手制作点心,而非买现成品;把衬衫熨烫得板正挺括,好让丈夫每天都身穿平整如新的服装走出家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务原本应该变得更加简单,但当时大家人为地把整洁和完美的要求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并以此视作评判妻子对丈夫爱情的标准。
奇怪的是,家务越变越多的同时,做家务的人却只剩主妇一个了。
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家中年长的孩子是承担家务、协助育儿工作的重要家庭成员,他们要负责照顾幼小弟妹。然而,如今孩子成了家庭全心全力灌注关爱的对象,原本的“小小劳动者”也成为需要被庇护的客体。换句话说,家庭成了养育子女的“温室”,原本可以分担家务或协助育儿的那个孩子摇身一变,成了和丈夫一样需要妻子去伺候的对象。
而且,之前在中产阶级家庭里普遍存在的家务协助者,也就是女佣们,她们的薪水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大幅上升,雇女佣逐渐成了奢侈。最终,所有家务全都落到了家庭主妇一个人的肩上。美观整洁的家庭环境,穿着可爱漂亮的孩子,都成了主妇们的骄傲。反之,如果做不好这些,主妇就会被贴上“不合格”的标签。
被赶进封闭空间的妻子们
做家庭主妇是一件孤独的事。井边会议
 不复存在,主妇们失去了原本可以用来倾吐不安与不满的公共空间。在农耕社会中,亲戚之间有很多互相帮衬和进出彼此家庭的机会,家庭之间的边界也比现在模糊。然而,进入现代,核心家庭
不复存在,主妇们失去了原本可以用来倾吐不安与不满的公共空间。在农耕社会中,亲戚之间有很多互相帮衬和进出彼此家庭的机会,家庭之间的边界也比现在模糊。然而,进入现代,核心家庭
 的出现使家庭之间产生了十分明确的界限。
的出现使家庭之间产生了十分明确的界限。
封闭的现代家庭将全职主妇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就像流水线上蓝领工人的劳动被当作是机器的一部分一样,主妇们的工作也遭到了极为严格和机械化的管理。同样,攀比着谁在工作中奉献更多的白领们,也把职场变成了永恒的竞技场。在职场这样一个重视“生产”的场所,大家会优先选择更符合市场主义合理性的选项。可是,在“再生产”,也就是在生育子女的情况下,人们却又好似要反抗合理性一般,追求着自身情绪价值的满足。家庭可以疗愈那些在职场终日厮杀的“企业战士”,为了让他们再上战场,家庭的存在缓解了战士的疲劳,为他们提供安宁与放松的环境。如果丈夫们想要袒露软弱,就需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完成。
如果说负责“生产”的职场是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负责“再生产”的家庭便成了私有空间,全职主妇则逐渐成为其中囚徒。如此一来,将家庭内部的秘密与外人共享变得不合乎常识,主妇们甚至连一个可以不时发发牢骚的同伴都没有。
20世纪50年代,在物质丰饶的美国,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始大批在郊外购买独门独院的房子。丈夫负责打点房子、车子等彰显阶级地位的象征物,妻子将对家庭的全身心投入作为回报。她们打扫宽敞的家,从烤箱里端出亲手制作的饭菜,把丈夫和孩子们都打理得整齐漂亮,更是将无限的热情灌注到孩子们的教育中去。
主妇们只能一边过着所谓的“幸福家庭”生活,一边按捺着难以言喻的不安情绪。她们面对的是只属于“我们”的城池、只属于“我”的地方,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人可以介入的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