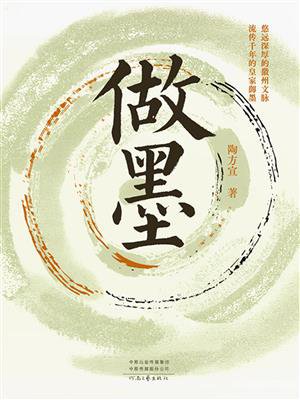第一章
太子之墨
胡黛墨冗长的回忆,从民国十三年(1924 年)春天开始。那是一个闷热的春夜,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尺蠖乱爬,昏鸦聒噪。金黄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如同一场大洪水汹涌而至,淹没了徽州千百座白墙黑瓦的古镇老村。
胡黛墨当年才十七岁,像徽州春山上一丛野兰花,是刚刚创立不久的黄山书院女学生。她和一帮来自徽州一府六县
 的同学,青春年少,同窗共读。从上海来的美人朱若心,母亲在四马路经营“长三书寓”,怕她跟着学坏,便将她送回徽州老家读书。她家祖辈以造纸起家,在绩溪的老宅院里,还开着一座大纸坊澄心堂。母亲希望她将来做个以笔吃饭的读书人,不要像她那样,一生沉溺在胭脂香粉里。与朱若心同来的曹思成并非徽州人,他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读得好好的,却因闹学潮被开除,只好跟随朱若心来到黄山书院。斯斯文文、爱穿青布长衫的汪钧儒,家里在休宁开着大笔庄,开了八代的笔庄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笔娘娘,他也是黄山书院院长汪应泽的儿子。还有常年流连于青楼戏院的江梦生,他弱不禁风,就是一个败家子模样。他家在屯溪城琴溪山下开着一爿大墨庄———徽墨世家,也在歙县江村开着大砚坊脂砚斋。他吵死吵活要到黄山书院来读书,其实根本无心读书,一上课就伏在桌上打瞌睡。汪院长从来不管他,当然也不会打扰他。他醒来东看看,西望望,揉揉眼睛接着再睡。还有胡文礼,他是胡黛墨的哥哥,两人相邻而坐。他们家也开墨庄,在黟县太子岭下胡村开着一爿大墨庄———太子墨。像他们兄妹这样男女同校同窗共读的,如果不是黄山书院这样的新式学堂,根本无法想象。所以黄山书院的学生,无论男女,只要出现在屯溪街上,就会受到市民的指指点点。他们也习惯了,从不计较,也从不当回事,照样在书院里读书看报。空闲时分,照样沿新安江上的文德桥、月亮桥、宝带桥穿城而过,跑步健身,或者结伴到城外琴溪山上、文笔塔下采兰花。徽州一到春天,山山岭岭全是野兰花,野兰花最得女生欢喜,她们往往采了个满怀满抱,抱回黄山书院。
的同学,青春年少,同窗共读。从上海来的美人朱若心,母亲在四马路经营“长三书寓”,怕她跟着学坏,便将她送回徽州老家读书。她家祖辈以造纸起家,在绩溪的老宅院里,还开着一座大纸坊澄心堂。母亲希望她将来做个以笔吃饭的读书人,不要像她那样,一生沉溺在胭脂香粉里。与朱若心同来的曹思成并非徽州人,他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读得好好的,却因闹学潮被开除,只好跟随朱若心来到黄山书院。斯斯文文、爱穿青布长衫的汪钧儒,家里在休宁开着大笔庄,开了八代的笔庄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笔娘娘,他也是黄山书院院长汪应泽的儿子。还有常年流连于青楼戏院的江梦生,他弱不禁风,就是一个败家子模样。他家在屯溪城琴溪山下开着一爿大墨庄———徽墨世家,也在歙县江村开着大砚坊脂砚斋。他吵死吵活要到黄山书院来读书,其实根本无心读书,一上课就伏在桌上打瞌睡。汪院长从来不管他,当然也不会打扰他。他醒来东看看,西望望,揉揉眼睛接着再睡。还有胡文礼,他是胡黛墨的哥哥,两人相邻而坐。他们家也开墨庄,在黟县太子岭下胡村开着一爿大墨庄———太子墨。像他们兄妹这样男女同校同窗共读的,如果不是黄山书院这样的新式学堂,根本无法想象。所以黄山书院的学生,无论男女,只要出现在屯溪街上,就会受到市民的指指点点。他们也习惯了,从不计较,也从不当回事,照样在书院里读书看报。空闲时分,照样沿新安江上的文德桥、月亮桥、宝带桥穿城而过,跑步健身,或者结伴到城外琴溪山上、文笔塔下采兰花。徽州一到春天,山山岭岭全是野兰花,野兰花最得女生欢喜,她们往往采了个满怀满抱,抱回黄山书院。
看起来平静如常的书院生活,就在这个兰花芬芳的春夜被打破。
那日晚饭后,学生们照例依次进入教室,听汪应泽院长主讲“徽州笔墨纸砚探源”。按汪院长的理解,徽州盛产文房四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南宋在临安(杭州)的建都。作为一朝之都,临安城一时人文荟萃、文风浩荡。因为是皇都,它从此取代长安、金陵这样的名城,成为中国文化另一处重镇。作为一位史上闻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与另一位南唐皇帝李后主,给他们所处的朝代带来书画业的空前繁荣,在客观上带动了笔墨纸砚的发明创造,也带动了与杭州一山之隔的徽州的手工制造,文房四宝便在此应运而生,走向鼎盛。虽然杭州与徽州之间山高林密,但是,一条鞭子一样抽在悬崖绝壁之上的徽杭古道、一条蓝带子一样逶迤而来的新安江,又将两地紧密捆绑在一起。徽杭古道上有一处山门石刻,上有四个字:徽杭锁钥。这四个字准确道出了徽州与杭州之间的锁钥关系,徽州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锁,杭州像一把金光闪闪的钥,是杭州这把黄铜钥匙,打开了徽州这把古老的铁锁。
就在汪院长抑扬顿挫的讲课声中,春雨潇潇而下,徽州的春雨总让人心乱如麻,如麻的春雨紧一阵,慢一阵。汪院长宣布下课前停了停,然后缓缓开了口:“两年一度的皇家贡墨即将开始,虽然现在已是民国,但贡墨规矩不变。今年文房四宝同业会破例,给我黄山书院两个名额,大意是让我们新式学堂也要继承徽州文化传统。这次我准备略作妥协,选派太子墨传人胡黛墨与胡文礼两名同学进京。理由很简单,八卦太子墨是皇家御墨,而此次朝廷贡墨,也是皇家御墨,所以选派他俩进京,理所当然。”
汪院长话音刚落,曹思成突然一反常态站起来:“现在已经是民国,还沿袭旧制向朝廷贡墨,更是荒唐透顶。作为新式学校黄山书院,本是开一代新风的教育机构,怎能依然重复旧制?这种古墓荒斋的废物,必须挖出来,砸个稀巴烂。同学们,我们要行动,行动,激烈地行动,过激地行动。行动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说,行动本身就是目的。”
汪院长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同学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身为一院之长,我也有苦衷,我们不能由着性子来。我们一府六县大徽州,一向被世人称作文化之乡,笔、墨、纸、砚全出在徽州。不用我说,同学们应该知道,徽文化就是幽深莫测的传统文化。但凡徽州人氏,哪怕目不识丁者,对文化也充满虔诚与敬畏。在徽州,满嘴之乎者也的老夫子、大师娘举目皆是。我们新式学堂黄山书院,取代私塾、蒙馆、家学,已成为徽州老夫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处处受打压,举步维艰。新旧交替的时代,有时候,为了生存下去,不妨也变通一下、妥协一下。希望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同学们都能理解,特别是曹思成同学,你从上海滩过来,又读过洋学堂圣约翰,你更应该理解我们的苦衷。”
曹思成仍然不依不饶:“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汪钧儒、朱若心、江梦生等一批同学也跟在后面表示反对。胡黛墨突然站起来说:“同学们的意见,汪院长都记住了。我想,大家也不必操之过急,给汪院长一些时间,到时再作决定不迟。”胡文礼也跟着说:“我也同意黛墨的意见。”
汪院长突然收起讲台上的书本、稿纸,果断地说:“这是同业会决定的板上钉钉的事实,不必更改,也无法更改,我也不想为此再费口舌。”
曹思成突然一拍桌子:“你这是让文礼和黛墨留千古骂名,谁不知道溥仪是末代皇上?你看看现在的报纸杂志,全是对他的咒骂。现在还心心念念想着给朝廷贡墨?让新派人士知道,要活活被他们骂死、打死。我不明白,这黄山书院,算什么新式学堂?”
汪院长拾起书本扬长而去,同学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一阵之后,也一哄而散。
人是散去了,一场蓄谋已久的骚乱却突然降临:半夜时分,胡黛墨突然听到一阵嘈杂的怒吼声。她和朱若心共居一室,赶紧跳下床铺打开紧闭的木门,发现通往院外的大门早已洞开,几十个身背书包的学生正聚集在一起。
胡黛墨跌跌撞撞从台阶上冲下来。看到领头闹事的正是曹思成,他疯了似的和劝阻的汪应泽院长揪打起来,汪院长被青砖绊倒,两个人在地上翻滚。胡文礼穿着内衣冲过来,上前揪住曹思成:“住手!思成,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动手打老师。”其他同学知道这样下去太不像话,七手八脚扶起了汪院长。汪院长脸上带着伤,那一刻他神情落寞,完全不是众人印象里那个端坐如钟、脸黑如铁的院长。他威仪尽失,狼狈不堪,站在屋檐下,声音有些颤抖:“同学们,请大家不要轻易离开黄山书院,学习机会,得之不易。”
他剧烈咳嗽起来,胡文礼扶着他去休息,他不肯离开,最后还是胡文礼强行将他拖离。
胡黛墨挤到曹思成面前,她知道他是喜欢自己的,她是个自信的女生,多次捕捉到他眼光里饱含的情意。不仅仅是他,还有汪钧儒、江梦生,或者还有别的男生,她都心领神会,不动声色。此刻,她含着微笑对曹思成躬身施礼:“师兄,别冲动好不好?我会劝院长收回成命。诸位复杂难言的心情,我完全清清楚楚。诸位师兄资历比我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朝廷贡墨都轮不到我胡家兄妹。我会向院长请辞,诸位也不必心急,要给院长一点儿时间,也请理解他的苦衷。在这里,我对诸位师兄深表歉意,请诸位不必愤愤不平,更不要轻易出走,让院长苦心经营的新式学堂毁于一旦。院长肯定会重新考量,或者大家就此商议,共同推选合适的代表。”
曹思成摇摇头:“黛墨,你好糊涂,我是在跟你抢这个进贡名额吗?新旧交替时刻,此时进京上贡,将背负一世骂名。你以后会知道,我们此举是为了救你兄妹。至于我们离开黄山书院,是早就谋划好的行动,与此无关,任何人也不能阻拦。”
更多的同学围拥上来,一时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曹思成说:“黛墨,跟我一起走吧!现在走还来得及。”朱若心说:“黛墨,走吧,大家一起走。”
胡黛墨看着众人灼灼的目光,内心一时忐忑不安。一阵骤雨扫在屋顶,鱼鳞似的青瓦上,发出一片爆豆般的响声。雨水紧一阵慢一阵,闷热加剧,青砖墙壁上沁出一片密密麻麻的水珠,一些尺蠖沿着青苔到处乱爬。油菜花香随风而来,淡一阵,浓一阵。清淡时,芬芳扑鼻;浓烈时,令人头昏。黄灿灿的油菜花黄得像金子,即便在夜晚也可以看到一片金黄。
胡黛墨心绪烦乱,一夜无眠。
那个闷热的春天后来一直留在胡黛墨记忆里,她就在那个春夜得到父亲胡祖春病倒的凶讯,兄妹连夜在新安江码头租船赶回胡村。胡文礼在半道上就下船,去齐云山齐云镇上借高利贷。他们兄妹此时一贫如洗,还欠着黄山书院一笔学费。
胡黛墨天亮时分回到太子岭下的胡村,绕过村口青砖砌就的八卦形太子墓,穿过十六座鳞次栉比的大牌坊。天气越发闷热,山道上有无数蜈蚣在急急奔逃。胡黛墨不敢跨过去,又发现离蜈蚣不远,更多的四脚蛇正在草丛里目的不明地蹿动。抬头一看,近旁香榧、枫香树上,蠕动着密密麻麻的四脚蛇,那潮湿绿的背部和桑子红的腹部,呈现出一种妖异的鲜艳,令人毛骨悚然。她有了一种不祥之感,胸闷得透不过气来。
太子岭上涌起一团乌云,乌云慢慢耸起,越耸越高,像太子岭背面那道高高耸起的万丈悬崖一样狰狞恐怖。顷刻之间,头顶上那道“太子崖”崩塌,乌云迅速密布天空,瓢泼大雨牛鞭子一样抽过来。仿佛老天被放牛娃用牛鞭子捅了个大窟窿,雨水倾泻而下,茫茫大水将天地淹没。
胡黛墨往村里一路狂奔,雨水实在太大,山溪眨眼之间变成了一条咆哮的巨龙。雨水漫漶,到处都是飞溅而下的瀑布。脚底一滑,她从石阶上滚落下来,跌得头破血流,幸好被几棵枫香树挡住。她浑身湿透回到青石巷弄深处的老宅院,父亲胡祖春脸色暗黄如草纸,侧着身子往高脚木盆里吐血,散发出一股腥臭味,血如同篱笆边熟透的桑葚那样,呈现紫黑的颜色。
银耳妈正在照顾他,他们没说几句话,胡文礼已经回来了,瘫坐在病榻前的红漆踏板上,仿佛病入膏肓的是他。
哗哗哗哗的雨水淹没了一切,胡黛墨左手扶门站在那里默默垂泪。胡文礼缓缓开了口:“大大不行了。”(徽州民间称父亲为大大)胡黛墨泪水滚滚而下:“你说怎么办?你去齐云镇……”胡文礼连连摇头:“齐云镇、谭家桥、枫树头,能借的地方全跑了一大圈。人家都怕,怕我大大这一走,剩下你我兄妹两人,穷学生饭都吃不上,哪里有能力挣钱还债?”
胡黛墨痛哭起来,瘫坐在天井柴火堆上,泪水如同天井里的雨水绵绵不绝。雨突然间就下大了,传来青瓦落地的声音。雨一直下到天黑,仿佛永远不会止歇。徽州的雨一下起来就是这样没完没了,令人绝望。
胡文礼坐了半天,突然想起什么,从柴火堆上站起来,绕过青石巷弄,走进远房堂叔胡先圣家。胡先圣在汉口开着两家当铺,据说家里的银子放了几十年不用,生满了乌花(银子放久了会产生锈蚀,民间称乌花)。可是,不管他的口气如何谦卑,甚至恳求,胡先圣始终默默无言,最后只是用两块银圆打发了他,如同打发上门要饭的叫花子。
胡文礼死活不肯接,推让了一番后,胡先圣才开了口:“我侄子,不是叔说你,我老哥病成这样,你死牛肝一个,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怨不得别人。”
胡文礼不明就里:“我叔说轻狂话,我哪里有金饭碗?”
胡先圣说:“胡村人都知道,胡氏一族祖传的八卦太子墨,就在你们家,这太子墨可是李改胡一族发脉的根。全徽州一府六县,从歙县到黟县,从绩溪到婺源,从祁门到休宁,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整个大清朝文人雅士、秀才状元,也都知道,徽州有块太子墨。我在汉口开当铺,一说起我是徽州黟县胡村人氏,都知道那块天下无双的八卦太子墨。有财东托我来买你这块墨,价格自然吓死人,开口就是五万银圆。我跟我老哥说过,他开口就骂。我侄子,你不能像我老哥,守着金山银山讨饭吃啊?五万银圆,你算算值多少钱?北平灯市口上好的四合院,也不过值五百块银圆。上海滩大马路边独门独幢小洋楼,也不过就值一千块银圆。你算算,你好好算算,你一块太子墨,能挣多少洋房洋楼?别说是一辈子,十辈子百辈子也吃不完、花不尽。”
胡文礼摇摇头:“我问过我大大,都是外面谣传,嚼舌头根,家里哪有什么太子墨?”胡先圣从鼻孔里喷出一股气:“你这样说,我也没办法。东西在你家,你不出手,别人又不能上门去偷去抢。”他啜了一口茶水,“还有一个办法,只怕你们不肯做。”
胡文礼说:“就想着救我大大一命,哪有什么法子我不肯做?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想做贼做匪,去偷去盗去抢。”
胡先圣凑近了胡文礼,压低了声音:“你妹子黛墨那么漂亮,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四月里一朵野兰花,六月里一朵栀子花。只要她愿意,我带她去汉口,那是大码头,有钱的财东多得像过江之鲫。如果她愿意做人家小妾,那得到的钱财更多。我负责打包票,从人家那里拿到五百块银圆。她从小是个左撇子,你知道,徽州人认为女人左撇子命硬,一般男人扛不住,只有有钱的财东压得住。”
胡文礼脸色一下子惨白如纸:“她是我妹,我不可能让她去做人家小老婆。”胡先圣翻了一个白眼:“我看你们兄妹念书念到书壳子上去了,妹子怎么啦?治病救人,古人还卖身葬父哩。我祖春哥也是糊涂,供儿子念书不得了,一个女儿也让她念书,他苦他死他活该。”
胡文礼一下子怒火中烧,不想再说下去,要将两块银圆放到八仙桌上,胡先圣拦住他。他突然弯下腰,将银圆丢到青石门槛上,一头扎进雨水里。胡黛墨此时就站在大门外砖雕下,精美的徽州砖雕刻着松枝与白鹤,还有兰草和梅花。她站在廊檐下,显得异常落寞。
胡文礼吃了一惊:“黛墨。”胡黛墨不理她,转身冲进天井:“我叔,我都听到你的话,我愿意跟你走,马上就去汉口。我愿意做人家小老婆,我愿意,只要能拿到银圆救我大大。他不能死,他不能死。”
胡黛墨泪水流了一脸,胡文礼拦腰抱住她:“黛墨,你疯啦?跟我回家。”胡黛墨此时的力气很大,大得如同一只刚刚在山岭上捉到的野鹿。她摇晃着身子左冲右突,将胡文礼摔倒在地,再次冲到胡先圣面前:“我叔,我都听到了,你带我走,马上就走。只要能救我大大,要我黛墨做牛做马都愿意。你知道我从小性子刚烈,说到做到,说一不二。”
胡先圣脸上挂着讪讪的笑意:“这个,这个……我也是替你们着急,这个你想好,我是怕你哥。”
胡文礼从地上翻身跃起,狠狠攥住胡黛墨的手腕,强行将她拖进雨水里,一直拖到自家破败的天井:“你疯啦?我去打长工做苦力是我的命。你怎么能跟他去汉口,还给人家做小?”胡黛墨喘着粗气,胸脯剧烈起伏:“做小又不是死?就是死也不可怕,大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太子墨这块徽州老牌子,就倒了。”
胡先圣这时缓缓踱进来,他背着的手里依然攥着那两块银圆。他将银圆搁在条台下,用插着柏枝的青花瓷瓶压住:“我侄子,我侄女,你们也不必生大气,你叔也是一片好心,叔是为你们着想。我侄女早晚要嫁人,财东家总比苦人家好。汉口又是大码头,不比我徽州胡村,就是一个穷山窝子。”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的胡祖春,突然摇晃着出现在厢房门口,他咳嗽着,凹陷的眼睛闪闪发亮。胡黛墨惊叫一声,和胡文礼冲上前扶住他。胡祖春怒目圆睁:“胡老二,你你你不是人。你早年去汉口做小朝奉,还是我送你银圆做路费。你不借钱我想得开,你哪能出这样的馊主意?畜生!”胡先圣脸红了,他晃了晃脑袋:“老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胡祖春颤抖着:“滚。”他说不下去,又吐出一口血来,血是黑色的,像砚台上磨出的墨汁。
胡文礼和胡黛墨七手八脚,将他拖到雕花木床上。他平躺着,目光平静地看着面前一双儿女。
胡文礼默默垂泪,叫了一声:“大大。”胡祖春喃喃地说:“文礼,别治了,我拖不过三天。大大心里清楚,大大这一生,什么事没经历过?死也死了好几回。”胡文礼平静地看着他。
胡祖春说:“有两样事,我要交代给你们,我一直不想说。但是这一次,我就要走了,不说不行。黛墨,你去把门关上。”胡黛墨走到天井里,胡先圣不见了,地上有一行湿漉漉的脚印子。她闩上沉重的大门,重新回到厢房。胡祖春说:“黛墨、文礼,你们,其实你们不是亲兄妹,黛墨只是我抱养的女儿。黛墨,对不起,大大要走了,不得不把真相告诉你……你,其实是胡家养女。”
胡黛墨吓出一身冷汗,头皮一阵阵发麻。她最后冷静下来:“那,大大告诉我,我亲生父母是谁?”
胡祖春只是摇头:“黛墨,我之所以一直没讲,是怕你难过,我是那年正月十五在新安江上捡到了你。你像一团水草,漂在江中,你命大不该死。”
那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太子岭上高高挂着一轮满月,大得如同挂在树上的灯笼。胡祖春外出送墨回到胡村,小木船泊在太子岭下,就在他洗洗手登岸回村时,突然看到江湾里一圈莹莹绿光,仔细一瞧,天哪,原来是七八只河龙,每一只河龙双眼都闪着绿光。胡村人称鳄鱼为河龙,河龙向来是不祥之兆,传说它们专吃男人的睾丸。可是,河龙一般在夏天涨水时才出现,这样水寒如刀的冬天,新安江里怎么会有河龙出现?他不敢久留,想赶紧回村,跳下船扭头便走,却听到一个女婴猫叫一样的哭泣。他吓得魂飞魄散,回头就看到江上七八条河龙,正围着一个漂浮的襁褓,厚厚的襁褓里裹着一个女婴。女婴从哪里漂来的,他一无所知,也不敢收留,只想快快离开。
他加快步伐逃离时,女婴哭得泣不成声,一声声尖细的啼哭让他心如刀扎。这个女婴太通人性了,好像生怕他跑掉,用不停的啼哭来恳求他,希望救一救她。他实在于心不忍,取来树棍打算吓退河龙,将襁褓弄到江边。那帮河龙似乎通晓他的心思,排成一条线,以布满獠牙的大嘴,将襁褓托到江边。胡祖春弯腰将襁褓抱在怀里,七八条河龙上半身拱出水面,向他点头致意,然后一条接一条消失在江中。
胡祖春说到这里,一时陷入沉默。三个人都屏息静气不说话,胡祖春挪动着身子,似乎要坐起来。胡文礼上前将一床棉被叠起来,垫在他身后。胡祖春用手指残缺的右手,艰难地支撑着身体,慢慢地挪动着,坐好。然后大口大口喘气,听得见他的肺部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胡黛墨长时间低下头,胡文礼岔开这个话题,说:“大大,我听说,我们太子墨庄,一向是徽州著名的大墨庄,家大业大,怎么会突然间就一败涂地?”胡祖春喘息着,平静下来:“就是被人所骗。”
他重新陷入漫长的回忆:多年以前,徽州青年胡祖春、江天福、朱和清三人,都是久负盛名的徽州世家子弟。胡家在黟县胡村,祖传做墨,太子墨名冠徽州。江天福家在歙县江村,开着一爿砚坊脂砚斋,名冠徽州。而朱和清家在绩溪,家中有一个祖传八代的纸坊,造出的纸远销海内外。三个年轻人都懂墨爱墨,以墨会友,交情深厚。朱和清因为深谙墨道墨规,后来被朝廷选为徽州墨务官,专为皇家选墨供墨。三位好友入股,在歙县齐云镇上开了一家名店———徽墨世家,一直在太子墨庄进货。胡家做墨十八代单传,徽州独一无二,徽墨世家一共在太子墨庄赊欠了五千两银子的徽墨后,又来为即将举行秋闱的南京江南贡院进墨一万锭,说妥了一月后送银圆过来,银货两清,经办人为徽墨世家朝奉程名高。
整整过了半年,胡祖春也没见着人来还款销单,便找到徽墨世家。这才发现,朱和清因私藏皇家御墨,被人举报,遭官府通缉,不知所终,徽墨世家也一夜之间从齐云镇上消失。多年以后,他听说程名高在屯溪街上另开了一家徽墨世家,便找上门去。这时候他才发现,江天福早已作古,大管家程名高拒绝承认赊墨之事,反咬胡祖春上门诈骗,告到徽州府衙,众衙役和地保将他右手指打断两根,使他再无法刻模造墨。太子墨庄元气大伤,自此一落千丈。
胡祖春断断续续说完这些,渐渐平静下来,他最后喘息着说:“我要走了,你们俩也别难过,是人总要死,你们好好地活着,别让太子墨这块牌子倒了……太子墨就出在我胡家,徽州李改胡一族从此发脉,徽墨也从此发脉,笔墨纸砚,妙笔生花,徽文化才名传天下。”
胡文礼大吃一惊:“大,徽州人传说中的八卦太子墨,真的就出在我家?”胡祖春点点头,沉默了许久,才开了口:“一代传一代,从唐昭宗之子李昌翼算起,传到我胡祖春手里,已传了十八代,也该传给我儿这一辈了。”
胡黛墨拿起做墨用的黑麻布围裙,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胡文礼点着灵芝样的细脖油灯,一豆幽幽光亮,照着灯脚下一小块斑驳的红漆踏板。在胡祖春指挥下,胡文礼拖开暗淡无光的红漆踏板,用镢头在床沿前刨挖起来。挖到两米深的地方,遇到一块大青石,费了好大力气才掀开那块青石板,地窖里搁着一只陶缸,被油着桐油的木板盖得严丝合缝。将木板揭开,防潮的油纸包裹着一只樟木箱子,四周饰有徽州精美绝伦的木雕,有麒麟送子、观音渡海,四角还装饰着重重的蝙蝠与蝴蝶图案。
胡文礼小心翼翼将箱子捧起来,放到床上,胡祖春眼光明亮:“打开。”胡文礼用了些力气,才打开箱子盖,一股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墨香里夹杂着沁人心脾的草药香气,似乎还有艾草与兰蕙的芬芳。那块驰名徽州的太子墨,就安静地卧在那里,它呈椭圆形,略有点长,正反两面均刻有精美的八卦太极图,像一只饱满发亮的紫茄子,被一块黑丝绸衬托着。
胡文礼小心翼翼地将它托起来,送到父亲面前。胡祖春用缺少两指的右手,轻轻抚摸着,蜡黄的脸上浮现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你闻闻。”胡文礼又将太子墨托到胡黛墨面前,两人都面露惊喜之色。胡黛墨撩了一下额角湿漉漉的鬓发,然后凑上去,一股浓郁的药香,伴随着一缕清凉的微风袅袅而至,仿佛人在炎热的盛夏午后,坐在枫香树下,或坐在生满苔藓的古井台上。
胡文礼将太子墨贴到胡黛墨脸上,她轻轻叫了一声:“啊,好凉。”胡祖春一直微笑注视着一对儿女,有气无力地说:“太子墨的神奇之处在于,冬日里它温暖如绒,炎夏天它又清凉如水。磨墨则不枯不滞,永远墨香浓郁,光亮如漆。只要不用歙砚研磨,它即便放在水中,也永远不融不化。作为盛唐时长安皇家御墨,它从长安未央宫来到我们徽州。徽州有句民谚‘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李墨就是李改胡家族的李家墨。李家就是李唐皇家,皇家墨自然比黄金还要珍贵。”
这个李改胡的故事在徽州一府六县可谓家喻户晓,胡文礼打小就听老辈人说过:相传唐昭宗年间,节度使朱温起兵谋反,放一把大火烧毁长安皇家宫殿,将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皇后何氏为昭宗产下一男婴,名叫李昌翼,被皇仆胡三公伪装成难民,逃出刀光剑影,来到重重叠叠的大山深处:徽州。这里是胡三公的老家,为了保护太子李昌翼不被追杀,胡三公将李昌翼姓氏由李改为他自己的本姓:胡。李改胡这一脉从此便在徽州代代相传,一块皇家御墨太子墨便是胡家身份证明,它被一代一代李改胡长房长孙保管,一直传到胡祖春手中,到此时已有一千多年没有现身。太子墨也终于由一个实实在在的皇家御墨,变成了一个神奇诡异的民间传说。
胡文礼将太子墨重新放进箱子里,胡祖春紧闭着的眼睛突然缓缓睁开:“黛墨、文礼,你们给我跪下来。”胡黛墨声音突然变了调:“大……”胡祖春说:“大大要给你们订下婚约。黛墨,我胡家现在一贫如洗,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你是个好姑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胡家不能亏待你。我的聘礼就是,就是这块太子墨。你,你和文礼,既是兄妹也是夫妻,你俩要好好地活下去,守着太子墨,藏墨做墨,爱墨赏墨,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胡祖春声音颤抖,说不下去。胡文礼和胡黛墨互望一眼,双双在红漆踏板上跪下,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一时泪如雨下。
突然窗外传来一声惨号,胡文礼大吃一惊,一口气吹灭了灯盏。雨过天晴,黑漆阴暗的天井里,落着一片四四方方的白月光,那是一方漂洗得纤尘不染的月光,像一方孝布或挽幛。它落在天井里,像秋霜,又像是宣纸。村外蛙声如雨,油菜花的香气时浓时淡,这是徽州一个春天的夜晚。胡文礼朝天井里看了一眼,月光漫漶,像一盆凉水浇了他一头一身。他竖起耳朵倾听,惨号虽然没有了,但是分明听见一个人,就在窗外夹弄里挣扎,弄出一阵嘈杂的声响。他拿过那柄父亲传给他的雕刀,那是雕刻墨模用的红柄雕刀。他就要出门时,被胡黛墨死死拦住。
窗外的声音停了一会儿,又开始持续,同时伴随着几声压抑的惨号,在空寂无人的半夜三更,听来让人汗毛倒竖。胡文礼果断开门而出,胡黛墨则紧紧跟上。他们在如水的月光下看到恐怖的一幕:一个蒙面人扒在高高的窗台上,两只手被竹箭死死钉入青砖墙壁。蒙面人挣扎了半天无法挣脱,他不想发出惨号,但是因为实在过于疼痛,忍无可忍,又不管不顾发出一连串惨号。胡文礼上前拔掉两支竹箭,蒙面人倒地打滚,又发出最后的惨号,然后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迅速消失在胡村迷宫般的幽巷里。
胡文礼迅速捡起遗落的一支竹箭,发现它以铁皮包着箭头,难怪它可以射进墙壁内,并且将手掌钉住。他四下看了看,迅速拉起黛墨的手回到屋内,关上那两扇沉重的木门。他不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面对卧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父亲,他一筹莫展。胡文礼呆呆坐在天井里,隔着徽州特有的砖雕木雕窗户眺望。月光下逶迤远去的是绵延青山,青山在窗外层层叠叠无穷无尽,月光下如一缕即将消逝的青烟,又如同宣纸上一汪洇化的水墨。那些青青大山就是徽州著名的黄山、九华山、齐云山,它们一年四季云雾缥缈,有无数迷宫一样的古镇老村就深藏在这些大山皱褶里。胡村只是其中的一个,它们就像一个个谜语,在大青山里年复一年沉默着,让人无法猜透。沿着那些古老的村巷蹀躞,似乎也看不到什么,不过就是随处而见的剥麻晒蕨的农人,老宅里悬着粽叶,挂着棕蓑,屋顶上丛生着瓦楞草。廊檐下垒着大大小小的燕巢,木炭炉里炖着火腿与冬笋,背衬着高高低低的青山,白墙黑瓦的古民居沿村巷而列,像山风吹乱的一册线装书,源远流长的徽文化就散落在这些宗祠、戏台、牌坊、天井之中。
胡文礼有过一刹那的愣怔,愣怔自己究竟置身何处,愣怔这个漂亮的妹子胡黛墨到底是他的妹还是妻。
胡黛墨就在此时捧着一瓷碗苞谷面疙瘩过来,左手还拿着一只烤焦的红薯。胡文礼淡淡地说:“你吃,你吃,我不饿,我实在吃不下。”他谦让着,胡黛墨黑下脸:“你得道成仙了是不是?你是男生,今后家里就靠你,大大靠你,我也靠你,你得给我天天吃饱喝足。”
她将红薯递到他面前,然后安静地坐下来,用膝盖夹住双手,定定地看着他。月光从窗口照过来,正好照在病榻上,胡祖春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光亮。一只猫发出一声惨叫,从起伏的老房子封火墙上走过,细腰一凹一凹,对着西沉的月亮叫了一声,像一个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