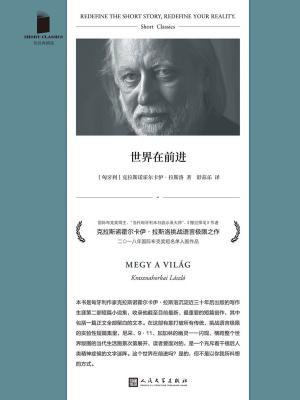最晚在都灵
一百多年前,那是一八八九年一个与今天相似的日子,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大街六号的大门,也许他要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取信。不远处,也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出租马车夫——可以这么说!——正在和他倔强的马匹纠缠。他学了几声马嘶,马儿依然纹丝不动,车夫——叫朱塞佩?卡洛?还是埃托里?——失去了耐心,开始用鞭子抽打这牲口。尼采来到好奇围观的人群中时,马车夫怒不可遏的场面已经结束。在围观人群无法掩饰的笑声中,这个身形魁梧、满面浓须的绅士猛然跳上马车,伏在马背上啜泣起来。房东把他领了回去,他木然、沉静地在沙发上躺了两天,不得不说出最后一句话——“妈妈,我是个傻瓜”。之后,在温柔的母亲和姐姐的照料下,他又活了十年。我们不知道那匹马的结局。
这个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成了理性戏剧的典范,人们天然地相信它的真实性,它尤其生动地照亮了我们精神的终极目标。他是生动哲学的恶魔之星,所谓“人类普遍真理”的耀眼的反对者,对同情、宽容、善意和同理心坚决说“不”的无可替代的胜利者——抱着一匹被鞭挞的马的脖子?用一句俗不可耐的话来说:为什么他没有抱紧马车夫的脖子?
就像莫比乌斯医生说的,这只是一例由梅毒引起的进行性瘫痪。但我们这些晚辈正在目睹一桩悲剧性错误被识别出的瞬间: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斗争后,尼采的存在对他魔鬼般的思维方式的后果说了“不”字。托马斯·曼写道:“这种错误就在于,这个脆弱的、卑劣的生活的预言家探讨了生活与道德之间的交换价值。”他补充道:“事实上,两者相辅相成。道德规范是生活的支柱,有道德的人才是生活真正的公民。”曼的言论——这一崇高宣言的绝对性——如此美妙,这种无条件的高尚宣言甚至让我们想花些时间领略一番,但我们没有,现在,由都灵的尼采掌舵。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水域,也需要不同的神经,甚至更恰当地说,是钢索般的神经。我们会需要它们,因为令我们震惊的是,我们终将抵达托马斯·曼引领我们前往的那个港口。我们将会需要钢索般的神经,因为即使是相同的港口,我们在那里的感觉也将与曼所许诺的相差甚远。
尼采在都灵的这出戏表明,遵循道德法则的精神生活并不意味着一种等级,因为我无法选择其他方式。我可以选择与它 背道而驰 ,但我无法摆脱将我与道德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秘而难以名状的力量。如果我这么做了,并且不顾一切地活着,那么我定能在由人类组织的、无疑不存在任何痛苦的社会中找到出路。尼采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活着和不公正是一回事”,但我无法在化解不了的冲突中找到出路,这时常会将我置于对自己存在之意义的探求中。正如我依然是这个群体世界的一部分那样,我同样也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出于某种未可知的原因,我一直称之为更大的整体。套用无法回避的康德的说法,这个更大的整体在我的身体内植入了这样或那样的法则,以及自由打破法则的可悲的权利。
我们游弋在港口的浮标之间,熟睡的灯塔值班员却无法为我们导航,这让我们变得盲目。我们在迷雾朦胧中抛下锚,迷雾让我们陷入了这样的疑问:此刻,这个更大的整体是否能反映这一法则的更高意义?于是,我们停在原处,无从知晓什么,只能看着同行者从四面八方慢慢向我们靠近,没有任何交流,只是看着他们,满怀怜悯地沉默着。我们认为内心的这种怜悯是对的,靠近者的内心也该怀有这种怜悯,如果不是,那么就期待明天……或者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后。
最晚在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