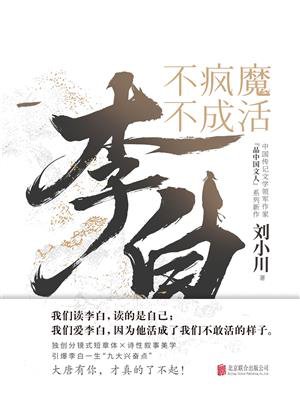“不迹城市”
李白三四岁,跟随父母从吉尔吉斯斯坦(唐朝时在中国境内)迁到西蜀,途中逗留过许多城市。父亲不缺钱,吃住行颇讲究,有趣的地方就待个十天半月,富家孩子一路上惊奇,满脑子遐想。大城小城,面目各异,万家灯火惹思绪,日后杜甫形容:“小邑犹藏万家室。”中原、江南道路安全,每隔三十里有个驿站。从洛阳到长安八百里,每隔五里有一根“里柱”,长路笔直,“野旷天低树”。李贺漫游这条八百里长路,留下许多传世佳作。
城是几百年缓慢生长的城,人是几十年缓慢成长的人。
古代的城与现代的水泥森林具有本质性区别。唐宋六百余年,诗人们持续兴奋长歌短吟。
全世界的诗人加起来恐怕不及唐宋一半。
遗憾的是,李白幼年迁蜀的资料几乎为零。
李白去过渝州(重庆)、益州和眉州。他早期的诗歌不见城市的痕迹。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他待在青莲乡,父亲教育他;其后,到百里外的大匡山读书、学剑。东岩子应该是最早发现李白才华的人,介绍他去见奇人、观奇书。
李白的生命冲动有两大喷发点:一、陶醉于山林;二、干大事,学诸葛亮或谢安。
“一生好入名山游。”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远古生物有一种看的冲动,于是有了一双眼睛。而这个进化过程只能进入哲学家的视野,不属于任何自然科学。生命冲动是柏格森的哲学概念。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自然给了人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注意到:自然在此。”
这等于说,自然自己看见了自己。类似的表达乃是哲学家的专利。
李白“不迹城市”,山林牢牢吸引他,古人的记载有说他居山林十年的。这是一个谜团,这样的谜团现代人是打不开的,这就意味着:谜团永远打不开。李白写山脉,全球第一,那审美冲击波及中国人、外国人。但是李白的强烈感受,我们是感受不到的。我们只能感受第二波、第三波。李白感受十分,我们感受五六分。这是一个动态性的衰减过程——今日青少年感受自然的能力动态性衰减,诗性大打折扣,神性且不论——无从说起。
人究竟是谁?人在什么地方出没?以少年儿童为例,大面积的“自然缺乏症”“运动缺乏症”“劳动缺乏症”“伙伴缺乏症”“美感缺乏症”已经持续数十年了,而自然、运动、劳动、伙伴、美感的价值,乃是人类生活永恒的核心价值。
举例来说,什么是风?树风,草风,山风,水风,沙风,旋风,熏风,晚风,远风,卷地风,穿林风,麦田风,太阳风,稻花香风,“袅袅兮秋风”,穿墙过门的窄窄风,呼啸转向的弯弯风,令人魂牵梦萦的原野之长风……什么是雨?阵雨,暴雨,春雨,秋雨,白雨,山雨,屋檐雨,梧桐雨,风叶雨,毛毛雨,偏东雨,雷阵雨,“鬼雨洒空草”“门前风景雨来佳”“无边丝雨细如愁”“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如今,饱含意蕴的下雨变成了气象术语:降水。
所谓中性词,让世界中性化了,去意蕴化了。世界没味道,导致了感觉的贫乏,端出了一杯生活世界之温暾水,挤走我们的香茶与咖啡。
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活世界的巨大遮蔽,去蔽需要时间,需要强有力的反思与追问。
每一种风都要吹进灵魂才好,每一场雨都要唤起周围世界之统觉才好。赖此统觉,方有世界之亲切。然而,在感觉层面,刮风下雨之丰盈与深切,正在大面积收缩。
人要爱自然,但是在今天必须强力追问,何谓自然?何谓一湾水、一朵花、一棵树?
眼下,迫切需要回答的本源性问题是:人是如何跟一棵树打交道的?
小孩子不爬树不玩树,对树的深切体验为零。长大了,树木山林作为风景,将大打折扣。
爬树是深埋在基因中的原始本能。各种各样的树,笔直的,弯曲的,奇形怪状的,硕果累累的,繁花似锦的,依山傍水的,引发联想、幻觉的,进入梦境的……小孩子的四肢与树干树枝纠缠在一起,唤起百万年的原始本能。
高低错落的树枝仅仅是树枝吗?非也,非也,它比树枝更多,它可以是单双杠,可以是平衡木,可以是秋千架,可以是临碧水的天然跳台,可以是躺下来看书看云的妙处,可以是睡梦香喷喷的有弹性的枝丫床,可以是花香、鸟语、果诱人、风送爽、阳光跳跃的幸福之所。
树木亲切了,树木才是风景。这是关键。关于风景的现象学追问,笔者另文展开。
生活之意蕴层,使任何一种物比它自身更多。反之,则是脱意蕴处理的干瘪之物、蒸馏残渣,硬邦邦的物,赤裸裸的物,是其所是的物,到处横呈的物。人们取之用之废之,只在转手之间。
坝子(成都平原)的数十种鸟鸣,我们这些人一听便知,包括九种丁丁雀儿(小鸟)。爱自然是这么爱的!我们的太阳绝不是互联网上的假太阳。我们的原野我们的风,我们的月亮我们的星空……
海德格尔说:“唯有艺术才能拯救技术。”
李白迷恋山林;李白崇拜华夏历史上的强大者。
此二者,在四川奠定了他一辈子生命冲动的基础。后者使他受辱受挫,伤痕累累。而前者,使他永久性地向汉语思维者发起审美冲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