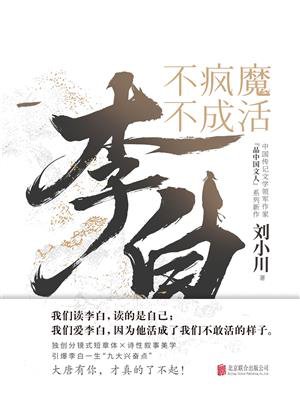《蜀道难》
李白登上了洪椿坪,淋了著名的洪椿晓雨。再往上,拜谒了洗象祠,叩头谢过普贤菩萨,默念西方佛祖爷爷。在接引殿他歇了一夜,次日凌晨,披星戴月登金顶,日出,云海,佛光,峨眉山的三大奇观俱现,据说这是罕见的福报。佛光太神奇了,李白居然在佛光之中!他跳,他手舞足蹈,佛光总能罩定他。神显啊,李白的第一次神显在峨眉山。没的说,从此既要拜李老君,也要拜佛爷爷。李白披荆斩棘上了万佛顶,坐上了一块大石头,看对面万丈悬崖,千仞壁立。“哇,哇哇!”诗人直欲大叫,哪里需要汉字符号。神性与诗意笼罩了血肉之躯,大半天一晃而过,太阳变晚霞,晚霞接黄昏,黄昏托起峨眉山著名的金月亮。
是什么发生了内爆?是远古人类的野性基因?是童年少年的山林体验?
李白尝言:“巢居数年,不迹城市。”
大哲学家尼采讲陶醉,未能思及这一层。中国诗人有非常特别的加强型陶醉。尼采称:“全世界的艺术家只有一个家,那就是巴黎。”这位德国大教授并不懂汉语艺术。
李白在金顶待了七天,滴酒未沾,神性占据时时刻刻,诗意从四面八方袭来。
山顶的和尚不饮酒,偷饮的和尚根本没有。少年酒坛子七天不喝酒,可谓稀奇。“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仙他年有好诗,却与金顶上七天七夜想美酒有关。舍身崖,万佛顶,顶天之绝壁,李太白流连忘返。万佛顶的那块大石头,他坐出了屁股印,历千年犹清晰。唐宋元明清,人们称之为“李白禅迹”。
历史上的一些雅事,源头并不雅。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灵感主要来自他两次爬峨眉山:“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仕途之艰与蜀道之难横呈纸上,李白这首诗,不朽如峨眉山。
苏东坡先后居眉山二十六年,未登峨眉山,不上青城山。他的山水情结显然不及李白。
自由的诗人与复杂的官场有结构性矛盾。这个容后细表。
重要的是,李白的眼睛激活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李白又带动了唐宋元明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