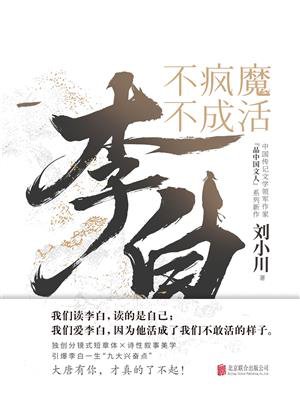“闻余大言皆冷笑”
李白拿舟下重庆,去拜访一个重要人物。此人叫李邕,官居渝州刺史。李白打通关节去见他,拿出师父东岩子的介绍信和三大赋,李邕看都不看,随手递给了白衣幕僚,幕僚又递给更低级的幕僚,穿大布衣裳的低级幕僚也不看,把李白的三大赋捏在手中,仿佛一卷废绢。
李白眼睛直了。浓墨书写的三大赋啊……李邕扫他一眼,不说话。他在想别的。渝州地盘上他说了算,他看谁顺眼谁就有才华。面对干谒者他一般不说话,哼哼,喷气,鼻孔朝东朝西都是说话。“鼻息干虹霓”,官场之常态。李白不甘心仰人鼻息。这里的前提却耐人寻味:李白一心要干大事,先要敲富儿门,先要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唐朝的干谒之风胜过宋朝,李白杜甫白居易皆不能免。大诗人犹如此,小诗人且不论。李白在渝州的刺史府,对李邕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从历代大贤说到他本人的雄心壮志,顺便提到他的绰号李卧龙李东山,他在官厅走来走去,拥鼻高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一个幕僚酸溜溜开了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另一个说:“不知天高地厚,是谓厚颜无耻。”
第三个冷笑:“你这小子狂妄自大,竟敢自比诸葛孔明。”
李白解释:“孔明二十三岁自比管仲、乐毅,我李太白今年也是二十三岁!我李太白五岁通六甲,十岁诵六经!我,诗书琴剑不同凡响!我两次登上了峨眉仙山!”
李邕不言语。此人的文章、书法俱称一流,在朝廷就狷狂。心情好的时候他接济贫士。他不喜欢李白,后来他在北海做太守,对杜甫不错。狂士见狂士很难一见如故,盖因同类相斥。李白到李邕的官邸求见,被拒之门外。看大门的下人白眼他,扫地的仆人扫到他脚下,这叫扫地出门。重庆人劝他:“你娃是哈儿哦,那些臭当官的哪个理睬你?那些臭当官的哪个甩你?你这哈儿哈撮撮的……”哈儿李白没门儿了,敲不开权贵门。白跑了千余里,白花了许多银子,白费嘴皮子……李白徘徊在刺史官邸的高墙外,风中雨中想不通。三天三夜绕高墙,想不通他就一直想下去。想累了,回客栈倒床就睡。在渝州,所有的开销都是自掏腰包,食无鱼,出无车。李白终于明白了,他不是州士,更不是国士,他只是辗转敲门屡吃闭门羹的一介游士。幸好他有钱,未可称寒士。李白二十三岁遭遇了平生第一次羞辱。夜里他大睁着眼睛到天明。在眉州他受宠,在渝州他受辱,破天荒失眠到天明。哦,青春年少,身体超级无敌好,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愤怒的诗人归于平静,盖因他不得不平静,自己抹胸口,白天抹晚上抹早晨抹。平静了一阵子,愤怒再一次突袭他:李邕的那张刺史脸确实太难看了。一剑刺死李刺史!李白在渝州写诗,旷世之作一挥而就。
《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邕看了诗,仍然不表态,很可能他嫉妒。他写诗一千首也不及少年李白的这一首。
“闻余大言皆冷笑。”李白向来不谦虚。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自大是一种向上的生存姿态,骄傲,狂傲,却有越用越多的骄傲本钱。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缺个人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