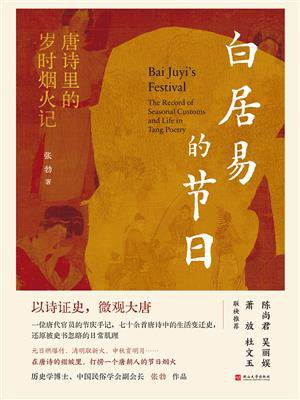引子
白诗中的流光与永恒
节日是以历年为循环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习俗活动的特定时日,由特殊名称、特殊时间、特殊空间、特殊活动、特殊文化内涵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节日是时间的驿站,生活的华章。节日与平常日子互相穿插协调,一弛一张,共同决定着日常生活的节奏。
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节日史。大致而言,先秦时期开始萌芽,秦汉时期初步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已经十分繁荣了。代隋而起的大唐帝国,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号称“海内雄富”,经济空前发展,社会长期安定,城市繁荣昌盛,文化开放包容,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中,经过唐朝人的传承和创造,节日生活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最为绚丽多姿、令人神往的部分,唐代也成为我国节日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新”“老”节日并存。唐朝建立之前,经过长期发展,一个较为完整的节日体系在我国已经形成。根据南朝宗懔(502—565)《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当时流传于荆楚地区的节日已有元日、人日、立春、正月十五、正月未日、正月晦日、二月八日、春分日、社日、寒食、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五月五日、夏至、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秋分、九月九日、十月朔日、冬至日、十二月八日、除夕等。这些从过去走来的“老”节日,大都能在唐代找到它们的踪影。但唐代人并非仅是继承,他们还有许多自己的创造,比如中和节、皇帝诞节、清明节、八月十五、降圣节等诸多“新”节日。另外,一些“老”节日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比如在元日,即新年第一天有“立竹竿、悬幡子”祈求健康长寿的做法,连寺庙也不能免俗,司空图《丙午岁旦》诗云:“晓催庭火暗,风带寺幡新。”
第二,具有浓厚的娱乐色彩。虽然节日历来都不乏娱乐色彩,但唐代以前,不少节日充满禁忌、迷信、祓禊
 、禳解
、禳解
 等观念及活动,人们过节时常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神灵。比如寒食节时人们不敢用火,害怕引起雹雪之灾。但到唐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唐代人已把节日视为佳节良辰,是追求欢乐的日子,当时的节日诗文中频频出现“佳节”“乐”“欢”等字眼。比如,“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冷朝阳《立春》)说的是立春;“佳节上元巳,芳时属暮春”(李适《三日书怀因示百僚》)说的是上巳;“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李适《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说的是重阳。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唐代的节日确实成为时人寻欢作乐的时间。几乎在唐代的每个节日里,我们都能看到欢乐的场面。正月十五,“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牛僧孺《玄怪录·开元明皇幸广陵》);三月三,“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崔颢《上巳》),人们倾城出游,乐而忘归;九月九,“移座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九日登西原宴望(同诸兄弟作)》],人们就在宴饮歌笑中娱乐身心……
等观念及活动,人们过节时常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神灵。比如寒食节时人们不敢用火,害怕引起雹雪之灾。但到唐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唐代人已把节日视为佳节良辰,是追求欢乐的日子,当时的节日诗文中频频出现“佳节”“乐”“欢”等字眼。比如,“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冷朝阳《立春》)说的是立春;“佳节上元巳,芳时属暮春”(李适《三日书怀因示百僚》)说的是上巳;“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李适《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说的是重阳。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唐代的节日确实成为时人寻欢作乐的时间。几乎在唐代的每个节日里,我们都能看到欢乐的场面。正月十五,“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牛僧孺《玄怪录·开元明皇幸广陵》);三月三,“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崔颢《上巳》),人们倾城出游,乐而忘归;九月九,“移座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九日登西原宴望(同诸兄弟作)》],人们就在宴饮歌笑中娱乐身心……
第三,节日活动往往在户外进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空间进行,节日活动也不例外。家作为日常生活的中心,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与此相应,户外则是公共空间,是社会可视空间。节日活动在户外进行,就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允许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更多人的“共同在场”,使节日呈现出热闹繁华的盛大场面。在唐代,虽然也有不少节日的活动是在户内举行的,但人们更愿意走出家门,走向大自然。像前面列举的正月十五、三月三、九月九都是如此。寒食清明节,人们郊游踏青,诸多娱乐活动更是在户外举行。“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杜甫《清明》),这些俯拾即是的诗句,展示了寒食清明期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的动人情景。在同一时间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从封闭的场所走向了开放的空间,从自我的后台走到了自我“表演”的前台。“肉既饱,酒既酣……有歌谣者进,有舞蹈者作,皆诚激乎中,章乎形容。”(欧阳詹《鲁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众人的“共在”,使得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观察者。节日的繁华和热闹就在这表演、互动、观察和被观察中形成了。
第四,宗教因素全面渗入岁时节日节俗之中。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在唐朝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节日也深深打上佛、道的烙印。这一方面体现在一些佛、道节日已成为百姓普遍参与的节日,甚至被纳入国家假日体系。比如十二月八日(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四月八日(浴佛节)、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都源于佛教,到了唐代均成为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参与节日的活动中去,和僧众一起营造节日的盛况。唐代宗就曾用奇珍异宝营造万佛山,并于“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唐懿宗也曾于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举行迎佛骨仪式:“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苏鹗《杜阳杂编》)另一方面,许多世俗节日也出现佛、道色彩的习俗活动。如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在唐代往往被称为上元日,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而它的佛教意味也很浓厚,崔液有诗描写节日的燃灯盛况:“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上元夜六首(其一)》]这里的神灯、佛火、百轮、七宝,无不彰显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另外,受佛、道戒律的影响,唐高祖曾下令:“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宜禁止。”(《唐大诏令集》)后世多位皇帝也不断颁发类似诏令,这深刻影响到很多节日的饮食活动,以至人们过新年(时在正月)、端午(时在五月)、重阳(时在九月)等节日时只能素食,顶多有些腌鱼、肉干而已。
第五,节假日广泛设置。至少从秦汉时代起,国家公务人员已有休假制度。休假一般包括休沐假
 、事假、病假、赐假和节假。节日放假从汉代就开始了,但当时放假的节日很少,普遍以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当时的节假日有40多天,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节假日更增至50多天。主要有元日、冬至,均放假7天;寒食通清明,放假5天;腊日、夏至、玄元皇帝降诞日、皇帝降诞日均放假3天;正月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正月晦日、中和节、春社、秋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上巳)、四月八日(浴佛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三伏(初、中、末)、七月七日(七夕)、七月十五(中元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十月一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均放假1天。这种以节为假的做法影响深远,由此节假成为休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唐代也奠定了节日放假的基本框架。节假日在唐代的普遍设置,对唐代人的节日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在长安建筑仙台,动用三千“官健”加紧施工,因赶工期,寒食节没有放假,结果三千人愤愤不平,差点惹出一场祸乱,最后只得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假才算了事。
、事假、病假、赐假和节假。节日放假从汉代就开始了,但当时放假的节日很少,普遍以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当时的节假日有40多天,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节假日更增至50多天。主要有元日、冬至,均放假7天;寒食通清明,放假5天;腊日、夏至、玄元皇帝降诞日、皇帝降诞日均放假3天;正月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正月晦日、中和节、春社、秋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上巳)、四月八日(浴佛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三伏(初、中、末)、七月七日(七夕)、七月十五(中元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十月一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均放假1天。这种以节为假的做法影响深远,由此节假成为休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唐代也奠定了节日放假的基本框架。节假日在唐代的普遍设置,对唐代人的节日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在长安建筑仙台,动用三千“官健”加紧施工,因赶工期,寒食节没有放假,结果三千人愤愤不平,差点惹出一场祸乱,最后只得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假才算了事。
第六,胡风弥漫。唐朝人开放包容,有着宽广的纳异胸襟。鲁迅先生曾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也因此,胡食、胡妆、胡音、胡俗盛行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殊节点,节日更是胡俗弥漫的时间和场合。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793—864)就曾记载:“开成六年(841)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六年正月六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节日里胡风弥漫,但并未对节日体系、节期、节日的阐释等造成根本性影响。不仅如此,许多在唐的“胡人”还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在过节方面体现出与唐人的一致性。比如登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是新罗人的一个定居点。生活在这里的新罗人在保持本国节日传统的同时,便受到了唐朝节日文化的影响。如圆仁就看到,开成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唐风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唐代节日呈现的上述特征,是唐代社会繁荣的缩影和表征。今天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唐代节日呈现的欢乐、祥和、热闹、多元文化色彩来认识大唐帝国的繁荣和独特气象。而这些特征的出现,既是节日不断传承发展的结果,又与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开放、文化繁荣等时代情境密切相关。
节日作为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唐代节日文化无疑是唐代人共同传承创造的;而每一个唐代人的节日生活,无疑也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唐代人的节日生活去管窥那个时代,也可以借此感受个体节日生活的立体、鲜活和多样性。
而这个唐代人,最合适的也许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因曾官太子少傅,亦称为白太傅。白居易祖籍太原,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唐武宗会昌六年(864)去世于洛阳,获赠尚书右仆射,享年七十五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传统社会,白居易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加长寿。他的生命历程恰恰伴随着由安史之乱后的凋敝走向中唐时代的中兴,而这一时期也是唐代节日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白居易是在政府中长期担任公职的官员,其通过刻苦学习由科举走向仕途,但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政治漩涡中被抛来抛去后,终于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中选择了后者。他曾经吃过道家的药以求长寿,但对佛教更加情有独钟,晚年自号香山居士,最终成为一名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他是一位多产佳作的诗人,年纪轻轻就显露出非同一般的诗才,并受到时人的推崇。贞元三年(787),年仅十五岁的白居易初次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有行卷
 的做法,他就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访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后不禁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当他打开卷轴读到第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后,就立刻改变了态度:“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张固《幽闲鼓吹》,上同)
的做法,他就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访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后不禁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当他打开卷轴读到第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后,就立刻改变了态度:“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张固《幽闲鼓吹》,上同)
白居易有着很强的国际影响力。他还在世时其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新罗
 等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日本,白居易更受推崇,被誉为“一代之诗伯,万叶之文匠”。日本的知识女性也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文。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雅号“草庵”,即采自白诗“庐山雨夜草庵中”(《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一句。清少纳言入宫后成为皇后定子的女官。一次大雪之后,定子问左右侍从:“香炉峰雪想如何?”清少纳言即起身将殿前的御帘掀起,请她凭栏远眺,结果受到定子和侍从们的盛赞。原来白居易《重题》诗中有“香炉峰雪拨帘看”之句。由此可见清少纳言的聪慧和后宫女子对白诗的普遍熟悉。直到今天,在日本京都“祇园祭”中,还有白乐天山(はくらくてんやま)。为期长达一个月的京都“祇园祭”起源于平安时代,与大阪的“天神祭”、东京的“神田祭”并称为“日本三大祭”,直到现在依然传承良好,其中7月17日的“前祭”与7月24日的“后祭”都有山
等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日本,白居易更受推崇,被誉为“一代之诗伯,万叶之文匠”。日本的知识女性也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文。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雅号“草庵”,即采自白诗“庐山雨夜草庵中”(《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一句。清少纳言入宫后成为皇后定子的女官。一次大雪之后,定子问左右侍从:“香炉峰雪想如何?”清少纳言即起身将殿前的御帘掀起,请她凭栏远眺,结果受到定子和侍从们的盛赞。原来白居易《重题》诗中有“香炉峰雪拨帘看”之句。由此可见清少纳言的聪慧和后宫女子对白诗的普遍熟悉。直到今天,在日本京都“祇园祭”中,还有白乐天山(はくらくてんやま)。为期长达一个月的京都“祇园祭”起源于平安时代,与大阪的“天神祭”、东京的“神田祭”并称为“日本三大祭”,直到现在依然传承良好,其中7月17日的“前祭”与7月24日的“后祭”都有山
 巡行。所谓“山”,是两种不同的祭祀用山车。其中规模大,有四个车轮推着走,中心装饰有一根巨大冲天真木;山则规模小,由多名壮年男子协力抬着前行,且中心部分设有冲天真木的装饰。山中一些是用古代中国故事命名的,白乐天山就是其中之一,表现白居易和道林禅师的问答场面。车顶站着头顶官帽、手持笏板的诗人,就是白居易。
巡行。所谓“山”,是两种不同的祭祀用山车。其中规模大,有四个车轮推着走,中心装饰有一根巨大冲天真木;山则规模小,由多名壮年男子协力抬着前行,且中心部分设有冲天真木的装饰。山中一些是用古代中国故事命名的,白乐天山就是其中之一,表现白居易和道林禅师的问答场面。车顶站着头顶官帽、手持笏板的诗人,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的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深受人们喜爱。尤值一提的是,白居易十分注意编辑、保存自己的作品,因而为后人留下了据以研究的重要资料。他先是在大约四十三岁时为自己编了一个15卷的集子,五十二岁时又由好友元稹帮助结集成《白氏长庆集》50卷,此后不断增补,直到七十四岁时,终于编定75卷的《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40篇。为保存作品,他还曾把三本文集分别寄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和洛阳圣善寺。虽然由于世事变化,白居易亲自编定的文集并未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唐以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得以存世。今人朱金城先生有《白居易集笺校》一书,“笺校全部《白集》及补遗诗文共三千七百余篇”
 ,其中与节日相关的诗文120多篇,涉及节日约二十个,创作时间从十六岁到七十五岁,跨度长达六十年,创作地点也随作者的行迹不拘一处。由于这些诗文的创作时间(多写作于节日当天)和创作地点十分清晰,我们不仅有可能将白居易描写的节日生活和当时的节日习俗相联系,而且有可能放在他的日常生活之流和生命历程中去解读。事实上,这些因节日而写,为节日而写,写节日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诗文,不仅是白居易自己的节日生活记录,也成为再现唐代节日样貌的难得史料。
,其中与节日相关的诗文120多篇,涉及节日约二十个,创作时间从十六岁到七十五岁,跨度长达六十年,创作地点也随作者的行迹不拘一处。由于这些诗文的创作时间(多写作于节日当天)和创作地点十分清晰,我们不仅有可能将白居易描写的节日生活和当时的节日习俗相联系,而且有可能放在他的日常生活之流和生命历程中去解读。事实上,这些因节日而写,为节日而写,写节日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诗文,不仅是白居易自己的节日生活记录,也成为再现唐代节日样貌的难得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