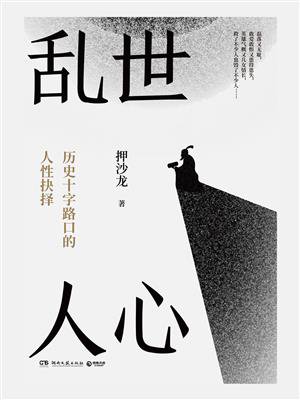二
但是有件事很奇怪。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暴力,是战争,是政治秩序的彻底丛林化。大形势很不乐观。各国的军备竞赛全面升级,野蛮善斗的秦国在西部崛起,至少对于儒家来说,这预示着一个黑暗恐怖的未来。但你翻看《孟子》的话,却会发现他最大的假想敌并不是那些操纵暴力的人,而是两个不相干的人物:墨子和杨朱。
孟子非常痛恨墨子和杨朱,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孟子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距杨墨、放淫辞”,不让他们胡说八道,整个社会才会好起来。他甚至上纲上线,把对杨朱、墨子的态度作为判断一个人好坏的依据。什么是圣人之徒?谁反对杨朱、墨翟,谁就是圣人之徒!
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杨朱、墨翟和孟子的观点,确实有很大差异。
首先说杨朱。在思想史上,杨朱是个谜团,因为他没有著作,或者有著作也没流传下来。关于杨朱的主张,人们都是听他的对手们转述的,这就难保没有简化歪曲的成分。《列子》里倒是正面记载了他的一些话,所谓“杨朱曰”如何如何,但是《列子》本身就是部伪书,所以杨朱到底“曰”过什么,还是说不清楚。按照孟子的说法,“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自私透顶。按照现代学者的解释,这也许是种曲解。杨朱说的未必是“一毛不拔”,而是“一毛不换”——即便拿全天下的财富换我的一根毛,我也不换。
这样一听似乎也没什么,毛长在杨朱身上,人家爱换不换。而且退一步讲,就算杨朱真是主张“一毛不拔”,最多也只是自私冷漠,遇事不出头而已,离真正的邪恶还有十万八千里,何至于就是禽兽呢?
再说墨翟。墨子的主张就比较明确了,主要是兼爱、非攻、尚同、明鬼、节葬那一套。现代学者多半都不喜欢“尚同”这一点,认为这里有精神控制的味道。但总的来说,大家对墨子还是以称赞为主,觉得精神可嘉。孟子本人也承认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并不是个自私的人。但是他对墨子的观点极不赞成,比如墨子主张薄葬,孟子就觉得他不孝顺,没良心;墨子说兼爱,孟子更是摇头,你能把亲侄子跟大街上的陌生小孩一样爱吗?这不成了神经病了吗?这还有人味儿吗?
在这一点上,孟子指责得有道理。墨家的说法过于高调,不近人情,真正实行起来恐怕会破坏人伦。但问题是:这就跟杨朱的学说一样,即便不对,也只是不对而已。满世界都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兼爱,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又是多要紧的争论呢?
放在那个大环境下看,孟子和杨、墨的主张其实多有重合,比如他们都反对战争。杨朱主张“贵生”,自然讨厌打仗。墨子更是把“非攻”放到理论的核心之处,他认为杀一人是不义,应该处死刑。那么杀十个人就该是十个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死罪。一旦打仗,“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发动战争的人怎么就不是死罪呢?这和孟子的反战言论并没有太大区别。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朱、墨翟,他们都反对屠杀,反对暴政,反对战争升级。他们的分歧,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的分歧。既然如此,孟子又何必把杨、墨当成头号假想敌呢?他又何必把对杨、墨的态度看成衡量是非的标准呢?
这就像外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还非要固执地认定用弓箭还是用矛戈对付虎狼,是顶顶重要的原则之争。跟这个争论相比,虎狼倒没那么可恨了。说起来,这也是人性中常见的偏执。写到这里,不免想到《笑傲江湖》里的华山派,一边说要练气,一边说要练剑,因为这个打得血头血脸,“气剑不分,是禽兽也!”最后等到日月神教来了,把气宗、剑宗一起捉了,挨个杀头。
这下好了,啥都没有了,也就不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