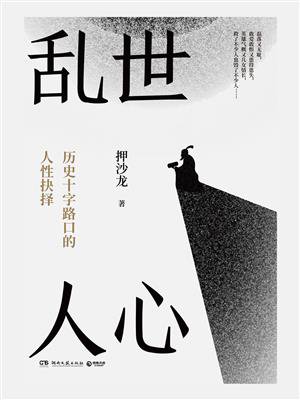一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史记》。中国正史的纪传体写法,也是从它开的头。如果没有《史记》,那么正史修撰者也许会延续《春秋》的编年体,大家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就很可能会是一部部类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的东西。这两种写法各有利弊。纪传体搞不好的话,容易像是人事局的干部档案袋;编年体搞不好的话,容易像是报社的新闻合订本。不过,要论起史料丰富性,似乎还是纪传体的存纳空间更大一些。
在中国史学传统里,司马迁是个奠基性人物,后来的史学家几乎都活在他的影响里。但是,真要拿司马迁和那些人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是独特的,跟谁都不一样。这倒不是说司马迁写得最好,所以与众不同。真正的差异不是才华,也不是能力,而是他们压根就不是一类人,兴趣点也不在一个频道上。
后来的史家都延续了《史记》的体例,但是在精神上,他们遵循的其实是班固路线,关注的是这类问题——比如一个大臣是忠还是奸?一个皇帝是明还是昏?一个社会是治还是乱?一项政策是好还是坏?从《汉书》到《清史稿》,差不多都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着。
可司马迁不一样。这有点像伯林(Isaiah Berlin)说的“狐狸和刺猬”的区分。班固他们是刺猬,心中只有一个大念头;而司马迁就是一个狐狸,对各种念头都感兴趣。他给任安写过一封很有名的信,里面就说自己的志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说得很大,也很笼统。什么是“究天人之际”?搞不太清楚。不光我们搞不清楚,就算司马迁自己也未必能搞得清。它有种无边无沿的感觉,这也难怪,司马迁的兴趣本身就是无边无沿的。所以人们读《史记》的时候,往往也想不到什么以史为鉴,只觉得千流万壑,尽奔眼底,有种仰俯天地、浩瀚苍茫的感觉。
不过,兴趣太宽泛了,就容易管不住自己。古人说“太史公好奇”,就是指他缺乏自制,太过偏好新奇之物。袁枚的评价则更露骨,他说司马迁这个人,有时候明知道某个事儿是假的,但是“贪于所闻新异”,所以照写不误,态度很不老实。这话也许有点苛刻,但并非毫无根据,司马迁确实有这个毛病。
就拿“赵氏孤儿”的故事来说,漏洞百出,绝非事实。屠岸贾这个大反派更是子虚乌有。但是这个故事实在太动人了,司马迁舍不得放弃,就把它收入了《赵世家》里。史学家很快就发现这个故事有问题,唐人孔颖达对此评论,“马迁妄说,不可从也”。那么,司马迁本人知道这是“妄说”吗?多半也知道。所以他一边在《赵世家》里收入“赵氏孤儿”的传奇,一边又在《晋世家》里老老实实记下另一个朴实无华的版本。
在《史记》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田单大摆火牛阵,“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大败燕军。清代的袁俊德就指出,这蕞尔小城,又被围了三年,哪里还有这许多牛?肯定是编的。可是老实人读了以后就会上当,宋朝有个将军邵青,读了《史记》以后就想照抄“火牛阵”,结果敌人拿弓箭一通射,群牛乱奔,把自己的队伍倒冲垮了。
《史记》里关于韩信的事迹也很可疑。司马迁说韩信用砂囊堵水,等敌人过河过到一半时,撤去砂囊放水,淹死敌人无数。对此,曾国藩就不相信:砂囊堆成堤堰,绝不可能忽堵忽决。至于什么韩信大军“木罂渡军”,更是无稽之谈,我亲自到那段黄河看过,哪里是木罂就能渡过去的?
司马迁性格就是如此,喜欢张扬阔大的人性,喜欢尖锐的戏剧冲突,喜欢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绝。这让他的文字有了双重色彩,一方面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被打动。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又说它“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这种评价里,就隐隐有点可疑又可爱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史记》确实有强大的魅力,其中有些章节简直就像是散文版的古希腊悲剧,悲怆而迷人。那些文字中弥漫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像绝域中一座突兀的山,尘世中一柄冷冷的剑。后来的中国也出了很多史学大家,但是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史记》成为“绝唱”,并非全是因为天才不可复制,主要还是时代变了。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人物,都不属于新的时代。
新时代里,没有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