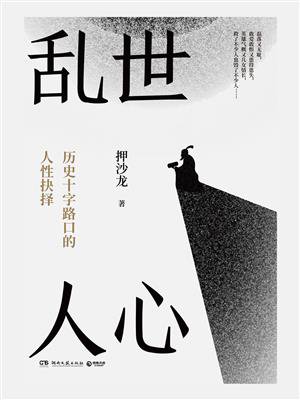三
《史记》里面,人们的勇气往往还有另一种维度,那就是恣肆。
在先秦时代,大一统帝国没有成型。人们有很多观念,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人世间,尚无一种可以笼罩天地,让人们无处可遁的话语体系。权力的话语、公域的话语、道德的话语虽然都存在,但还不够强壮,没有彻底压倒民间的话语、私域的话语、血性的话语。
这可以拿《伍子胥列传》做例子。
当时的楚国和吴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楚平王杀掉了伍子胥的父兄,这当然是楚王对不住他。可是伍子胥为了私人恩怨背叛父母之邦,带着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用后世的道德标准来看,这么做很容易招致诟病。
可司马迁完全不认为伍子胥有什么错,他说伍子胥是“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至于带异国军队攻打楚国,司马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不光司马迁觉得没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没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压倒个人,君主还没有压倒家族,复仇的火焰可以毫无顾忌地快意燃烧。
《刺客列传》传达出来的观念更有意思。
当然,也有人说《刺客列传》可能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他父亲司马谈写的,这里也不必深究。总之,这篇文章一共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聂政。后世的不少文人都觉得聂政这个人很有问题,比如明代的黄洪宪就骂得很厉害,他说司马迁写的那五个刺客里,专诸很低下,而聂政最低下。严仲子送给聂政一百金,他就把自己的命许给人家。其实严仲子和侠累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君父之仇,不过是争权夺利的私人恩怨而已,聂政无谓地卷进去,为此毁容、杀身,他这是勇敢吗?他这是正义吗?这跟猪羊卖肉有什么区别?!
这就把聂政说得形同猪狗了。
这种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那就先来看一看聂政的故事。
当时韩国有一场政治斗争。大臣严仲子和丞相侠累有矛盾,害怕侠累害自己,想抢先一步,雇凶杀人。聂政是个齐国的屠夫,大家都说他很厉害,严仲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
严仲子跑到齐国,恭恭敬敬上门拜访,还“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当然,所谓“为聂政母寿”,就是一种说话技巧: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妈的!其实就是送给聂政的。聂政觉得不能无缘无故拿这么多钱,不肯接受。
严仲子就实话实说了,我有仇人。
聂政回答,我母亲还在,所以我不能以身许人。他把这些金子退回去了。
过了一阵,聂政母亲死了。他去找严仲子,说,现在可以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仗剑而行,到了韩国。他的刺杀方法极其简单利落,不用化妆,也不用献图。他直接找到相府,二话不说就杀进去,一直杀进大堂。侠累正在那儿坐着,聂政上去就把他刺死了,周围的卫士也被他杀了好几十个。这种武功确实高得不可思议。
最后,聂政怕被认出后连累自己的家人,就把自己毁容,挖出眼睛,然后剖腹自杀。
故事至此完结。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关键问题:聂政为什么要替严仲子杀人?
聂政自己是这么说的:“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说:严仲子身为贵族,我是个屠夫,人家这么谦卑地跟我结交,我要报答他,替他杀人!
在后人看来,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充分。
可以拿另一个故事跟聂政对比一下。《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田七郎》,讲的是勇士田七郎感激于武承休的知遇之恩,替他杀人报仇的故事,情节和“聂政传”颇为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受了《刺客列传》的启发。但《田七郎》在叙事上有个很大的不同,它用很大篇幅交代报仇的背景,渲染武承休如何含冤受屈,他的对头甚至还利用手中的权势,把武承休的叔叔活活打死,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蒲松龄这么写,就是要强调一件事,田七郎替他报仇是道德的,是正义的。可司马迁倒好,他对严仲子和侠累的恩怨,甚至都懒得交代。
谁对谁错,根本就没关系。
在《刺客列传》里,聂政的态度很简单:你对我好,我就替你杀人报仇!其他的跟我无关。这多少有点像后来黑社会的作风,所以也难怪黄洪宪瞧不上聂政。现代人的价值观,更接近于黄洪宪,而不是聂政。文明已经驯化了黄洪宪,也驯化了我们。可是在《刺客列传》的世界里,人们还没有被驯化,在聂政看来,个人之间的“情义”比什么都重要。“情义”就是最大的正义。你对我好,那么我就用生命来报答你,至于你的是非曲直,道德与否,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这种“情义”曾深深打动了司马迁,但是到了蒲松龄的笔下,“情义”就必须由道德伦理来包裹,否则就是让人不齿的“蛮勇”。
不过,《刺客列传》里的“情义”并不平等。刺客们坚信人与人之间有等级,有高低贵贱。面对高位者表现出的“情义”,低位者要用更多的“情义”来回报,其分量的多寡几乎不成比例。
聂政去杀人的理由就是:人家身为公卿,对我这个屠夫如此客气。可如果严仲子是隔壁的另一个屠夫,客客气气地求上门来,那聂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魏公子列传》里的侯嬴也是如此:人家是魏国公子,居然对我这个看大门的老头如此恭敬,我怎么能不感动?怎么能不为人家自杀?
我们对这种想法可能有点无法接受,但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先秦时代的社会在某些方面虽然比较宽松,但是绝不平等。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就像《左传》里说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们的身份等级有严格的界定。后来,大一统帝国兴起,很大程度上碾平了这座金字塔。所有人都变成了帝王的绝对臣民,身份等级的观念反而有所削弱。
不过,这种金字塔有点像托克维尔说的“贵族化社会”,多少给自由留下一点点罅隙。所以,侯嬴、聂政这些人虽然认可等级,但也拥有独立人格——我可以对你忠诚,可以为你舍弃生命,可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用你的“情义”来交换的。这种交换不是等价的,信陵君、严仲子他们谦恭一下,侯嬴、聂政就要拿命去换,双方付出完全不对等。但不等价的交换,毕竟还是交换,交换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独立,而奴隶是无法和主人做交换的。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贵族时代的普遍精神。当时,人们还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笼罩,还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权利也被淹没了。忠诚和服从再也不需要条件。
前面说到了伍子胥的故事,那么不妨再看看李陵的故事。
李陵的战败被俘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可他的老母因此被杀掉,妻子儿女被斩尽诛绝。司马迁替他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也因此被处以腐刑。如果按照伍子胥故事的逻辑,李陵当然有权向汉武帝报复,先秦时代的人无疑都会这么想。可是时代不同了,汉朝人并不认为李陵有这个资格。
在《答苏武书》里,李陵最多也只能抱怨几句“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这已是当时道德所能容忍的极限了。就算这样,更多的时候李陵还是哀叹“命也如何”。
当然,《答苏武书》多半是篇伪作,但是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匿名作者为李陵辩白喊冤,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再往下说,自己可能都会觉得有悖天理。
从伍子胥到李陵,哪种观念是正确的?不好评价。但是从这种演变里,存在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人们从“相对的时代”渐渐走向了“绝对的时代”。